保定问题的来龙去脉
(四)
作者 邵小兵
有不少读者问我,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文中提到的军区和河北省主要领导及相关人物的姓名呢?说心里话,对这个问题,笔者是相当的纠结和为难的。在这之前,《保定风云》的作者可是直呼其名,几乎没有任何的遮掩。但我一直认为,对这些领导人要全面和历史的看,他们在战争年代都是立下战功的人,对于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要放在特殊时期的大背景下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一切。当然,对于他们的问题和缺点,笔者尽可能的回避和少讲,实在绕不过去的地方我会实事求是的点到为止。
——作者留言
陈伯达在石家庄和邯郸等地的讲话,将保定的”工总派”判了死刑,也将极力支持”工总派”和”工筹派”进行大联合的38军推到了风口浪尖,处境相当的艰难。何去何从?如何应对?刻不容缓地摆在了38军的面前。
按照通常的认知,下级服从上级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军队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作为下级谁愿意与上级领导对着干呢?那不是犯错和找不自在吗。如果是战争年代或者是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和抢险救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38军肯定是要毫不犹豫的无条件的坚决执行。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各种各样的矛盾交织,诡秘和复杂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一些问题判断处理起来相当的棘手和困难,而且全国不少地方也有在支左问题上下级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有人会问,38军为什么那么硬气和顽强,那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主席的指示和军委的命令,而且还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大联合的愿望为底气。所以面对困难的局面,38军敢于斗争,敢于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虽然对方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的超大号人物,而且围在他身边马首是瞻、听令于他的是军区和河北省委、省军区的主要领导。现在看,当时38军的力量的确是太弱小、处境太困难了。
一月初的那几天,38军党委会议室是烟雾缭绕,灯火通明,党委班子成员连续好几天开会,研究如何应对陈伯达等的讲话问题。
在讨论中,很多同志对陈伯达等人的两面三刀、颠倒黑白的做法非常反感和气愤。但是在如何处理上又拿不出好的办法。是死扛硬顶?还是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作为军长的李光军和政委王猛压力山大。最后大家经过研究,一致同意,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听听各师团的领导和支左一线的同志是什么看法和意见。
保定于家庄火车站
1968年1月15日,也就是陈伯达等对”工总派”宣布死刑,命令38军抓人、明确表态认错的半个月之后,38军86名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在当时的113师师部于家庄召开,史称:于家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为了避人耳目,防止会议内容外泄,负责支左工作的李军长、刘副军长等军首长和支左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像平常一样坚守岗位。
这次会议开的很特别,也非常的民主。主持会议的王政委真诚地动员参会的同志打消顾虑,敞开思想,对军长政委和军党委有什么批评意见可以毫无保留的提出来。
王政委动情地说:”我们不要怕否定自己,不要怕否定38军,如果这次会上,大多数同志认为我们真的有错了,我们就要为保定六百万人民负责,也为38军全体指战员负责,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我和李军长负一切责任,我们去向保定人民负荆请罪,向陈伯达认错检讨,请求处分。”
王政委的开场白,让大家打开了心扉,无所顾忌的发表埋藏在心底的声音。
会议开始后,王政委首先详细介绍了38军刚到华北介入保定文化大革命所面对的形势。通报了军党委如何指导支左工作一步步的做法和要求。然后采取”四头对案”的方式,领着大家重温主席、中央军委发布的十条命令和对军队支左工作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和要求。接着,又把陈伯达和军区主要领导在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一次次讲话,对38军一次又一次的批评和38军党委的态度和思考,一条条、一件件原原本本的摆在桌面上来,让参会的同志自己领悟和理解:
看看毛主席怎么说的,
看看陈伯达怎么说的,
看看38军怎么做的,
看看保定怎么变化的,
“四头对案”,对照分析。
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对在哪里?
错在哪里?
对正确的怎么办?
对错误的怎么办?
大家回忆讶,对照讶,分析讶,比打一个大战役搞总结还认真严格。
身处支左第一线的师团主要领导同志纷纷开腔,他们说:我们从长白山下来到北京附近、中央身边,大家都很高兴,但没有想到这儿的政治环境这样糟糕、关系那么复杂,有些人看不上我们这个”外来户”,处处刁难找茬。从介入保定的”文革”开始,我们就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生怕有一点闪失。同友军支左的同志打交道,态势温和,细声慢语,生怕引起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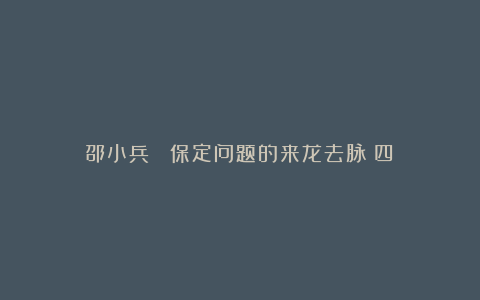
这一年,我们全军没有解散和取缔一个群众组织;
这一年,我们没有向任何群众组织发过一条枪;
这一年,我们没有一次在社会上发表过单纯支持一派群众的讲话;
这一年,我们没有公开散布过一次对陈伯达和军区领导的不满言论;
这一年,我们全军上千人被打,数百人受伤,几十个干部战士被打死。一想起他们,真是伤心的掉泪,我们怎么对的起他们的父母、妻儿老小?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他们死的比战场还惨,我们到底有什么错,我们还要认什么罪?
有些同志说到这里,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难过的哭出了声音,会场上弥漫着痛惜和悲愤的情绪。
有些同志说:如果我们听陈伯达的指示,执行上级的命令,不分青红皂白地转头支持”工筹派”,而去打压”工总派”。
“工总派”真的能老老实实吗?他们的人数可是远超另一派的。如果真的”工筹派”单独掌权,保定的武斗能制止了吗?”工总派”肯定不服,会十倍百倍的反抗,那样保定的武斗会升级,社会将长时间无宁日,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动荡不安。一派建立的所谓”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因为没有大多数群众的拥戴和支持,又缺少大联合的基础,很快就会垮掉的。
到那时,我们38军真成了历史的罪人,成为保定六百万人民的罪人。
因此,参会的同志一致反对向错误的领导低头,不同意执行破坏大联合的一切指示和要求。
王政委在会议过程中没有讲话,他担心自己的观点容易引起导向的作用,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因此他始终强调要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让大家都讲真话、说实话。直到会议总结时,王政委才谈了自己的态度。他坚定的说:”如果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错,但看到前面征途上有危险,就因此而低头,违心认错,这不就是战场上因为怕死而放下武器投降吗?打仗有危险就要下战场,就不是真正的军人,也不是38军的传统和作风。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真理而怕打击,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不能违背做人的良心,不能违背军人的职责,不能违背共产党员的党性……”
同时,王政委还宣布,无论是在一线支左的同志,还是在部队正常工作的官兵,不管是团以上干部还是基层的干部战士,对我们在解决保定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人随时可以反映看法和提出批评意见,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决不歧视、决不排斥、决不打击。在我们内部一定要形成发扬民主、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
听了王政委的总结,大家群情振奋,使劲鼓掌,不少人热泪盈眶。有的同志激动的站了起来,激动的高声说:”我们是38军的英雄汉,我们要做真正的共产党员,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是低头认罪趴下去,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坚持到底!”
会场上只有86个人,可吼声却响彻云霄,震的地动山摇。
这次38军党委扩大会议开得人人热血沸腾,个个斗志昂扬,大家没有认为38军支左错了,没有害怕退却。许多师团首长被李军长和王政委等军领导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威武不屈,立党为公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纷纷表示:有人对38军算账,那怕是撤职、罢官、坐牢,甚至杀头,我们愿和军首长一起承担,那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这次”于家庄会议”是一次凝聚力量,鼓舞士气,斗争到底的大会,为38军坚决同陈伯达等的斗争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为38军在十年动乱的旋涡中站稳脚跟,奋力搏杀,没有沉落丧气树立了坚定的政治勇气,是38军在特殊历史时期一次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会。多少年后,每每谈起和回忆这次军党委的扩大会议时,一些参会的老同志仍然心潮澎湃,悲壮不已。王猛老政委曾动情地说:这步棋是38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一步指导全局的好棋,是一步绝处逢生的妙棋,怎么形容它都不过分。
心中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冲锋陷阵就更加无所畏惧。党委扩大会议之后,李光军军长、王猛政委、刘海清副军长、邢泽副政委,四人联合签名,向党中央、毛主席先后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反映两派群众迟迟不能联合的原因;一份是对保定问题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有人会问,38军为什么越过军区,直接向中央写报告,这不符合规矩,其实在这之前和后来,38军为了解决和处理保定问题共向军区发了234封电报,写了47份报告,但都石沉大海,音信全无,所以向中央直接报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被形势逼迫的举动。
当时摆在38军面前最辣手的问题是两件事,一是陈伯达和军区主要领导指示38军抓捕农大造反团头头崔世林,该组织是”工总派”的骨干组织之一,让38军去抓人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另一件事是与省军区发表共同声明,支持陈伯达的所谓重要的讲话。
对此,军里的回复是:崔世林不知去向,我们找不到他,省军区办法多门路广,让他们去抓吧。这件事就推了出去。
崔世林当时21岁,是河北农业大学的学生,其父亲崔田民是开国中将、铁道兵的政委,”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打倒,是被陈伯达多次点名批判的军队高级干部。
说来也有意思,崔世林我真认识,还见过几次面。记得在1967年初冬的一天,我父亲带我去洗澡,路上迎面过来几个人,他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其中一个身材不算高的就是崔世林,他看着干练利索,精气神十足,说话幽默风趣,一口的京腔,根本看不出来他就是特殊时期保定地区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们和我父亲比较熟悉,东拉西扯不知说些什么。当他知道我的身份后,笑嘻嘻蹲在我的面前,把我的手拉到他的腰部,我感觉触碰到像铁一样硬硬的东西,他伏在我的耳边,小声说:”有空我带你去打枪”。这我才弄明白,他腰上的家伙是手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崔世林,现在看,他就是一个初出茅庐、涉世不深、精力充沛的大男孩儿。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八点钟左右,崔世林穿了件军大衣,心急火燎的来到我家,他气呼呼地说:”处长,怎么把我的枪给缴了,我是用来防身的。”我父亲态度威严,但又诚恳地说:“现在都在收缴武器,你让你的人把没交的枪都交出来吧,要快点……。”崔世林不服气地辩解道:”那他们再打我们怎么办?我们要自卫的”。”扯淡,自什么卫,他们的枪也在收缴,今后绝不允许再搞那些打打杀杀的武斗了。”我父亲严肃的教训他。他们争论好一会儿,最后崔世林垂头丧气的走了。我和我父亲送他到门外,我拉着他衣袖,意思是要打枪,他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完了,枪没了,你打不了枪了。”说完,气呼呼的头也不回的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
1987年夏,崔世林和几个同学到东北推销复合肥,在哈尔滨见到了我爸爸,他们谈了许久,后来听我父亲讲:崔世林”文革”结束后受到了审查,遭了不少罪,但他的问题并不太严重,主要是”文革”初期在学校造反的事,最后处理好像被划成了”三种人”。
崔世林他2006年正常工作到退休。
2018年夏,我请肖南溪大姐吃饭,她叫了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38军政治部的同事5、6个人,其中还喊了崔世林参加。这是我五十年后第一次见到他,除了岁月的刻刀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外,性情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整个晚宴他很少讲话,也不张扬,没有了存在感。吃完饭后我和朱晓斌战友送他回家,在他家坐了一会儿,因为我喝多了,说了什么都忘了。后来我们在微信中经常聊天、问好。我父亲去世时,他还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
退休后,崔世林经常参加红色文化活动,回到他父亲曾经工作战斗的地方讲革命传统,回忆父辈的英雄事迹,他还担任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的副会长等社会职务。2022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76岁。闻此消息,我还挺难过的。
至于与省军区共同发表声明,支持陈伯达的讲话的事,省军区表现的非常的主动积极,他们找到38军首长希望尽快落实上级的指示精神。省军区主要领导兴奋地讲:”解决保定问题,首先是落实伯达同志的指示。为了表示两军的团结,省军区坚决拥护伯达同志这次河北之行一路的讲话,一定要把我们的联合声明写好。”
38军领导的回答很有策略和艺术,他们好像十分真诚地表示说:”声明是要写好,拥护陈伯达的指示也应该,不过声明还是不要在一起写,因为你们的声明是拥护支持,我们是自我批评作检查,让你们跟我们一起吃刮烙,我们真是不好意思和于心不忍啊。”
省军区领导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不好提出来,现在人家自己说了,就立刻顺水推舟地说:”好啊!这是个好办法,反正都是拥护伯达同志,分别声明也一样。”
后来38军写的声明,让一些人如鲠在喉、有苦难言,气的直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