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由于战争、迁徙、赏赐、赠送等多种原因,在制作后可能辗转流传至他人手中,这种现象在古书中常有记载。器主发生变更后,有时器物上原有铭文会被刮磨,或者加刻新的铭文。讨论这种刮磨、加刻现象,对于研究青铜器的先后归属、时代国别、铭文释读等均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借此梳理青铜器的流转方式等问题。
铭文的刮磨、加刻现象较为普遍,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宜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首先,青铜兵器作为战争工具在先秦时期流动性较大,而且兵器铭文刻款极多,这种流动在性质上与青铜礼器存在差异,所以兵器的加刻现象不在本次讨论的范围之内。其次,先秦器物流传至秦汉时期,多被时人加刻铭文,这是由于时代变迁、朝代更替所引起,而本文讨论的器物及铭文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所以秦汉时期的加刻现象也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要之,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铭文的刮磨、加刻现象。
一、金文刮磨、加刻现象的分类
金文刮磨的方式大致有三类:器主名字被刮去、诅咒誓词被刮去、铭文全部被刮去。铭文全部被刮去者无法确知原铭内容,难以深入讨论,本文重点讨论前两种情况。
(一)刮磨器主之名
刮磨器主名字在先秦金文中十分常见。如伯□作尊鼎铭(《集成》[1]2438)云:“伯□作尊鼎,其万年永宝用。”铭文共三行,后两行文字清晰可见,而首行模糊不清,这是由于该行文字被刮磨所致(图一,1)。首字“伯”、第三字“作”、第四字“尊”可据残存笔画辨识,第二字即器主之名难以辨识,因此被定名成“伯□作尊鼎”。从铭文风格看,学术界将此器定在西周中期是可信的。
图一 刮磨器主名字的金文拓本
1.伯□作尊鼎 2.釐姬鼎 3.为甫人盨 4、5.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编镈 6.下寺M3出土飤簠
《陕西金文集成》著录了一件:釐姬鼎[2],器物现藏西安博物院,是近年征集所得。观诸器形,此鼎呈半球形,深腹,三蹄足,口沿下饰两周弦纹,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器。铭文云:“□□作釐姬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图一,2)。铭文中“作”字尚可辨识,但器主名字模糊不清,从铭文拓本不难看出器主名字已被刮去。
为甫人盨铭文(《集成》4406)云:“□□为甫人行盨,用征用行,万岁用常。”从器形上看,盨的时代为春秋早期,该盨是器主为甫人[3]所铸,器主之名被刮去(图一,3)。
一些传世铜器铭文的刮磨比较复杂。从理论上讲,这种刮磨可能是先秦时期器物被埋藏或下葬时便已经存在,也可能是铜器出土后所进行的刮磨或加刻。所以,传世金文中刮磨究竟发生在何时尚需辨析。从金文发现情况来看,清代开始大量出现伪铭,其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所以往往直接伪造铜器及铭文,或者在真器上加刻伪铭,以此来抬高器物价格。若毁坏真器上的铭文,反而使价值折损。所以推诸情理,传世铜器铭文的刮磨多数应在先秦时期。
与传世器物相比,考古发掘所出铜器铭文被刮磨的现象更为丰富。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八件编镈,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其中七件具铭(铭文在镈的钲部、左右鼓部),现择其中之一转录于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择其吉金,自作龢钟。肃肃鎗鎗,嘉平元奏,孔乐父兄,万年无期。□□三寿,其永鼓之,百岁外,遂以之遣。
整理者已经注意到,七件镈钟上钲部的人名均被刮去[4]。其实除了钲部的人名外,鼓部“三寿”之前也有二字被刮磨,七件镈钟的刮磨情况相同(图一,4、5)。“三寿”是长寿之义,见于者减钟(《集成》193)、㠱仲饮壶(《集成》6511)等铭文,“□□”应该也是人名。被刮磨的内容与钲部相同,都是此钟原来的器主之名。后因器物易主,原名遂被刮去。
刮磨现象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所出铜器。下寺楚墓是春秋时期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有铭铜器,其中部分铭文器主名字被刮去,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M1、M2、M3中。例如M2出土了二件铭文、形制、纹饰相同的青铜鬲[5],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前段。整理者公布了其中一件鬲的拓本,铭文云:“□□□自作荐鬲,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其中器主名字被刮去(图二,2),不能按照物从主名的原则命名,故此鬲被称作“荐鬲”。
图二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1.敬事天王钟 2.荐鬲 3.尊 4.下寺M3出土飤簠
淅川下寺M3出土了四件簠,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前段。簠的器、盖均有铭文,铭文共八件,八件铭文中除了最后一组盖铭作“之飤簠”外,其余七件铭文内容全同:“□□□□自作飤簠,子子孙孙永保用之。”[6]这些铭文中器主名字全部被刮去(图一,6;图二,4)。所以这组器物无法根据器主定名,而被称作“飤簠”。
淅川下寺M1出土八件具铭钮钟,时代为春秋晚期前段,其中五件涉及器主名字[7],但这五件编钟里器主名字都被刮去。以其中一件铭文为例(图二,1),铭文云:“唯王正月初吉庚申,□□□□自作詠铃,其眉寿无疆。敬事天王,至于父兄,以乐君子。江汉之阴阳,百岁之外,以之大行。”由于器主名字被刮去,所以学术界称之为“敬事天王钟”。
在已发掘墓葬中,铜器被刮磨数量最多的就是淅川下寺楚墓。赵世刚指出,在出土的一百一十三件有铭铜器中竟有十七件铜器上的铭文或被全部、或被部分刮去,占有铭铜器总数的15%[8]。这个比重是相当大的。对于铜器铭文被刮磨的原因,赵世刚认为可能与楚国贵族之间的斗争有关。淅川下寺M2墓主是楚国令尹子庚,而M1、M3的墓主为子庚的配偶。令尹子庚是楚庄王之子,而楚庄王曾伐灭若敖氏。所以他认为楚庄王灭若敖氏之后得其家资,并分给儿子子庚,最后随葬于墓中。之所以要刮去器主的名字,主要原因是蔑视该族之意[9]。按:赵世刚认为刮磨器物是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这个判断方向是可信的。但认为这些器物源自与楚庄王斗争失败的若敖氏,现在还无法证明。至于作器者名字被刮去,虽掺有对敌人的蔑视之意,恐怕更多还是欲去除原器主的痕迹以明确新的归属。
(二)刮磨诅咒誓词
刮磨现象中除了刮磨器主名字外,还存在特殊情况。君鲜鼎出土于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M22[10],此鼎折沿,圆腹,三蹄足,一对附耳,口沿饰窃曲纹,腹饰垂麟纹,从形制上看是春秋早期器(图版壹,1)。鼎腹铸有铭文,整理者所附释文如下:
图版壹 存在刮磨或加刻现象的铜器与铭文
君鲜作其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用之。其或隹□,则明殛之。
整理者将“隹”后一字以阙疑处理,同时怀疑该字可能是“丧”字,并推测说:“从残留笔画看可能是’丧’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器物丢失,就要受到惩处。总之仍然是希望子孙永远保有、勿丧勿亡。”按:铭文清晰部分的释读不存在争议,关于“隹□”二字的释读从字形和文意上看,十分可疑(具体考释详后文),但整理者对文意的把握是可信的,此句是说如果子孙将器物遗失,会遭受惩罚,属于诅咒类誓词。此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铭文中“隹□则明殛之”六字被刻意刮磨(图版壹,2),整理者对此曾有介绍:“’或’字以下诸字经过打磨,不甚清晰。”此句是原器主“君鲜”所作的诅咒之词,那么刮磨者显然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剔除此内容。此鼎为君鲜所作,大概传至其后人手中,使用者担心因器物脱失而受到诅咒,便刮削了铭文中诅咒的内容。
君鲜鼎出土于郭家庙墓地M22,墓中同时还出有伯盘,整理者根据墓葬没有出土兵器和车马器认为墓主为女性的可能性较大,并云:“这件君鲜鼎显然是拿别国的铜器来陪葬的。”[11]其说可信,君鲜鼎既然是来自他国的随葬之器,说明此鼎已从君后人手中流转到了别处,这与铭文中“子孙永用之”的期望相左,所以铭文中诅咒誓词才会被刮磨。总体而言,含有诅咒誓词的铭文数量并不算多,而刮磨誓词的现象则更为少见,此鼎值得重视。
铭文的刮磨方法可大致分为利器刮削和锐器錾戳两种。赵世刚认为下寺楚墓铜器“刮去铭文的方法有两种:最常见的一种是用刀或其他利器,在所需去掉的铭文上下或左右刮削,直至笔道刮平为止,此种方法常在铭文部位留下弧形浅凹槽;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尖锐的工具在铭文部位凿出麻点,从而使铭文模糊不清”[12]。按:由于著录方式的改进,现在能够看到更多清晰的铭文照片,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刮磨方法基本与赵说相合。需要补充的是,用利器刮削者还可在其上部加刻新的铭文;而以锐器錾戳者则不利于加刻新铭。
(三)刮磨并加刻铭文
一些青铜器铭文被打磨、刮平后会在同一位置上加刻新的铭文。西周晚期的成钟即属此例。成钟出土于陕西宝鸡西秦村青铜器窖藏,曾被宝鸡市文物商店购得,后来为上海博物馆购藏。钲部、鼓部共有铭文三十三字:
唯十又六年九月丁亥,王在周康夷宫,王亲锡成此钟,成(引者按:以上刻款)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引者按:以上铸款)。
钟铭十分特别,其中前三行二十二字是刻款,而鼓部后三行十一字是铸款。并且刻款和铸款可接续连读。此钟最早由陈佩芬公布,其云:
此钟在钲部和鼓左部原铸有铭文。从实物上观察,钲部中间突起,两侧明显凹陷,并留下原有铭文的模糊笔迹,如钲部的左面上角“在”字竖画两旁有“八”痕,……这一现象估计是器主成将钲部的原铭刮去,又在原处刻上铭文。因原钟铭字数较多,所以钲部两行铭文起首两字都刻在钲部之巅。……另外,“此钟成”三字只能挤刻在鼓左原铭文的右面。这样,刻铭与原铸铭文才能通读[13]。
此段所论十分细致。通过成钟的清晰照片,再结合铭文拓本(图三,2)[14],不难看出钲部两侧的刮磨痕迹和残留笔画。加刻铭文中“王亲锡成此钟”一句交代得十分清楚,此钟由周王亲自赏赐给成,这与多数铭文所载周王赐金、赐贝后受赐者单独铸造器物的情况不同,铭文记载周王把这件已经铸好的钟直接赐给成。成收到赏赐后,便铲掉钟钲部的原有铭文,并在同一位置加刻新铭,致使此钟原来的器主已不可知。“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为原来铸款,这些字之所以未被刮去,是因为这些内容并不体现钟之前的归属。所以,被刮去的内容应当是这件钟原来的制作者及相关信息。成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宣扬周王赐赏所带来的荣宠;另一方面也是尽量剔除上一任器主的信息,从而使器物彻底归属于自己。关于成钟的时代,陈佩芬认为属于西周晚期,而李学勤认为其在厉王时期[15]。由于铭文是后来加刻,所以钟的制造时间应较加刻铭文的时间略早一点。
图三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1.晋侯稣钟第1钟 2.成钟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还出土有九件鄱子成周钟,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其中编号P9、P10两件编钟铭文内容有“鄱子成周,择其吉金,自作龢钟”。铭文为铸款,可见这两件钟原本便是鄱子成周所作。但是编号P11(图版壹,3、4)和P12两件钟上“鄱子成周”四字均是刮去原来的铭文后又重新加刻的[16]。以此观之,这两件钟原来可能为他人所有,后来才归属鄱子成周,于是他刮去原铭,同时加刻自己的名字。这组编钟铭文情况较为特殊,从形制上看,九件编钟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看似原本属于一套,但根据铭文内容可知,它们来自不同的组合。
传世铜器中也存在刮磨并加刻的现象。尊铭文(《集成》5908)云:“作厥皇考宝尊彝(图二,3)”。从铭文拓本来看,第一字与其他铭文风格差异较大,《集成》在“备注”一栏中说“第一字系刻款”[17],其说可从。从铭文位置看,刮去的是原器主名字,加刻的“”字是新器主名。再观诸刻铭写法及线条,“”应是先秦时期加刻。从器形及铭文风格来看,此器的时代属于西周中期偏早。
(四)直接加刻铭文
商周青铜礼器铭文大多属于铸款,但也有部分刻款。刻铭在商代铜器中便已出现,如殷墟戚家庄M63出土了四件刻铭铜器,分别为鼎、簋、觚、斝,后三器上刻铭内容为“贾箙”[18],属于族徽铭文。这类刻铭与器物时代相近,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差异,较难判断究竟是器物铸造完成之后便刻写铭文,还是从别处获得后再加刻,因此也就无法确定器物是否发生了流动和转移。
此处所谓的直接加刻是指在青铜礼器易主后对本无铭文的器物加刻新铭。这种现象在先秦时期也较为常见,下面仅列举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楚季钟出土于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最早公布在《中国文物报》上[19],随即引起很大反响。钟上有铭文:
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
此铭并非铸款,而是后来加刻而成,从铭文字口上看,錾刻痕迹十分清晰(图版壹,5、6)。钟铭较为特别,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此钟最初为楚季所有,由其后世子孙献给了楚公。那么此钟至少先后归属三个人:一是楚季本人,二是楚季之孙(也可能是裔孙),三是楚公。这是铭文反映出来的信息。而万福垴遗址从规模、出土器物、性质等多个角度来看,都不会是楚公的居地。所以,此钟在归属楚公之后,又流转到他人手中,最后埋藏于地下。
提及加刻铭文,最为著名的便是晋侯稣编钟。这套编钟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8,共十六件,其中十四件流散到香港,后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收藏。而另外二件仍留存墓中,经考古发掘出土。二者正好组合成套,钟上刻有长篇铭文(图三,1),记载了晋侯稣随周王东伐夙夷的史实[20]。这十六件钟的铭文都是刻款,高至喜据合金成分、形制纹饰将编钟分为二型三式,并认为这套编钟不是在晋地铸造,而是来自江南[21]。关晓武从形制、尺寸比值所表现出来的波动性证明高至喜的观点可信[22]。李学勤也认为编钟并非整套一次铸就,而是后来拼凑而成,是从铭文中提及的战事所获[23]。那么,此钟是从敌人手中掳获,后来加刻长篇铭文以彰显晋侯稣的功绩。
直接加刻铭文的现象还有很多,如陈璋方壶铭文是齐国将领在伐燕所获铜壶上加刻而成。而燕王职壶铭文是燕昭王在伐齐时所获铜壶上加刻而成。类似例子还有一些,此不赘举。
(五)保留原铭而于他处加刻铭文
有些铜器本身具有铭文,但后来由于器物易主之后又在其他位置上加刻了新铭。1940年2月陕西扶风法门镇任家村青铜窖藏出土了一件鼎[24],从器形上看是商代铜器(图版壹,7)[25]。鼎内壁铸有铭文:“作父庚。册。”旁边还加刻两行铭文(图四,4;图版壹,8):“唯丁未,……鼎。”由于公布的图版不够清晰完整,加刻内容难以尽释。此鼎本为商代器物,后来刻款铭文为周人所加,出土地点也在周原地区,这件鼎很可能是周人伐商所获(详后文)。商代铜器在周人墓葬、窖藏中出土较为常见,但加刻铭文者并不多,此鼎值得注意。
图四 保留原铭并加刻新铭的金文
1.卫夫人鬲第一器 2.卫夫人鬲第二器 3.卫夫人鬲第三器 4.鼎 5.陈璋圆壶 6.陈璋圆壶(1-4、6为拓本,5为摹本)
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即在原铭的空隙间加刻新铭,通读铭文时需将原铭与新铭接续连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河南濬县辛村5号墓出土的卫夫人鬲,现存三件[26],铭文如下:
卫文君夫人叔姜作其行鬲,用从遥征。
三件鬲铭本为铸款,但是后来加刻了“文君”、“叔姜”四字。其中第一器分别在“卫”字后加刻“文君”,在“夫人”后加刻“叔姜”(图四,1)。而第二、三器因铭文前两字之间距离过窄,而把“文君”二字也挪至“夫人”之后(图四,2、3),但阅读顺序仍应以第一器为准。此器自名“行鬲”,根据学术界近年研究,自名修饰语中含有“行”字往往说明该器是作为陪葬来用[27],吴镇烽就认为卫夫人鬲“其实并不是卫夫人在世时自作之器,而是死后家人用其名义为之铸造”[28]。按:本文观点与此略有不同。首先,这三件鬲铸造较为精美,无法从器物本身看出其为明器;其次,设若此器是卫夫人死后其家人所作,那么死者的身份和称呼应当都是明确的,似乎不应在称谓上出现模糊之处,而且是三件鬲同时出现。此处尝试对这一情况进行探讨。如果三件铜鬲的器主原本便为叔姜,很可能也是其生前所作,大概因为无论是从其丈夫角度,还是从其自己私名角度,铸铭“卫夫人”所指都较为宽泛,所以死后加刻铭文,以明确具体所指。如果铜鬲原本不是为叔姜所作,而器主是其他卫夫人,只是叔姜死后她的后人拿来为她随葬,那么加刻铭文是有意更改器主信息,确定器物新的主人。无论如何,鬲上加刻铭文的目的是要明确器物新的归属是可以肯定的。
1982年2月,江苏淮阴盱眙县穆店乡南窑庄窖藏曾出土一件精美的铜壶,其口沿上刻有铭文(图四,6):“重金[29],受一觳五。”这是典型的燕国计容铭文。除此之外,器物上面还刻有其他铭文,整理者最初公布时介绍说:“圈足外缘铭文二十余字,刻划浅,多锈蚀。”但并未给出圈足铭文的拓本与照片[30]。后来,周晓陆公布了壶圈足外部铭文并对其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此壶共有三处铭文,除了口沿外,圈足内部有一处,约二至四字,但被锐器细细錾戳,已经很难辨识,同时他还公布了铜壶圈足外部刻铭的摹本[31]。《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公布了该壶圈足外部刻铭的最新摹本(《集成》9975;图四,5),较之周晓陆公布的摹本更为准确。现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和本文的理解将铭文转录于下:
唯王五年,郑、陈得再立事岁,孟冬戊辰,大将孤、陈璋纳伐燕胜邦之获[32]。
此器是齐燕之战中齐国的战利品,旧说认为是陈璋伐燕所得,所以目前多将其称作陈璋圆壶。与旧说不同,本文认为此器是孤、陈璋二人所得,两人都是齐国伐燕时的将领,陈璋即齐国大将田璋,见于典籍记载;至于孤所指难以明确,附此待考。此器的特殊之处在于铜壶口沿略向外侈,上面的燕国铭文更加显豁,易被看到,而圈足内部铭文不易被发现,但陈璋等人获得此壶后,在加刻铭文的同时,錾凿了圈足内部铭文,却保留了更为显豁的口沿铭文。推测其原因有二:一是口沿铭文属于计容内容,并未记录器主名字,而圈足内被剔除的文字可能是原器主之名;二是此器过于精美,发掘者赞誉其“精美绝伦”,如果在口沿上錾刻会影响器物的美观。大概是因为这两点,陈璋等人才剔除了更为隐蔽的圈足内部铭文,而保留了口沿上的燕国原刻。
另外,商周铜器上还存在很多刻款铭文,但有些不能判断是否为器物易主后所加刻,这种情况无法直接看出铜器的流动,此处暂不讨论。
二、刮磨、加刻金文的内容研究
上文结合具体实例对刮磨、加刻铭文现象进行了分类讨论。经过辨析可知,存在此类现象的铜器器主大多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些器物本身与后来加刻的铭文在时代、国别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仅仅依据所加刻的铭文来判断,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也使得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器物十分复杂。这类器物的器主、时代、国别、铭文释读等方面需要详加辨析,才能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下面便结合实例对一些复杂情况予以分类研究。
(一)刮磨、加刻铭文与器物的主人
铭文中器主名字若被铲掉,就会抹去器物原来主人的记录,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会随之淹没。有时需要深入剖析、挖掘,才能对作器者的身份进行判断。西周晚期的士父钟现存一组四件(《集成》145-148)。钟铭开篇及中间都曾被刮磨,而且四件钟铭被刮磨的位置是相同的。下面先录写铭文再讨论相关问题:
□□□□作朕皇考叔氏宝林钟,用喜侃皇考。其严在,丰丰,降余鲁多福无疆,唯康佑纯鲁,用广启士父身,擢于永命。士父其眔□□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
观诸铭文拓本(如《集成》147、148),铭文被刮磨的地方共有两处,一处在开端,应是作器者的名字;另一处在铭文后端,位于“士父其眔□□万年”一句中。从位置上看,前者被铲掉的大概是四字,后者应该是二字(图五,1、2)。《故宫青铜器》一书曾收录其中二件编钟的清晰图版,从图版可以清楚地看到铭文中两处刮磨痕迹[33]。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此点,方浚益在《缀遗斋彝器考释》中曾著录二件士父钟,并云:“其阙处凹下有昔人摩砻痕迹,非后来土蚀也。”又谓:“然文中’用广启士父身’一语,乃作器人自谓。”并将钟名定作“士父钟”[34]。郭沫若的观点与此类似:“此钟传世凡三器,凡有人名之处,大抵凿去,仅’士父’二字之一得免于难,疑在古时由贿赂或虏获之故而易主,后之所有者凿去之也。”[35]自此以后学术界多将这几件钟称作“士父钟”。但仔细探求,这种处理是十分可疑的。
图五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士父钟铭文拓本
1.《集成》147 2.《集成》148
铭文第一处被铲去的显然是作器者的名字。至于第二处,“眔”字作为连词,其前后是并列关系,所以被铲掉的也是人名。着眼于铭文整体,前后两处被铲掉的应该是同一人名,如此前后才能相互对应。只是人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共四字;而第二次出现时用简称因而少了两字,这些都是不难判断的。刮磨两处人名是有意彻底清除器物原主人的痕迹。过去将此器定名作“士父钟”主要是依据“广启士父身”一句。但此说可疑,假设作器者为“士父”,那么为何在开篇将其铲掉,而在铭文后部“广启士父身”和“士父其眔”两处又将其保留呢?即使认为这是不小心而遗留也不能成立,因为铭文后面也存在刮磨现象,可见刮磨者是对全篇铭文都有留意的。而且四篇铭文刮磨情况整齐划一,每篇铭文中两处“士父”都被保留。所以,本文认为编钟上被刮去的铭文并非“士父”。
按照通例,西周金文中“广启某身”之“某”多数都是指器主而言,那么这套编钟若非士父所作,制作者必然与士父关系极为密切,最有可能就是士父的夫人。铭文里“士父其眔□□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一句十分关键,作器者将自己置于士父之后,两者共同“万年”,且子孙也是两者共有,所以作器者应该就是士父的夫人。这一点还可通过同类词例加以证明,金文中在“A眔B万年”的词例中,A、B往往是夫妻关系。如:
叔㚤作宝尊簋,眔仲氏万年。 叔㚤簋(《集成》4137)
县妀……我不能不眔县伯万年保。 县妀簋(《集成》4269)
芮伯稽首,敢作皇姊盉,其眔倗伯万年。 芮伯盉[36]
虘眔蔡姬永宝。 虘钟(《集成》88、89)
与上述铭文相类,士父钟里与“士父”并列的应该也是他的夫人。所以钟铭被刮去的应是士父夫人之名,她可能正是这套编钟的制作者。由于她与士父关系紧密,所以在铭文中会使用“广启士父身”的语句。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其名字被铲去,她作为器主的身份也就未被揭示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过去根据早期女性墓葬中很少有钟磬等乐器作为随葬品,有学者认为西周时期女性不能使用编钟等乐器,如印群认为西周至春秋中期随葬金石之乐仍是男性高级贵族的专利[37]。常怀颖对此进行了辩驳,指出西周中期横水墓地M1、张家坡M163两座女性墓都随葬了编钟[38]。但学者对此的认识并不相同,或认为女性墓葬随葬编钟是墓主丈夫或儿子所为,随葬编钟是强调和抬高女子身份。从逻辑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横水墓地M1编钟未铸铭文,而张家坡M163编钟是井叔所铸,很可能是女性墓主死后生者以别人使用的编钟进行陪葬。现在来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争议,是没有找到确定的女子作钟的实例。近年新公布的嬭加编钟出土于湖北枣树林墓葬[39],嬭加是曾公宝的夫人,时代明确,属于春秋中期[40],说明春秋中期已有女子制作乐器并可随葬,这已经说明上引印群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士父钟属于西周晚期,两者相隔不远。如果本文所论可信,士父钟的制作者就是士父之夫人,这为西周时期女子铸造乐钟提供了一个关键例证,也说明西周时期女子可以使用金石之乐[41]。
(二)刮磨、加刻铭文与器物的时代
刮磨、加刻铭文的器物时代较为特殊,铭文反映的时间和器物的制作时间往往不同。如上文所讨论的成钟,铭文是西周晚期(可能是厉王)所刻,但器物肯定较铭文早。类似现象还有一些,如果研究者不加留意,将铭文时代与器物时代等同便会造成误判。
下面讨论一套学术界长期误判时代的器物。曾侯乙墓曾出土一套尊和盘,器物十分精美。盘上带有铭文,一般著录书籍直接命名作曾侯乙盘(图版贰,1),并将释文录作:
图版贰 存在刮磨或加刻现象的铜器与铭文
曾侯乙作持用终。
其实,如此处理并没有体现出器物的复杂性和铭文的原始特征。关于此器铭文,发掘报告曾有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尊盘的盘内底上一圈铭文,原来是“曾侯之□□”六字,后刮去“”及最后二字,但“”字仍依稀可辨认,保留原来的“曾侯”和“之”三字,利用“之”字改刻成“持”字,加刻“乙作”和“用终”四字为“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可知此器原为曾侯之器,后为曾侯乙所有,故改刻了他的名字。从字体风格来看亦显系两人之手迹。前者秀丽,后者恣肆[42]。
从铭文照片来看(图版贰,2)[43],发掘报告的描述客观准确。曾侯乙对此盘的处理值得玩味,其所刮磨之字为“”,是原器主名字。最后二字可能是器物的自名,被刮的原因是此位置需加刻“用终”二字,“……作持用终”的表述是曾侯乙时期铜器铭文最为常见的范式。而“曾侯”、“之”未被刮磨,是因为这与要加刻的铭文内容相关,“曾侯乙”身份亦为曾侯,而“之”字正是“寺”字的组成偏旁。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曾侯乙对于该盘的刮磨与加刻就是要去除器物旧主人的痕迹,进而彰显器物新的主人。关于盘的时代,现在著录书籍根据铭文中曾侯乙字样,将其判定在战国早期。其实,此说并不可信,这是没有注意到加刻铭文的特殊性所致(详后文)。
提到此盘,就不得不讨论与其一同出土的曾侯乙尊。两者组合、配套使用(图版贰,1)。此尊颈部外面刻有铭文:
曾侯乙作持用终。
仅着眼于铭文,此铭为曾侯乙所刻,且又出自曾侯乙墓,所以一直以来都将此器的时代定在战国早期,认为器主是曾侯乙。学术界对此均无异议。但若仔细分析,这一意见恐怕是站不住脚的。此尊与盘的制作工艺、方法一致,形制纹饰、款式风格基本相同,两者是一套器物,彼此搭配使用。据此不难判定,这套尊盘是同时制作而成。根据盘的铭文可知,盘的最初拥有者为曾侯,是在曾侯时期铸造而成。那么这件尊显然也在曾侯时期铸成,我们还可通过分析铭文的制作方式来佐证这一结论。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很多带有铭文,但绝大多数都是铸款。上文讨论的盘是铸款改成刻款,而这件尊则是纯粹的刻款(图版贰,3)[44],这是比较奇怪的。所以不难推断,尊与盘原本都是曾侯所作,只是铸造时盘上铸有铭文,而尊上未铸铭文。这是由于尊盘需配套使用,在盘上铸铭便等于标注了尊的归属。后来这套器物转至曾侯乙手中,曾侯乙便将盘的原铭进行刮磨并改刻,同时对本无铭文的尊直接加刻铭文,使自己成为两件器物的新主人,这也可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物勒主名”了。
再回头看这套尊盘的时代。由于其上面标有“曾侯乙”字样,又出自曾侯乙墓,而曾侯乙处于战国早期,时代明确,所以过去学术界都将这套尊盘定在战国早期。现在明确了这套器物为曾侯所作,而根据文峰塔曾侯墓地,曾侯处于春秋晚期[45],那么这件尊也属于春秋晚期。过去将其定在战国早期,时代判断有误,应加以修正。
判断加刻铭文的器物时代颇为复杂,不宜根据铭文直接判定器物的年代;也不宜根据器物的形制直接判定铭文的年代。建议将两者分别标注,以曾侯乙尊盘为例,盘和尊器物的时代宜定在春秋晚期,而所加刻的铭文宜定在战国早期。
(三)刮磨、加刻铭文与器物的国别
加刻铭文的国别也十分复杂。上文讨论的陈璋圆壶,整理者最初并未公布圈足铭文的拓本与照片。此器出土于江苏盱眙,该地战国时期曾属楚国,同窖藏还出土有战国时期楚国“郢爯”金版,所以学者或认为此壶为楚国器物[46]。也有学者根据壶口沿上的刻铭认为此为燕器。因而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后来圈足外部铭文公布,根据内容可以明确此器本来属于燕国,后被齐国虏获。所以器物本身及口沿铭文应属燕国;而圈足外部铭文属于齐国,应该把性质不同的材料分开判断。
同类材料还有战国时期的平安君鼎。二十八年平安君鼎出土于河南泌阳官庄三号墓[47],鼎身和器盖都有两处不同时期加刻而成的铭文(图六,1),因这是一座秦墓,所以整理者认为平安君鼎为秦器。李学勤反对此说,认为此鼎属于卫国器物[48]。与此相关的是一件传世三十二年平安君鼎,在清代就已经著录,清代陈介祺曾提出三十二年平安君鼎为“周末梁器”的意见[49]。后来学者也多认为两件平安君鼎属于魏器[50],而吴良宝则从文献记载、地理变革等方面对诸说做了全面辨析,他认为在战国中晚期,鼎铭所记的单父一地归属大概经历了“卫(或魏)→宋→齐→魏”的变化,而平安君鼎是卫国或魏国的可能性都存在[51]。可见,学术界对两件平安君鼎国别的判断是存在争议的。本文认为现在仍然应该将器物与铭文区别对待。从形制上看,这两件平安君鼎本身究竟属于卫国还是魏国,尚难论定。但这两件鼎所加刻的铭文应当是魏刻,铭文中“”是典型的魏国容量单位用字[52],所以加刻的铭文应是魏国文字。
图六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1.二十八年平安君鼎 2、3.安邑下官锺
战国时期还有很多加刻铭文的器物国别比较复杂,如安邑下官锺(《集成》9707),该器出土于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53],锺上有三处刻铭:
第一处铭文:安邑下官锺。
第二处铭文:十年九月,府嗇夫成加、史狄校之,大大半斗一溢少半溢。
第三处铭文:十三斗一升。
“安邑”为地名,战国时期曾一度是魏国都城,所以第一处铭文为魏刻(图六,2;图版贰,5);第三处铭文是秦系文字(图六,3),器物又出自秦墓,此铭文是器物流传至秦国之后加刻,学术界对此多无异议。而第二处铭文(图六,2;图版贰,5)过去也被当作是魏国刻铭[54]。但是随着新见资料的增多,证明这一认识是有问题的。近些年公布的荥阳上官皿中校量铭文与安邑下官锺第二处铭文几乎全同,李学勤据此认为安邑下官锺第二处铭文是韩刻[55],其说可信。可见安邑下官锺本为魏国器物,但上面所刻的三处铭文分属魏国、韩国、秦国,器物的国别与铭文的国别不能完全等同。所以,在结合铭文讨论器物国别时,如果铭文为刻款,应当充分注意加刻铭文的复杂性。
(四)刮磨、加刻铭文与文字释读
刮磨现象会导致文字形体不全,若根据残余笔画释读文字容易导致误释。刚刚公布的一件封鼎(图版贰,4),从形制上看为西周早期器物。铭文下部不够清晰,整理者说:“因字口极浅,无法拓印,湿水后字迹稍微明显一些。”其实观察铭文照片可以看出(图版贰,6),这篇铭文上部字迹清晰,而下部曾被刮磨,导致铭文模糊不清。整理者给出的释文作[56]:
惟十又二月初吉丙申,在井,仲锡封贝,用作宝尊彝。
整理者把“井”字读为“邢”属上读,认为是地名,“中”是赏赐者,读为“仲”表示兄弟排行,在铭文中代表邢仲。按:从断句上看,整理者的解释有可能成立,但是也存在其他可能。这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故此处不赘述。至于整理者所释的“封”字,原篆照片仍能辨析出偏旁和笔画(图版贰,6),整理者摹本作,对此形摹写准确,但释读有误。此形左部下面竖画穿出,而西周金文中“封”字作,左下部从土,竖画都是不穿出的;右部所从并非“又”或“丮”旁,而是“殳”旁。所以无论是着眼于字形的左面还是右面,释“封”说都站不住脚,整理者在文章中说“暂时隶定为’封’”,这说明他们的认识也有所游移。本文认为此形应是释作“”,只是形体右部“殳”旁因刮磨而模糊才导致误释。类似写法的“”字在金文中曾有出现,如学术界公布的几件卫簋,器身、器盖都有铭文,作为赏赐品的“朱亢”一词的“朱”作、[57]、等[58],是借“”为“朱”。妊爵铭文中“”字作。以卫簋、妊爵铭文中“”字与形相比,诸字写法基本一致,可见后者也是“”字。铭文是说井仲赐给“”贝,而“”作了这件宝鼎。所以过去将这件西周早期青铜鼎称作“封鼎”是错误的,其正确定名应为“鼎”。
因刮磨而导致误释的现象还有其他实例。上文讨论过的君鲜鼎铭文如下:
君鲜作其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用之。其或隹□,则明殛之。
整理者所释的“隹”字,字形略有残损,从铭文照片大致可辨析出轮廓(图版壹,2),其与常见的“隹”形相比,明显多出一些笔画,其上部多出三个点画,所以整理者给出的摹本作,将上部摹写成“屮”旁,虽不够精确,但也注意到了“隹”上部有三处笔画。除此之外,在“隹”的下部还有一个“又”形,这从器物的照片和拓本中都能看出。下面结合清晰照片和拓本为此形重新作出摹本。需要注意的是,形并非此字全貌。上文已论,此铭曾经刮磨,整理者曾有介绍:“’或’字以下诸字经过打磨,不甚清晰。”从彩色图版上看,铭文最后两句被刮磨的十分严重,以至于个别文字残缺,形就是被刮磨后剩余的部分。结合形体写法与结构,此形应该释成“夺”字。金文中“夺”字或作(《集成》5331)、(《集成》3372),与此类“夺”字相比,鼎铭所从的“衣”形被刮磨掉,只残留了中间部分,但同时含有“小”、“隹”、“又”三个部件的字并不多见,再结合文意,仍可识出。
将“隹”改释成“夺”后,可训作夺失、脱落。君鲜鼎铭文可与下录金文相互类比:
惟王三月丁丑,大师氏姜作宝盘。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其敢有夺,则俾受其百殃。 太师氏姜匜[59]
太师氏姜匜铭文的“夺”字应训作夺失、脱落[60]。铭文是说如果子孙失去此器,会遭受祸殃。而君鲜鼎铭文中“夺”字用法相同,铭文是说君鲜作铸此鼎,子孙要永远珍用。若有脱失,则会遭受明殛之罚。
(五)刮磨、加刻铭文与校正修补
刮磨、加刻铭文常常是因器物流转所引起,但并非全部如此,面对一些特殊现象还需要仔细辨析,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如铭文的校改与补充。以虘钟为例,此处要讨论的虘钟共五件[61],为了便于比对,现附录编钟的铭文拓本(图七,1-5),同时录写释文于下:
图七 虘钟铭文拓本
1.甲钟 2.乙钟 3.丙钟 4.丁钟 5.戊钟
唯正月初吉丁亥,虘作宝钟,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乐好宾。虘眔蔡姬永宝,用邵大宗。虘钟甲(《集成》88)
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乐。虘钟乙(《集成》89)
唯正月初吉丁亥,虘作宝钟,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乐好宾。虘眔蔡姬永宝,用邵大宗。虘钟丙(《集成》90)
好宾。虘眔蔡姬。虘钟丁(《集成》91)
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考釐伯龢林钟,虘眔蔡姬永宝。虘钟戊(《集成》92)
五件编钟里除了乙钟铭文不全外,其他钟铭文都出现了“虘眔蔡姬永保”一句。其中甲器铭文“眔蔡姬”三字风格与其他铭文区别明显,应是后来刻款[62]。清人刘心源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云:“’永’上三字,篆迹窳劣,疑后人补镌者。”[63]陈昭容说“’蔡姬’明显是将原来铭文刮去后原位加刻”[64]。
根据甲钟的刮磨、加刻情况,容易得出此钟与同组其他编钟最初并非一套而是后来拼凑而成的结论。那么甲钟应该是虘为另一夫人所作,后来这位夫人名字被改成“蔡姬”,又重新进行了编组。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也可能原来甲钟此处就是“眔蔡姬”三字,只是铭文铸坏或铸错,后来又将坏铭铲平,重新加刻这三个字,属于铭文修补。那么哪一种推测更接近事实呢?
观诸形制方面,对比原器形可知,甲、乙、丙、丁四件器更为近似:其纹饰相同,基音点标志都是圆涡文。而戊器的基音点标志是鸟纹。从铭文内容上看,前四器都是为“追孝己伯”而作;而戊器是为文考釐伯所作,“虘眔蔡姬永宝”的位置在钟的甬部。所以这五件钟原来至少应该分成两组,即甲、乙、丙、丁四件原为一组,戊属于另一组。前一组里甲钟与其他三件形制一致,铭文内容相同,看不出明显差异,这四件钟原本应当就是一组。那么甲钟铭文里“眔蔡姬”三字,虽是刮削后补刻,但未必涉及到器物流动,很可能原铭文此处制造时存在坏损或误铸,后来被刮磨并改刻,这似可看作金文中的“校正修补”,值得日后留意[65]。这也提示我们在遇到刮磨加刻铭文现象时,应当充分注意此类情况。
(六)刮磨、加刻铭文所体现出的时代、器类差异性
时代差异方面,本文对先秦时期青铜礼器中刮磨、加刻现象进行了排查,发现这种现象在商代出现极少,而主要存在于两周时期。对比两周时期,数量方面东周较西周呈大幅增多趋势,这与两周时期政治格局变化关系密切。自春秋开始,周王室影响日渐式微,而诸侯国的权力逐渐扩大。诸侯之间相互征伐是常见现象,战国时期则出现了诸国混战局面,领土变更、财货流动较西周时期更加频繁。从诸侯国内部来看,各个执政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剧烈,相互倾轧,覆宗灭族的情况屡见不鲜,器物的易主也就更为常见了。总体而言,铜器铭文的刮磨和加刻现象数量上的变化与社会结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器类差异方面,经过排查可知,食器、酒器、水器、乐器都存在刮磨和加刻现象(相关资料见附表)。细加统计,诸类器物里青铜钟的刮磨和加刻现象最多,如上文已经详论的敬事天王钟、成钟、楚季钟、鄱子成周钟、士父钟,还有蔡侯申编钟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值得探究。一方面,从典籍和铭文来看,青铜钟的流动是比较大的。如《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郑人所贿赂的器物除了车马兵器外,就是乐器,包括编钟与编镈等,而晋公又把其中的一半分给了魏绛。在这一次记载中,乐器就易主两次,流动甚为频繁。金文中所见赏赐青铜器的现象,也是以编钟为多。如:
锡汝圭瓒一、钖钟一肆、鐈鋚百钧。 多友鼎(《集成》2835)
锡汝戈琱□柲彤緌、干五钖、钟一肆五金[66]。 簋(《集成》4311)
锡汝马乘、钟五金。 公臣簋(《集成》4184)
铭文中还有其他类似记载。这说明两周时期青铜编钟常被用来赏赐、赠予,流动性较大。另一方面,钟镈在青铜器中也有其特殊性。两周时期人们非常重视礼乐文明。在祭祀、宴享等场合常常会使用乐器。在时人的观念中,乐器是连接自己和祖先的桥梁,所以钟铭常云:用追孝(昭格)喜侃前文人,前文人严在上,降余多福。“前文人”即前辈祖先,器主认为通过钟乐可以感通、喜乐祖先,祖先也会赐予福禄。试想,如果某位祭祀者使用的乐器来自他人,上面还铸有他人名字,那么从形式上讲祭祀者所“昭格”、“喜侃”的便是别人的先祖,这显然令人无法接受。所以钟铭里面器主名字被刮磨也就不难理解了。
战国时期青铜容器中还存在很多计容、计重铭文,这些铭文中有一些是后来加刻而成,这种现象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原器铸造完成后随即加刻,铭文所反映的是器物原始面貌;另一类则是器物产生了流动,或者国别、或者时代发生了变化,在新的体系下铭文无法反应出准确的容量或重量,要对器物进行校量,需按照新的校量结果加刻铭文,才能便于时人使用。后一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前文已经提到的安邑下官锺便属于这类现象,与此相似的还有三年垣上官鼎[67],鼎的器身加刻了校量铭文:“三年已校,大十六斞。”[68]从铭文风格和用字上看,校量内容应该也是韩刻。还有一些战国时期六国器物,后来流转至秦国,被重新加刻了校量铭文或置用地信息,这是金文中常见现象,毋庸赘述。
三、刮磨、加刻现象与青铜器流转
铭文的刮磨、加刻与铜器流动关系密切,可以此为切入点,再结合传世典籍、金文内容等资料对铜器的流转方式加以探讨。事实上,过去已有学者从考古学角度对青铜礼器的流转方式进行过总结[69],本文与其角度不同,所得出的流转方式也不尽相同。
(一)战争中的捷获
战争俘获是青铜器流动中的常见现象。《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左传·庄公二十年》:“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吴大子诸樊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孟子在批评齐宣王伐燕时也云:“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而文献中将这种现象称作“掳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而却。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湣王出亡,……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张守节《正义》曰:“卤掠齐宝器也。”读“卤”为“掳”,是掳略其他国家的器物。陈璋圆壶、陈璋方壶、燕王职壶都属于此类情况。上文所论淅川下寺楚墓出土众多被刮磨的青铜器,赵世刚认为这是楚国贵族之间的斗争所引起,如果此说可信,这则属于掳略本国内部政敌的器物了。关于斗争虏获器物的情况典籍记载较多,出土铭文中也有所反应,我们曾在两篇小文中略有介绍[70],此处不再赘述。
(二)祖先的遗留
两周时期为世袭制,子孙在继承先辈职事的同时也承袭他们的家资,而青铜器是家族身份、权利、财富的象征,自然也会世代相传。所以金文中“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勿丧”之类的套语极为常见,都是器主强调后辈要珍爱器物,永承祖业。而考古发掘的墓葬或窖藏中往往会出现某个家族从早至晚的器物。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铜器窖藏出土有铭青铜器数十件[71],根据铭文可以判断出折、丰、墙、为依次承袭的四代人,他们的铜器出自同一窖藏,说明这些器物被世代相传。类似的情况还可举出扶风强家村窖藏[72],据铭文可知师载、师望、即、师臾为前后相袭的四代人,其中三代人的器物也出自同一窖藏[73]。这与庄白一号窖藏的情况是类似的[74]。
前文所论被加刻铭文的楚季钟,本为楚季所有,后流传到“厥孙”手中。曾侯乙墓出土的尊和盘本为曾侯所有,同样流传至曾侯乙手中,都是祖先器物流传到子孙那里。类似情况还可以举出彭伯壶。彭伯壶共两件,可分别称作甲、乙两器,1974年2月出土于河南南阳西关煤场一座春秋墓葬内[75]。器物内颈和器盖内都铸有铭文,其中甲壶器身、乙壶器身、甲壶器盖三件铭文作(图八,1-3):
图八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1.彭伯壶甲(器身) 2.彭伯壶乙(器身) 3.彭伯壶甲(器盖) 4.彭伯壶乙(器盖) 5.蔡侯钮钟
□□□□□壶,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这三件铭文中的首行五字都被刮去,而只有乙壶盖铭文完整(图八,4),内容作:“彭伯自作醴壶,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对比可知,其余三件被刮去的铭文是“彭伯自作醴”,属于刮磨器主名字现象。与两件彭伯壶出于同一墓葬的还有两件申公彭宇簠,学者多认为此墓为申公彭宇的墓葬,这是可信的。根据形制,彭伯壶的时代应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76],即两周之际。而墓葬的年代却晚于此,徐少华认为应在春秋中期前段,不早于春秋早中之际[77]。所以尽管彭伯壶与申公彭宇簠出自同一墓葬,但是两者却非同一时代的器物,前者要早于后者。彭伯的器物出自彭宇的墓葬,应该不是偶然巧合,很多学者认为彭伯是申公彭宇的先祖[78],此说可信。那么,这两件壶也属于祖先遗留的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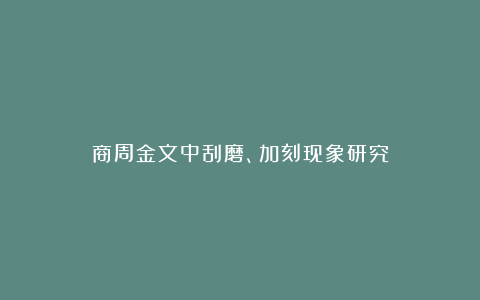
至于彭伯壶铭文为何会被刮磨,王伟认为这与楚国对彭国的政策有关,楚灭彭后并没有毁其宗庙、迁其宝器,彭国因畏惧楚国,所以将标明身份的“彭伯”等字样刮去,以向楚示好[79]。王说较具启发性,但事实是否如此,还无法论定。从前文讨论可知,曾侯乙曾刮去曾侯的名字,两位曾侯之间看不出有何仇恨,而且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其他曾侯的器物,名字并没有被刮去,这说明曾侯乙刮去盘上曾侯的字样而加刻自己的名字,很可能只是强调自己作为器物新主人的身份。与此相类,两件彭伯壶的刮磨原因相同,其中三件铭文的器主名字被刮去,还有一处保存完好,所以可能是彭伯后人只想单纯地去掉之前器主的痕迹而已。
过去在提到刮磨现象时,学者常常会将其与斗争、仇恨联系到一起,即使同一家族内部的器物也多作此解。如蔡侯申墓出土了大量有铭器物,其中圆缶(图九,2)、方鉴、一组钮钟(图八,5;图九,1)、一组编镈上面的蔡侯之名都被刮去[80]。关于刮去的原因,诸家说法不同。如殷涤非认为这些是当时宴会常用之器,文献载蔡昭侯二十八年被人谋杀,这些人杀了昭侯后把他经常用作宴会的器物上面的名字刮去,但还未全部刮掉,内乱便已平息,所以其他器上的昭侯名字被保存下来并随葬于墓内[81]。而李学勤认为这些编钟是蔡平侯的,平侯立而杀隐太子,蔡昭侯又是隐太子之子,故而蔡昭侯与平侯有很深的仇恨,因此刮掉平侯的名字[82]。按:殷说偶然性太大,恐未必符合事实。李说有成立之可能,但亦无法证实。关键问题是被刮掉的铭文究竟为何字不得而知,相应地这几件器物原本究竟为哪一代蔡侯所铸也就无法落实。联系上文所论曾侯乙尊盘的情况,我们认为比较平实的看法是这几件器物应是蔡昭侯之前某一蔡侯所作,后流传至蔡昭侯处,他为了抹去原器主的信息故而将蔡侯的名字刮去,是否与仇恨和斗争有关,现在仍无法坐实。
图九 蔡侯申墓出土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1.蔡侯钮钟 2.蔡侯圆缶
(三)君长的赐赏
《左传·昭公十五年》:“彝器之来,嘉功之由。”为了褒奖下属的功绩,君长往往会赐予青铜礼器。上文提到晋公以郑国所贿赂乐器的一半赐给魏绛,便属此例。此类现象出现极早,西周初年便已存在。文献记载,武王克商后把所俘的商代器物分赐给有功之臣,或称作“分器”。《尚书》本有一篇《分器》专门记录此事,惜已佚失,现仅存《书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周墓葬中出土很多商代器物,学者多归因于“分器”,并对此有专门讨论[83]。前文提到的鼎,本为商代器物,但出土于周原地区,且加刻了西周铭文。颇疑这件鼎也是由于“分器”所致,该器原为商代贵族所有,武王克商后,将其分赐给参与伐商的将士,自此归属周人,并被加刻周代铭文。
两周铜器上常常铸有赏赐铭文,在众多赏赐品中青铜礼器的数量相对少见,以至过去很多研究者认为赏赐品主要是“圭瓒、舆服、兵器、土田、臣民,而不是青铜礼器”[84]。事实上,青铜礼器作为赏赐品在金文中也有出现,上文已经略述赏赐青铜钟的例子,下面举出一些其他礼器。如史兽鼎(《集成》2778)记载尹赏赐的物品为:“赐方鼎一。”小臣逋鼎(《集成》2581):“小臣逋即事于西,休仲赐逋鼎。”鼎(《集成》4119)记载云:“赐鼎二。”这些都是上级赏赐下属青铜礼器的例子。这些例子似与“器不假人”的观念相矛盾,实则不然,遍查两周金文资料,赏赐青铜礼器的例子甚少,不足以颠覆“器不假人”的传统认识。而且,这些铭文中赏赐的礼器存在其他解释。本文认为这些作为赏赐品的礼器并不是赏赐者自己所作的器物,而是另有来源。《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晋侯染疾,子产谏言后晋侯疾病日渐痊愈,晋侯则“赐子产莒之二方鼎”。杜预《注》:“方鼎,莒所贡。”可见赐赏的青铜鼎是莒国所贡之器物。《左传·襄公十九年》:“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是鲁襄公送给荀偃的鼎来自吴国寿梦。两周赏赐金文中也存在内证,如师隹鼎铭文(《集成》2774):“王母赏厥文母鲁公孙用鼎。”铭文记载十分清楚,赏赐给文母的是“鲁公孙”所用之鼎,也是来自他人,而非王母自己。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证明金文中所记赏赐的青铜礼器并非赏赐者本人所作器物,而是源自他处。
结合铭文的刮磨、加刻现象来看,上文所论成钟记载周王赏赐给成青铜钟,而成将上面原有部分铭文剔除,再加刻新铭。其实不难推断,周王所赐的青铜钟也不会是王家之物,应当是取自别处。设若该钟本是周王所作,按照惯例原来钟铭应记载了器物的制作情况,那么对于成来说,受赐王室之器,是极大的荣耀,他不会把原来记载周王作器的内容铲去,只需在其他部位加刻新铭即可,如此处理更能彰显其功勋与荣耀。所以此器应当是周王以他处所得来的编钟赏赐给成,成刮去原铭,加刻新铭以记录并彰显功绩。
战国时期的加刻铭文也有体现君上赏赐的例子。1997年河南洛阳市针织厂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器物上带有刻铭,其中一件青铜鼎(器盖对铭)、二件青铜盉、一件玉鼎上面都加刻了“公赐鼎”字样(图一〇,1、2)[85],说明这些都是“公”赏赐给墓主人的器物。学者或怀疑这几件器物是西周君的赗赠[86]。需要注意的是,这件青铜鼎出土时内有残存羊骨、猪骨,这说明器物在入葬前还被使用,所以也有可能是公在墓主人生前赏赐给他铜鼎,墓主人加刻铭文并使用,同时把“公赐鼎”这件事记录在青铜盉上,其亡故后这些器物也一同下葬。无论如何,从加刻铭文来看,这件鼎是公所赐予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赏赐铜鼎的一个实例。总之,赏赐是青铜礼器的流动方式之一,只不过用作赏赐的器物大多来自他处而已。
图一〇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1.公赐鼎 2.公赐盉
(四)敬献与赠送
除了君长对下属的赏赐,还有下属对君长的敬献。《左传·昭公十五年》:
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
是周王与荀跞饮宴,使用的正是鲁国所进献的壶,周王借此责问为何唯独晋国没有进献器物。这是典籍中关于“献器”的直接记载。而金文中也有一些记录,例如两件琱生器铭文云:
唯五年正月己丑,琱生有事召,来合事。余献寝氏以壶。 五年琱生簋(《集成》4292)
唯五年九月初吉,召姜以琱生五寻、壶两。 五年琱生尊[87]
簋铭中“壶”是琱生敬献给寝氏的[88];尊铭中“壶”是召姜赠送给琱生的。铭文中分别记载了敬献与赠送铜器之事。结合加刻铭文现象来看,上文所论楚季钟即属于此类现象,铭文记载楚季之孙将先祖的编钟献给楚公,这与传世文献记载是相合的,都是先秦时期青铜礼器流动方式的具体呈现。
赠送是青铜器的流动方式之一。典籍中存在很多以铜器贿赂的记载。《左传·桓公二年》:“(华父督)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所记的即是宋国华父督以郜之大鼎贿赂鲁桓公之事。《左传·成公二年》:“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是齐败于晋后,以纪国的青铜甗、玉器等贿赂晋国。这都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敬献青铜礼器,均属赠送器物现象。从记载也可看出,这些被赠送的器物多数也不是赠送者本人所作,而是来自他处,这与上文所论赏赐情况是相同的。
从考古材料来看,墓葬出土的器物中多数是墓主子嗣所随葬;有的可能是他人所赗赠。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其中镈钟与其他编钟铭文不同,内容作: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可见镈钟是楚惠王熊章赗赠曾侯乙的。与此类似,我们推测现在所见的铭文被刮磨的青铜器,有一些可能就是墓主亲朋僚友赗赠死者的。因为这些器物最终作为他人的陪葬品,故赗赠者将铭文刮去,以抹除器物原始痕迹。包山楚墓出土了赗书类简牍——包山277号竹简和单独一支木牍[89],简牍内容记录了墓主人接受赗赠的器物包括车马、甲胄等物品。我们怀疑一些墓葬中出土的部分被刮磨铭文的器物可能有的便属于赗赠品,只是由于出土赗书类材料较少,无法与随葬器物相互印证,故而现阶段尚无法证实。相信随着资料的不断增加,会出现更多明确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赗赠类的青铜器。
上文分类讨论了青铜礼器铭文中刮磨和加刻现象,从微观上看,其关乎铜器的定名与时代、铭文的分域与释读,可以推动并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从宏观上看,这一现象映射了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商周之际的武王克商,到东周时期的诸国混战,很多史实都可从中窥见。我们还可据此现象讨论先秦时期静态的时代特征以及动态的社会结构变化等等,这对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都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附表 铭文刮磨、加刻辑录表
备注:此表主要收录考古发掘出土和部分传世器物,收录之时也考虑了图像的辨识度。还有一些铭文可能有刮磨现象,但是没有足够证据,暂不予收录。表格先后顺序按器物时代排列,同一时代内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的次序排列。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基于金文资料的中国先秦语言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3VRC03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本文简称“《集成》”,后文引用该书时,除了需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情况之外,一般直接给出该书的著录号。
[2]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14册,142、143页,三秦出版社,2016年。
[3]一般认为“甫人”应读作“夫人”。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49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125、12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221-223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81-8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8]赵世刚:《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9]赵世刚:《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博物馆考古队:《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M10、M13、M2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方勤、胡刚:《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博物馆考古队:《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M10、M13、M2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12]赵世刚:《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3]陈佩芬:《新获两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14]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7册,119页,三秦出版社,2016年。
[15]李学勤:《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的两次考验》,氏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53、54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这组编钟铭文情况较为特殊,其刮磨内容较为复杂,整理者曾有介绍:“M1P:13编钟,铭文在正面的钲部和鼓角,其人名三字已被铲掉,背面无铭文。……M1P:15编钟,铭文在正、背两面的钲部与鼓角,钲部铭文多被铲掉,共23字。……M1P:16编钟,正背两面铭文均被铲掉,但隐约可见4字。……M1P:17编钟,铭文全部被铲掉。”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4416页,中华书局,2007年。
[18]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75-7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岳占伟、岳洪彬、刘煜:《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
[19]宜昌博物馆:《宜昌万福垴编钟出土及遗址初步勘探》,《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28日第8版;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第11册,196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文中所用图片采自后者。
[20]马承源:《晋侯穌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21]高至喜:《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年第3期。
[22]关晓武:《两周青铜编钟制作技术规范试探》,《机械技术史》第3辑,2002年。
[23]李学勤:《晋侯苏钟的年代学问题》,《故宫学刊》总第二辑,2005年。
[24]段绍嘉:《对师克盖和鼎铭文鉴别的商榷》,《文物》1960年8、9期。
[25]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4册,96页,三秦出版社,2016年。
[26]三件鬲的铭文分别取自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二),539、538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郭宝钧:《濬县辛村》,图版陆壹,科学出版社,1964年。辛村5号墓为女性墓葬,曾被盗扰,一般认为卫夫人鬲便出自此墓。
[27]杨华:《“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8]吴镇烽:《试论古代青铜器中的随葬品》,《青铜器与金文》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29]李家浩:《谈古代的酒器》,《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
[30]南京博物院、姚迁:《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31]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陈璋圆壶读考》,《考古》1988年第3期。
[32]学术界对铭文的考释意见纷繁,孙刚曾有总结(孙刚:《东周齐系题铭研究》,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在诸说中,本文认为“”读为“将”是正确的;而形,有释“孔”、释“孤”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占主流,本文赞同释“孤”说,“鈛孤”应是人名。铭文最后一句,过去断句和破读也存在分歧,多数人赞同读作“陈璋入伐燕,胜邦之获”,而本文赞同读作“……陈璋纳伐燕胜邦之获”,“纳”字读法可参照鄂侯驭方鼎(《集成》2810)“鄂侯驭方内(纳)壶于王”一句。
[33]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221、222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34]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14册,线装书局,2005年,30页。
[3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本,128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3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物局联合考古队、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158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期。
[37]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2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38]常怀颖:《西周钟镈组合与器主身份、等级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39]关于此钟器主的讨论参李春桃、凡国栋:《嬭加编钟的定名、释读及时代》,《江汉考古》2022年第6期。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2019年发掘收获》,《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
[41]关于此问题,本文定稿后得到学者的反馈建议。首先,审稿专家指出,铭文中“男性器主眔夫人”的表述在当时应是一种习惯,表示礼制所强调的“夫妇一体”,实际上此钟的作器者也可能是男性器主。其次,吴振武师提示笔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即西周时期乐器的制作主体为男性,而士父的夫人作为此套编钟的作器者,行为僭越,因而其名被刮掉,目的是隐藏其作器的行为。按:无论何种原因,此套编钟原本为士父夫人所作,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现将审稿专家和吴振武师的提示附录此处,兼表谢忱!
[42]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18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3]照片采自张昌平:《关于曾侯乙尊盘》,《上海文博论丛》2007年第3期。
[44]照片采自张昌平:《关于曾侯乙尊盘》,《上海文博论丛》2007年第3期。拓本也能看出铭为刻款,参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181、281、282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46]吴蒙:《盱眙南窑铜壶小议》,《文物》1982年第11期。
[47]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泌阳县文教局:《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年第9期;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第10册,426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
[48]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49]陈介祺:《簠斋吉金录》,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16册,线装书局,2005年,25页。
[50]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
[51]吴良宝:《平安君鼎国别研究评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
[52]黄盛璋:《魏享陵鼎铭考论》,《文物》1988年第11期。
[53]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的铜器》,《文物》1975年第6期。彩图选自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10册,110页,三秦出版社,2016年。
[54]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古文字研究》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
[55]李学勤:《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钟》,《文物》2003年第10期。
[56]任雪莉、董卫剑:《新见封鼎小考》,《文物》2021年第10期。
[57]张光裕:《乐从堂藏㺇簋及新见卫簋三器铭文小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58]吕章申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87页,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年。
[59]湖北省博物馆:《晋国宝藏:山西出土晋国文物特展》,92、93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60]拙文:《太师氏姜匜铭文释读》,《古文字研究》第31辑,中华书局,2016年。
[61]《陕西金文集成》另著录一件虘钟,因图版不够清晰,该钟的流传情况不详,故此处暂不讨论。该钟图版参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5册,563页,三秦出版社,2016年。
[62]此处顺便提及,甲钟甬部略有倾斜,容庚认为是“甬稍右倾乃后补”,参容庚:《商周彝器统考》,3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63]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13册,线装书局,2005年,290页。
[64]陈昭容:《周代妇女在祭祀中的地位——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一)》,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65]前文讨论的鄱子成周钟的刮磨现象,也可能属于校正修补行为。
[66]其中“金”是钟的量词,相关考释参张亚初:《金文新释》,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
[67]蔡运章、赵晓军:《三年垣上官鼎铭考略》,《文物》2005年第8期。
[68]吴振武:《关于新见垣上官鼎铭文的释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裘锡圭:《谈谈三年垣上官鼎和宜阳秦铜鍪的铭文》,《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
[69]袁艳玲:《周代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动》,《考古》2009年第10期。
[70]拙文:《太师氏姜匜铭文释读》,《古文字研究》第31辑,中华书局,2016年;《自钟铭文补释——兼说掳器》,《古文字研究》第30辑,中华书局,2014年。
[71]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72]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
[73]其中师望所作的器物为传世品,据铭文内容可与其他三人系联。
[74]两个窖藏世系关系可参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
[75]王儒林、崔庆明:《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尹俊敏:《〈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补记》,《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
[76]尹俊敏:《南阳出土的彭伯壶》,《文物》1997年第12期。
[77]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3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而亦有学者认为应属于春秋早期,最迟也不会晚于春秋中期(王儒林、崔庆明《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78]张丹:《楚彭氏家族研究》,《珞珈史苑》201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79]王伟:《从彭伯壶看古代彭国》,《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80]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8-10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八,5采自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二),378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九采自《集成》211、9994。
[81]殷涤非:《蔡器综述——兼论下蔡地望》,《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
[82]李学勤:《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
[83]黄铭崇:《从考古发现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现象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的类型与阶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三本第四分、第八十四本第一分,2012、2013年。
[84]袁艳玲:《周代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动》,《考古》2009年第10期。
[8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针织厂东周墓(C1M5269)的清理》,《文物》2001年第12期。
[86]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5月,159页。
[87]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扶风县博物馆:《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8期。
[88]敬献铜壶的例子还可举出鄂侯驭方鼎(《集成》2810),铭文云:“王南征,伐角、僪,唯还自征,在坏,鄂侯驭方纳壶于王。”是鄂侯驭方敬献壶给周王。
[89]陈伟:《关于包山楚简中的丧葬文书》,《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90]罗振玉谓此簋“与前器文同而多磨灭”,详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45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