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的“胡不与之国“考析
——探索华夏远古文明边缘的历史记忆
姜里洲
《山海经》作为我国先秦时期集地理、神话、民族志于一体的综合性文献,其价值远不止于表面所见的“志怪”特征。这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奇书,实际上保存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夏先民对周边世界的认知体系。其中《海内南经》记载的”有胡不与之国”,以其独特的否定式命名方式和鲜明的文化特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远古时期华夏边缘族群关系的窗口。
从文献生成的角度来看,“胡不与之国”的记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记忆。这个称谓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文化编码——”胡”指代北方族群,在甲骨文中已有雏形;”不与”则反映了某种特定的交往状态;而”国”的称谓则表明其已被纳入当时的天下体系认知。这种命名方式与《左传》记载的”不羹”、《国语》中的”不屠何”等形成系列,共同构成了先秦时期华夏族群对”他者”的认知范式。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我们得以用“四重证据法”重新审视这一记载。甘肃马家塬战国戎人贵族墓出土的”胡化”车马器,既带有草原风格的动物纹饰,又采用中原工艺制作,生动诠释了”不与”表象下的文化互动实质。新疆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文化的青铜器,则展示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欧亚草原与中原地区的技术交流。这些物质遗存表明,《山海经》的”荒诞”记载背后,往往隐藏着真实的历史内核。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突破传统文献学的局限,整合考古学、语言学、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证据;其次,将静态的文本考据转化为动态的认知史研究,探索“胡不与”观念的形成过程;最后,通过跨文明比较,揭示古代中国族群认知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我们相信,这一研究不仅能够还原一个远古方国的历史真相,更能深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理解。
通过对“有胡不与之国”的系统考辨,我们最终要回答的是:在华夏文明形成的宏大叙事中,这些被标记为”不与”的族群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的历史命运又如何映照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特质?这些问题的解答,将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新的思路。
一、文本溯源与历代注疏的深层解读
(一)原始文本的语境分析
《山海经·海内南经》将”有胡不与之国”与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置西北的记载,体现了战国时期华夏士人的空间认知框架。这种排列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遵循着特定的政治地理逻辑:从已知的匈奴(北方强族),到开题(西域古国),再到更具神话色彩的列人之国,最后到”胡不与”,形成一个由实到虚、由近及远的认知序列。这种文本结构暗示,”胡不与”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治实体,又带有某种文化想象成分。
(二)郭璞注的玄学阐释
东晋郭璞“不与其事而自足”的注解,需要放在魏晋玄学思潮下理解。这种解释明显受到《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将”不与”诠释为一种主动的避世态度。郭注的价值在于首次尝试对”不与”进行哲学解读,但其局限性在于脱离了先秦时期的历史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郭璞在注释《山海经》其他类似国名时也常采用这种玄学化解读方式,如将”无肠之国”解释为”道气内充”,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阐释体系。
(三)清代考据学的突破
郝懿行“疑亦国名,其义未详”的谨慎态度,代表了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山海经笺疏》中,郝氏对这类特殊国名的处理显示出方法论上的进步:一方面承认其作为国名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对含义保持存疑态度。这种处理方式比郭璞的过度诠释更接近先秦文献的本真状态。郝懿行对《山海经》中所有以”不”字开头的国名(共7处)都采取了相似的处理原则,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规范性的注释体例。
(四)现代研究的范式转换
袁珂先生“不与邻国交往”的解释,反映了20世纪以来将神话历史化的研究取向。这种解读将关注点从哲学寓意转向实际的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现代人类学色彩。在《山海经校注》中,袁珂系统地比较了”不屠何”(《海内北经》)、”不廷胡余”(《大荒东经》)等类似称谓,指出这些以”不”为前缀的国名共同构成了先秦华夏对边缘族群的”他者”叙事。这一观点为理解早期中国的族群观念提供了重要思路。
(五)命名模式的文化逻辑
《山海经》中“不X”类国名的集中出现,揭示出先秦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编码方式。这类命名往往具有双重特征:
1. 语音层面:可能保留着对原住民自称的音译痕迹(如”胡不与”中的”胡”);
2. 语义层面:通过汉语否定词”不”表达文化区隔(如”不廷”指不朝贡,”不屠”指不祭祀)。
战国楚简《容成氏》中“不与”族群的记载尤为珍贵,证明这种命名方式并非《山海经》独有的文学想象,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认知模式。该简文将”不与”族群与”百蛮”并提,暗示这类称谓特指那些在政治、文化上与华夏保持距离的边疆群体。
(六)注释传统的学术史意义
从郭璞到郝懿行再到袁珂,历代注疏的演变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学术思想的三大转向:
1. 魏晋的玄学化阐释(重义理);
2. 清代的实证性考据(重文本);
3. 现代的跨学科研究(重语境)。
这种注释史的变迁,本身就成为理解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论发展的重要案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代注释者都未否定“胡不与”作为实际国名的可能性,这种共识为今天的考古与历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学基础。
二、历史地理考辨的文献学解析
(一)《山海经》地理叙事的认知体系
《海内南经》将“有胡不与之国”与匈奴、开题之国并列记载的文本结构,反映了战国时期”层递式”的地理认知模式。这种排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方位记述,而是按照文化疏离程度构建的想象地理:匈奴作为北方强敌最为人熟知,开题之国代表西域远邦,而”胡不与”则被置于认知边缘的模糊地带。这种文本构造与《尚书·禹贡》”五服”制度形成呼应,共同构建了先秦时期的”中心-边缘”空间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地形训》对类似族群的记载采用了更为系统的方位划分,表明汉代地理认知已向实证化方向发展。
(二)开题之国的文献互证
《汉书·西域传》关于开题国的记载,需要放在汉代西域知识扩展的背景下理解。班固将开题定位为”西域国也”,与其说是精确的地理标注,不如说是对张骞”凿空”后获得的新知识的整合。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大宛列传》中并未明确记载开题,而《汉书》突然详述其方位,暗示这类信息可能来自西汉中期与匈奴争夺西域过程中获取的情报。文献记载从模糊到清晰的变化过程,恰恰反映了中原王朝对西北认知的渐进式发展。将开题比定为塞种(Saka)的观点始于清代学者徐松《西域水道记》,这种族属认定体现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的考据成果,但也存在将复杂族群关系简单化的风险。
(三)“浑庾”与”胡不与”的语音关联
《史记·匈奴列传》所载”浑庾”的族称考辨,展现了古代音译问题的复杂性。司马贞《索隐》认为”浑庾”即”浑邪”,而清代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提出”浑庾”与”呼揭”通假。从音韵学角度看,”胡不与”(上古音拟构*ga-pɯ-la)与”浑庾”(*ɣuən-ɣĭwo)确实存在音转可能,但这种联系需要放在更广阔的阿尔泰语系背景下审视。历代注家对这类族称的考释往往陷入两种倾向:一是过度依赖音转通假(如清代考据学派),二是机械对应现代民族(如近代某些边疆史研究),这两种方法都难以完全还原古代族群关系的复杂性。
(四)阴山岩画的文化阐释
阴山岩画中游牧民族形象的文献价值,需要结合古代华夏的“图像志”传统来理解。《吕氏春秋·特君览》记载:”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狙。”这种将北方族群动物化的表述,与岩画中突出狩猎场景的视觉表现形成互文。汉代《盐铁论》中”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的记载,同样反映了中原对游牧民族的生态认知定式。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强调”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种文本建构与视觉表现的一致性,说明”胡不与”类族群的物质文化特征在华夏文献中已被高度符号化。
(五)地理认知的文本演变
从《山海经》到《史记》《汉书》的记载演变,展现了三个认知阶段:
1. 神话地理阶段(战国):将远方族群神秘化、怪异化
2. 探险地理阶段(西汉):通过张骞等使者的实地考察获得新知识
3. 政治地理阶段(东汉):为行政管理服务的地理志编纂
“胡不与”从《山海经》的模糊记载到可能对应《史记》中的具体部族,正是这种认知发展的典型例证。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试图将这类古族名与现代地名对应,虽然具体结论多有商榷之处,但其试图连接古今地理认知的方法论仍具启示意义。现代研究应当避免简单的地理比附,而更关注这些记载背后的认知机制和文化逻辑。
三、族称语义分析的深层文化阐释
(一)“胡不与”的语言学解构
“胡不与”这一复合族称的语义结构,体现了华夏边缘叙事的特殊编码方式。从词源学角度考察,”胡”在先秦文献中已形成特定语义场:《周礼·职方氏》”四夷八蛮”的记载中,”胡”特指北方骑射民族;《诗经·小雅》”玁狁匪茹”的”玁狁”(上古音*hram-lunʔ)与”胡”存在语音关联,暗示这个称谓可能源自某种北方族群的自称。而”不与”的否定结构,在《尚书·尧典》”不格奸”、《诗经·大雅》”不显不承”等早期文献中,往往用于描述违背礼制的行为状态。这种语言组合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定位——通过汉语的否定句式将异族纳入华夏的话语体系。
(二)阿尔泰语系的参照意义
将“胡不与”置于阿尔泰语系背景下考察,需要注意古代语言接触的复杂性。《淮南子·原道训》”胡貉不与百产同”的表述,实际上反映了汉代人对语言障碍的认知。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指出:”胡语多倒装,与华言异”,这种观察虽然简单,却触及了语言类型学的核心问题。蒙古语”bui”(不)与汉语”不”的相似性,可能并非偶然对应,而是古代阿尔泰语与汉语长期接触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国语·周语》记载的”戎狄荒服”,其”荒”字(hmaŋ)在音义上都可能受到草原语言影响,这种语言渗透现象为理解”胡不与”的构词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三)否定式族称的政治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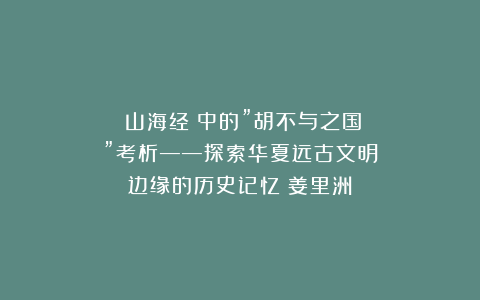
先秦文献中系统出现的否定式族称,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他者”话语体系。《左传》襄公十四年”不羹”的记载,杜预注明确指出:”不羹,楚地,言其不祭祀也”;《国语·郑语》”不屠何”韦昭注:”不屠何,东北夷,不敬王者”。这些注释共同揭示了一个文化逻辑:通过”不+X”的命名方式,华夏作者将异族在礼制(不祭)、政治(不王)、经济(不贡)等方面的差异符号化。这种命名策略与《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的表述一脉相承,都是通过否定性定义来确立华夏的文化优越地位。
(四)语义演变的历史轨迹
从西周到秦汉,“胡不与”类族称的语义内涵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变:
1. 西周时期:作为方国专名(如金文中的”不廷方”)
2. 战国时期:成为文化差异的标记(如《山海经》的命名体系)
3. 汉代以后:演变为政治身份的象征(如《史记》对”不臣”族群的记载)
《说文解字》对“胡”字的解释”牛颔垂也”,已经失去最初指代族群的含义,这种语义变迁恰恰反映了华夏边缘观念的固化过程。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试图还原”胡”的原始语义,但其解释仍受制于汉代的认知框架,未能完全突破文化偏见的局限。
(五)比较视野下的命名政治
对比古代近东文献对异族的称谓方式,可以发现相似的命名政治。亚述帝国铭文中常见的“不服从之王”(LUGAL la mu-kin-nu),与华夏”不廷””不与”的表述如出一辙。这种跨文明的相似性暗示,古代帝国对边缘族群的命名往往服务于中心权力的叙事需要。《春秋》笔法中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与”胡不与”的否定性定义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构成了华夏处理族群关系的双重话语策略。这种策略既保持了文化边界,又为政治整合预留了空间。
四、胡不与国的文化意涵阐释考析
(一)华夷观念的文本建构
“胡不与之国”的记载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话语的建构。《孟子·滕文公上》”用夏变夷”的论述,需要放在战国时期”华夏认同”形成的背景下理解。这种观念在《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表述中达到系统化,构建出清晰的文明等级序列。《虢季子白盘》”不廷方”的铭文(西周晚期),与《诗经·鲁颂》”戎狄是膺”的表述相互印证,表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原王朝就已形成对边缘族群的政治期待框架。值得注意的是,《礼记·王制》将”不火食者”与”不粒食者”并列为化外之民,这种将生活方式差异道德化的倾向,正是”胡不与”称谓产生的思想基础。
(二)文化差异的符号化表达
《山海经》对“胡不与之国”的记载,采用了典型的”异质化”书写策略。这种策略在《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表述中得到强化,将地理边缘(裔)与文化异质(夷)双重他者化。战国时期形成的《禹贡》九州体系,通过”五服”制度(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将”胡不与”类族群定位在”荒服”之外,完成了空间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对接。汉代《盐铁论·备胡》中”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论述,延续并强化了这种将经济生活方式差异本质化的倾向。
(三)现实交往的文本遮蔽
文献记载与物质文化的反差,揭示了先秦族群关系的复杂性。《国语·晋语》记载”戎狄荐处”,韦昭注明确指出这些族群实际与华夏杂居。这种混居状态在《左传》襄公四年”戎狄豺狼”的贬斥性表述中被刻意遮蔽。《战国策·赵策》”胡服骑射”的改革记载,反向证明了所谓”不与”只是相对状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货殖列传》详细记载了中原与边疆的商贸往来,这种经济层面的密切互动,与官方文献强调的文化隔离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不同文本类型对族群关系的差异化呈现。
(四)文化互动的辩证逻辑
“胡不与”现象需要放在动态的文明交流史中理解。《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记载,与《汉书·匈奴传》”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的对比,构建出农耕与游牧的二元对立。但《周礼·考工记》”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的记载,又暗示技术传播的无形渠道。这种文本矛盾恰恰反映了古代中国族群关系的真实状态:官方话语强调差异以巩固认同,而民间实践则突破界限实现融合。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已注意到”外夷风俗虽异,而渐染华风”的历史现象,这种观察为我们理解”不与”背后的文化动力学提供了重要视角。
(五)观念与现实的调适机制
从《山海经》到《史记》的文本演变,展现了华夏族群观念的自我调适过程。《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的记载,显示早期儒家对文化差异的相对开放态度;而《荀子·正论》”诸夏之国同服同仪”的论述,则标志着战国晚期文化边界意识的强化。在这种演变中,”胡不与”类记载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观念的建构——它们既记录了真实的交往状态,又参与了华夏认同的塑造过程。明代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对”华夷之辨”的重新诠释,代表了后世学者对这种文本传统的反思与重构,这种思想史脉络正是理解”胡不与”文化意涵不可或缺的维度。
五、对“胡不与国”在比较视野下的再认识
(一)古代文明的他者叙事比较
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对斯基泰部落“不与外人交往”(οὐκ ὁμιλητικοὶ)的记载,与《山海经》”胡不与”的叙事形成跨文明呼应。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而是古代农耕文明对游牧族群认知的共性体现。《史记·大宛列传》通过”土著”与”行国”的二元分类,构建了与希罗多德”农耕斯基泰”和”游牧斯基泰”划分相似的认知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文献将黑海以北族群统称为”斯基泰”,而《汉书·西域传》将西域各族泛称为”胡”,这种将多样性族群简化的命名策略,反映了古代帝国边缘认知的普遍局限性。古罗马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对北方蛮族的描述同样采用了”不事农耕”(non arant)的否定性定义,与华夏”不火食”的表述异曲同工。
(二)族群分类的认知模式
《淮南子·地形训》将”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各族分别冠以”夷””蛮””戎””狄”的称谓体系,与希罗多德对欧亚族群”四分法”(利比亚人、亚细亚人、斯基泰人、希腊人)形成有趣对比。这种基于方位和生计方式的分类学,本质上是古代文明试图将复杂族群关系纳入可控认知框架的努力。汉代《盐铁论·备胡》中”胡人食肉饮酪”的刻板描述,与希罗多德笔下”饮马乳”的斯基泰人形象惊人相似,暗示古代东西方对游牧民族的认知共享某种原型意象。古波斯贝希斯敦铭文对”不臣服”部落的记载方式,同样显示出与华夏”不廷””不与”类称谓相似的权力话语逻辑。
(三)选择性文化接纳的文献反映
《汉书·西域传》对鄯善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的记载,与同传对精绝国”种五谷”的描写形成对照,这种差异化的记录方式实际上反映了西域各族对周边文明的选择性接纳。《后汉书·西羌传》”羌胡杂处,习俗既异”的记载,暗示了文化接触中的主动调适机制。古希腊斯特拉波《地理志》对黑海沿岸族群”既非完全野蛮,也非完全开化”的描述,与《史记·大宛列传》”颇与中国同俗”的评语共同构成了对文化混合状态的认知。这种文献记载的复杂性,打破了”交往-不交往”的简单二元对立,为理解”胡不与”现象提供了更立体的视角。
(四)文本与现实的解释张力
《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与同书《轻重》篇”胡人不得以为牧”的表述形成微妙反差,这种文本内部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实际族群关系的流动状态。古罗马凯撒《高卢战记》对日耳曼人”不事农耕”的断言与其实际观察到的农业活动并存,同样展现了文献记载的选择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传对”随水草放牧”与”作弓矢鞍勒”并存的记载,突破了早期文献的刻板印象,暗示随着接触深入,对”不与”族群的认知也在不断修正。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西对欧亚草原族群的描述同样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这种认知演变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五)比较研究的理论启示
通过跨文明比较可见,“胡不与”现象的本质是古代文明处理文化差异的认知装置。古印度《摩奴法典》将边境族群定义为”不遵行正法者”(adharmika),与华夏”不臣不贡”的话语如出一辙。这种比较视角揭示:古代文明对边缘族群的”否定性定义”(negative definition)是一种普遍的话语策略,其功能在于维护中心文明的身份认同。但不同文明对这种策略的运用程度各异——与古希腊相对开放的”蛮族观”相比,华夏的”夷夏之辨”表现出更强的文化排他性;而与古印度严格的种姓隔离相比,中国的”用夏变夷”传统又显示出相当的包容性。这种差异正是比较研究的价值所在,它帮助我们既理解人类认知的共性,又把握文明发展的个性。
结语:“胡不与国”的文明史意义
(一)《山海经》民族志书写的双重性
“有胡不与之国”的记载典型地体现了《山海经》作为民族志文献的特殊价值。这部奇书既保存了先秦时期对西北族群的真实认知片段,又系统地构建了一套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编码体系。《左传》昭公九年”戎狄豺狼”的表述与《国语·周语》”戎狄荒服”的记载,共同构成了理解”胡不与”叙事的政治语境。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侍君览》将四方异族描述为”被发左衽”的标准化形象,与《山海经》对”胡不与”的记载形成互文,表明战国时期已经形成成熟的族群表征系统。这种双重性提示我们,早期中国的边疆认知始终在现实观察与文化想象之间保持着辩证张力。
(二)从文本到实践的历史延续
从“胡不与”到魏晋南北朝”五胡内迁”的历史进程中,华夏对边缘族群的认知模式展现出惊人的延续性。《晋书·载记》对匈奴刘渊”汉氏之甥”的谱系建构,与《史记·匈奴列传》”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一脉相承,揭示出古代中国处理族群关系的独特智慧——既通过”不与”类称谓确立文化边界,又借助谱系联结提供融合通道。唐代杜佑《通典·边防典》对”西戎”的系统记载,在方法论上仍可见《山海经》分类逻辑的影响,这种文本传统的持久性,正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生动体现。
(三)文化动力学的现代启示
“胡不与”现象的研究最终指向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文明命题:古代社会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的原则,与《礼记·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的弹性,构成了古代中国族群观念的两重维度。宋代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对”夷夏之防”的强化诠释,与清代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中”天下一家”的构想,展示了这一命题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演绎。这种思想史的流变启示我们,当代跨文明对话需要既承认差异的真实性,又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
(四)神话与历史的辩证认知
《山海经》“胡不与之国”的研究最终打破了神话与历史的绝对界限。正如《尚书·尧典》”宅嵎夷”的记载与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这些看似荒诞的文本往往包含着被文学修辞包裹的历史内核。明代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已意识到”古今语异,方俗称殊”造成的理解障碍,而现代研究的价值正在于通过多学科方法,解码这些古老记载背后的文化密码。从司马迁”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的实地考察,到当代学者对欧亚草原文明的重新发现,对”胡不与”的探索实际上是人类不断突破认知边界的永恒旅程。
(五)中华文明的特质再思
“胡不与”个案研究最终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根本特质。与希罗多德笔下希腊人与波斯人的绝对对立不同,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始终保持着”可变性”——《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的论述,暗示着文化身份的可转换性。这种独特的文明观,使得中国历史上虽屡经族群冲突,却始终保持着文化主体的延续性。从《山海经》的”不与”叙事到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族群关系史,更是一种文明存续的深层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胡不与之国”的研究已超越单纯的古典学考辨,成为理解人类文明共处之道的重要参照。
参考文献:
1. 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2.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
3.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5. 李零《我们的中国》第一编,三联书店,2016年;
6. 《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作者:姜里洲,浔州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