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家的厨房的橱柜里或灶台上瓶瓶罐罐全是各种调味品。炒菜时,辣椒、花椒、葱、姜、蒜要放,酱油、醋、酱料少不了,鸡精味精也要放。
抖音、小视频上教做饭,各种调料齐上阵,“哗 哗”酱油蚝油搞里头,“啪 啪”各种大料搞里头,“刷 刷”鸡精松茸鲜搞里头,好吃难吃不知道,总之就是各种调味品,各种添加剂大聚会。
其实在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厨房的调味品非常简单,除了盐就是从地里拔几根葱、几块姜,剥几颗蒜。自家的花椒树,花椒晒干放石窝里捣碎装在小瓶子里就是炒菜的调和面。要吃酸,一年四季浆水菜、泡菜吃不退,夏天还有西红柿;要吃辣,地里种的有辣椒,青辣椒、红辣椒、辣椒面自产自销。醋一般人家平时不咋吃,来客人了或要吃面皮了,大人有时会打发孩子拿个空酒瓶子去打上半斤或一斤,孩子稀罕,一半走在路上喝了。酱油我小时候都不知道这个调味品,倒是酱,家家夏天都要晒的酱记忆犹新。
小满,家家户户收油菜,收胡豆(蚕豆)。端午节过后,麦子入仓了,秧插上了,家庭主妇开始准备晒酱了。打开胡豆袋子,称上十斤或二十斤,捡去霉颗、土坷垃、沙石,然后开始炒胡豆,小孩烧火,大人翻炒,那炒胡豆的香味飘满院子,不一会青青的胡豆变焦黄了,吃一颗嘎嘣脆,胡豆炒熟了,嘴馋的小孩顾不上烫开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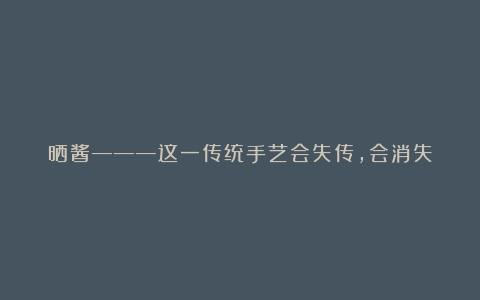
胡豆晾凉后,女主人提到手磨旁,一手放胡豆,一手推磨,让胡豆壳肉分离,变成大大小小的豆瓣,拿回家,簸一簸,筛一筛,取掉胡豆壳,然后浸泡在新挑的井水里。第二天,浅黄色的胡豆瓣泡胀了,控干水分后拌上面粉,要发酵了。男主人忙着折一些香椿树枝叶,女主人把拌上面的胡豆平铺在旧竹席上,上面盖上椿树叶子,再盖上旧棉被。两三天后,豆瓣捂好了,生了一层黄绿色的霉,听母亲说,黄绿色霉就是捂的好,温度控制得好,如果发黑霉,那已经坏了,要倒掉。各家女主人都是凭经验手摸试温度,加被子还是取被子。这时用铲子铲下结成块的霉豆,晾在太阳底下。
入伏前,家家户户要下酱了。晒干的霉豆敲成碎块,取出专门晒酱用的大瓦盆,刮掉去年剩的陈酱,洗净,在太阳底下晒干。先晾上一大桶凉白开,讲究的人家会熬一大锅大料水放晾。(母亲说大料水里不能放花椒,会发霉。)根据盆的大小放豆瓣,按比例加盐,加水,搅拌均匀。最好的晒酱地方就是房顶,没有苍蝇。那时候,修一层楼房的人家也有一些,平坦的楼顶就成了左邻右舍的晒酱场。没有楼顶放,就在院子中间摆个桌子,把酱盆放桌子上。伏天的太阳可毒了,晒上十几天,酱盆不再是清汤寡水,表面一层渐渐变成暗红色了。
下午太阳落山了,各家都会把酱盆盖上,早上,酱盆凉了,揭去盖子,拿竹板搅一搅。天天如此循环,热酱不能搅,雨水不能进。红辣椒收回来了,挑一些没有虫眼的,洗净晾干水份,切碎后再放到石磨上磨得再细碎一些,倒入酱盆里。酱盆之前没有加调料的,有的捣一些草果大香粉加进去,有的把院子里的茴香籽、杆或荜拨秧揪一些放进去,也有剥一些大蒜瓣放进去。放了调料的酱还要继续晒,每天晚上总有家人问“酱盆盖了没”,每天吃早饭时,总有家人问“酱盆揭了没”。夏天暴雨来得快,盖酱盆更是耽误不得,幸好每家酱盆旁都会一直放个盖子,酱盆里有一把竹板,左邻右舍也会帮你搅,帮你揭,帮你盖。
处暑后,有的人家酱已晒好,红艳艳,香喷喷。有的人家觉得酱晒得时间还不够,一直到白露前后收稻谷时才开始享用新酱。晒好的酱连盆放屋里,随吃随舀。也有装上一两瓶送亲戚;邻里之间交换一大碗,看看谁晒得酱又香又红。
在调味品单调的年代,一两盆自己晒的酱就是一家人一年的调味品,汉中熬肉熬菜要用酱上色增香,燣臊子要用酱提色提味。吃菜豆腐时,青辣椒拌酱、韮菜拌酱、芫荽蒜苗拌酱就是最好的配菜。住校的学生带一瓶青辣椒炒酱,一宿舍的人吃得有滋有味,一顿饭,酱辣子瓶见底了。
十几年前,我在城里的小巷子里见到有老人卖捂好的霉豆,家里人少,我打消了晒酱的念头,其实放在阳台上晒酱,免去了盖盆揭盆的麻烦,辣椒也不用切不用手磨,打浆机一会儿就打好了。现在农村也好,城里也罢,几乎没有人晒酱,可能九零后,零零后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晒酱是咋回事,当然也没有吃过纯手工的酱。
终究,晒酱这一传统手艺会失传,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