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明”是华夏文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夏文明”也是连接远古社会“原始文明”与“国家制度文明”的关键节点。
本文并不做学术研究,笔者的本意在于“三星堆”刨开了一个历史的辉煌文明时期,就是“夏文明”,研究“三星堆”的历史意义在于对远古文明的探索更近了一步,“三星堆”是解读华夏文明的重要溯源密码。
历史学界仍处于对“三星堆”属于商周文明的认知阶段,以至于对“三星堆”的历史研究陷入瓶颈,这是对历史及其不负责的。
有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来自埃及文明,其理由是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纵目” 与古埃及荷鲁斯之眼存在惊人的相似性,体现了人类对神圣权力的共同认知,还认为三星堆金杖与埃及权杖都象征宇宙秩序,象牙在两种文化中都代表纯洁,暗示在早期文明两者可能共享某种原始思维模式。
学者刘光保提出“东埃为蜀论”,他认为古埃及祭司集团有组织地迁移进入四川,与当地人一起创建古蜀国,系统性地传播了古埃及文化,这类观点笔者绝不苟同。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发掘的古代青铜、玉器文明具有强烈本土色彩,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分支。基因考古技术显示古蜀先民的遗传标记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族群存在显著关联。
为此,更多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属于中原文化的一个分支,属于古蜀文明。受文化“中原中心论”的思维定式影响,考古界一直认为中原历史文明代表着华夏文明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历来排斥边际文明对“中原中心论”的冲击,认为“三星堆”处于中原文明的地域边际,这是极不合理的。
一、华夏文明是“华胥氏”文明和“夏朝”文明的结合体
“华”与“夏”最初是两个有着某种关联但不完全等同的概念。
“华”的起源一说源于上古部落“华胥氏”(传说中伏羲、女娲的母族,被视为中原族群的远祖);另一说与“花”同源,象征中原文化的“繁荣与文明”(如《说文解字》注:“华,荣也”,引申为文化的兴盛)。
其实我不认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在于,上古部落时期其实还没有“文化”这一说,况且当时的文字其义单一,并不会代表多重意思,“华”就是来自“华胥氏”。
“夏”最早的核心文明指向可追溯到“夏朝”文化的源头,约公元前2070年在大禹成功治水后成为民众首领。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后奠定中原统治基础,其子启建立夏朝。此时的“夏” 首先指代 “夏文明”,是传统意义上“中原地区”(这里的中原地区是后来冠上去的)的主导族群,以及他们建立的政治实体。
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华”与“夏”已常被互换使用,均指向“中原族群”与他们的文化。例如《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孔子之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 “夏” 与 “华” 完全同义,均指中原文明圈层,体现出 “以文化认同来区分族群” 的核心逻辑,而非单纯以血缘关系来进行社会种族的划分,这实际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
由此可以看出,对当时的文化认同仍单纯以“中原族群”文化认知来定义华夏文明,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首先,“华胥氏”文明不仅仅局限在中原族群。华胥氏在八千年前,在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承担起了延续氏族生存的重担,带领远古先民不断的迁徙,足迹遍及黄河流域和其它各地,开创了中国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先河。
有文献记载,华胥氏怀孕期间,由于自然灾害造成食物匮乏,她率领家族部落走出蓝田来到渭河流域,后继续向西迁徙,到达甘肃成纪(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生下了伏羲。
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后,部落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寻找新的食物源地,于是部落内的氏族,有的留居,有的向北或向东发展,华胥带领部落之民向北迁徙,其中一支居于华亭(今甘肃庆阳华池县),逐渐形成新的“部落”。
在大地湾遗址中发掘出半地穴式的方形、椭圆形简陋住房及陶器,说明华胥族人已迁入该地区,或是其文化已影响到今甘肃东南和岑南地区。
同时,其他族群向西(今甘肃中部、西部及青海等地)和向南(今甘肃陇南、陕西汉中及四川等地)迁徙发展。华胥在成纪居住一段时间后,留一部分氏族在此发展,自己便带领一些氏族先民沿渭水东返。陕西宝鸡市发现的距今约8000年的关桃园前仰韶文化遗址,说明华胥族曾迁居于此。所以,华胥氏的活动范围及种族延续并非只局限于中原地区。
有学者认为“华夏”之称直接来源于华胥,中华之称亦然。顾实《华夏考源》一文从文字训诂得出结论:“胥、雅、疋、夏等古字相通,华夏就是华胥。因此可以说,华夏文化就是华胥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就等同于华胥文化。”这一说法非常偏颇,华胥文化并非等同于华夏文化。
华夏文明在历经5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融合了族群、文化、生活、政治、经济、制度等多元文明的社群、阶层、邦交等国体生态结构,远远超出了氏族的界定范围,顾实的结论明显太过狭隘。
华夏文明的联合称谓,最早明确出现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中原族群为强调自身文化的正统性与族群统一性,逐渐将“华” 与“夏”合并使用,形成 “华夏” 这一稳定的称谓。
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 这里的“华夏”已明确指代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与文化共同体,所以“华”与“夏”的早期含义,是从族群标识到文化认同的过程,是伴随上古族群融合、文化认同,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凝固发展为稳定的集体身份符号。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 年—公元前221年),“华夏”的使用更为普遍,成为中原族群对自身文明与地域的共同认同符号,与 “四夷” 的区分进一步强化。
“华夏”文明的形成并非起源于某个具体时间点,本质上是中原文明在与周边族群的权力与文化的角逐中,逐步形成文化认同与族群凝聚的体现,背后有两大关键因素。
一是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强化中原文化认同。周天子权威衰落,周边夷狄族群(如北方戎狄、南方楚国)势力扩张,威胁中原诸侯国(如齐、晋、鲁等)。此时,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以“尊王攘夷”为旗号,联合中原诸国抵御夷狄,这一过程中,“华夏”作为“中原文明共同体”的符号被强化。
二是在诸国纷争中,均以“华夏”自居,将夷狄视为“非我族类”,文化上的共同归属感(如遵周礼、行农耕、用汉字)成为“华夏”的核心标准。
这一时期的《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国语・周语》等文献中,“华夏”已作为整体概念出现,例如“楚失华夏”(指楚国若背离周礼,便不再被视为华夏一员),可见“华夏”已超越单个诸侯国,成为中原文明圈的共同身份。
可见,“中原中心论”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思维体系,以致影响到现在。
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华夏”的范围从原有的中原地区扩展至整个帝国疆域,其含义也从“族群与文化共同体”逐渐演变为对“中国”的代称。此后,历经汉、唐等王朝的发展,“华夏”与“中华”“中国”等概念逐渐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对自身历史与文明的核心认同符号。
二、“三星堆”祭祀坑揭开王朝神权宗庙制度文明
既然华夏文明与“华胥氏”和“夏朝”紧密相连,上古时期华胥氏所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及证据非常有限,那么“三星堆”对了解证实夏朝文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9年春,四川广汉真武村月亮湾村民燕道诚父子在自家院开挖水坑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大堆形制各异的玉石器。这批玉石器包括璧、璋、琮、刀、斧、钏、珠及玉料等共400余件,之后玉石器便流入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从此“三星堆”遗址进入了公众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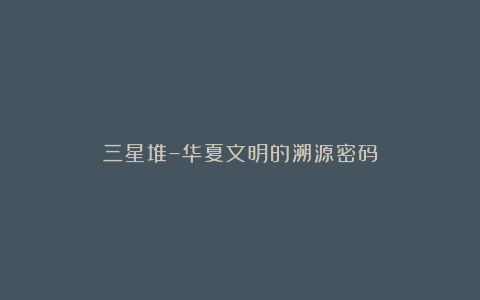
原华西大学地质系任教葛维汉先生对古董有所研究,当看到这些玉石器后,初步认定这些玉器是周代礼器,于是组织了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察。考古队在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石器、玉珠、玉圭等稀世珍宝,后发掘工作因抗战爆发被终止。
第二次发掘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考古队采集了大量石器和陶器标本,根据初步考证,确定该遗址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遗址。
1980年,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对“三星堆”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全面展开,这次出土了不少的陶器、玉器、石器,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基址和四千多年前的墓葬,并将该遗址正式定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6年考古队第五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1275平方米,发现了上面刻有鱼、鸟纹和王者之像的“金腰带”,大量的玉器、象牙、青铜器及金器,以及大量灰坑和房屋遗迹,这些遗迹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上限推至距今5000年。
同年7月18日,发现一号祭祀坑,出土铜、金、玉、琥珀、石、陶等器物共420件,象牙13根。8月14日,距一号祭祀坑东南约30米处发现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金、玉、石等珍贵文物1302件,象牙67根,海贝约4600枚。尤其是青铜器中的各式人头像和黄金面罩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祭祀坑”的首次发掘标志着一个王朝文明及国家祭祀礼制的惊世出现。
2019-202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发现6座“祭祀坑”,截至2022年5月,基本完成挖掘,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包括金面具、铜大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爬龙器盖、铜扭头跪坐人像等典型文物。
“三星堆”文明神秘的历史面纱被逐一揭开,尤其是最近的发掘,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一个神权祭祀、宗庙礼制、人物崇拜及社会等级体系全面展现在世人面前,制度文明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形成,这些都非常明显的共同指向“夏朝”文明。
其理由在于,一个王朝的神权祭祀、人神相通的活动是非常庄严神圣的,夏王朝的祭祀庙堂只能修建在王朝附近。其次,三星堆的金杖、青铜树等代表着权力象征的器物体系、建筑结构和宗教制度并非原始宗教,而是一个早期王朝文明的王统礼制系统。
其次,神树与神坛,连接天地与祖神,青铜神树象征天界道路,神坛与面具是人神对话的载体,这完全契合《尚书》《礼记》中“天子祭天帝”的结构。
第三,大型青铜面具的组合秩序,这些不是图腾,而是王者神祇,祖先神格化,或是夏王朝祭祀尧、舜、禹三帝的神像。
第四,完整的神权宗庙制度,据《大戴礼记》记载:古有“灵府、文祖府、神斗府、显纪府、玄矩府”等五帝天府庙。三星堆很可能承袭并在巴蜀落地了这个庙制,形成王朝礼制的“天帝之府”。
既然这些物证都说明了一个王朝的真实存在,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夏朝初期的建立者大禹与三星堆有着怎样的关系?大禹治水治的是哪里的水?
三、大禹是锚定“三星堆”文明的关键人物
据《史记》《尚书》等权威典籍均明确“禹兴于西羌”,这一说法在汉代以前已形成共识,可信度远高于后世附会的说法。“大禹生于西羌”(核心在今甘肃西南部,或涵盖四川西北部) 是最符合文献记载、且与考古背景相契合的结论。
甘肃洮河流域、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马家窑、齐家文化),在时间、地域上与大禹时代高度匹配,且符合“治水” 的地理背景。
由于上古史缺乏直接文字证据(大禹时代尚无成熟文字),所有观点均基于“文献+考古+传说” 的综合推断,未来随着更多龙山时代晚期遗址(如甘肃临洮 “马家窑遗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或许能为大禹出生地提供更精确的证据。
那么大禹治水治的是哪里的水?最准确的答案就是四川的水。
民科探奇认为就远古时期水利工程和治水而言,位于岷江流域的成都平原各方面条件都优于以中原为代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大禹治水最可能发生的地点。四川宝墩遗址及三星堆遗址,以及都江堰为代表的水网工程与大禹治水时期的历史有着紧密联系。
成都平原存在洪水和治水的考古证据:1. 岷江上游叠溪遗址有4000年前后的人工河道;2.新津宝墩遗址发现防洪土垣;3.郫县古城出土陶制排水管;4.牧马河在3200年前存在人工改道的痕迹;5.金沙遗址发现3200年前的竹笼卵石护岸;5.十二桥文化有系统性洪水淤积层;6.现存最古老的引水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具有灌溉、航运、防洪等多方面长效功能的水利工程。
再对比黄河中下流,二里头遗址(前1800年)仅发现小型排水沟,商代殷墟的洹水治理规模有限,西周洛邑未见大型水利遗迹,这些水利工程都不符合大禹治水的宏大叙事。
传统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李冰父子所修建,但存在很多疑点。李冰在宋代才被封王有没有历史或政治诉求原因?为何南北朝以前都江堰二王庙是杜宇庙?为什么司马迁没说李冰姓李也不提朝代?历史诸多疑点等待考古去发现,到时都江堰的历史地位将被重新改写。
成都平原长期领先全国的最高水网密度,仅靠李冰一任蜀守短短一个任期,而长期处于统一战争中的秦国在四川造就了这样一个千年唯一的神话?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可见都江堰水利工程并非秦朝李冰始䢖,实为大禹的主要功绩。
四川还有很多疑似大禹治水的遗迹,比如重庆铜锣峡存在人工开凿迹像,《华阳国志》记为大禹用铜斧劈开,三峡的夔门鬼斧神工让四川境内的水彻底排到长江中下游,从而减少成都平原的水患,虽有神话加工但最初的来源是否确与大禹相关?都江堰宝瓶口劈山引流的开凿手法与这些遗址的引流方式何其相似。
以上治水案例说明大禹一直在四川境内活动,在四川建立王国也是非常符合常理解释的,成都宝墩遗址就是大禹父亲鲧治水失败的现场之一。
四川宝墩古城遗址,根据碳14测年确定存在于4500至3700年前,是当时全国最大城市之一。宝墩古城遗址在时间上,跨越了大禹治水的时间范围,曾多次毁于洪水,又多次加固防水城墙,最终仍然放弃。这种不断加固城墙仍毁于洪水的情况,与大禹父亲鲧治水失败的记载暗合。
据《史记》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 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鲧因治水失败被处死,儿子禹接着治水,禹在调查上下游情况后新修水利工程,并了解到上游更加安全后,有可能在治水完成的前后,把都城迁往三星堆这个上游地区。都城搬迁后帝王不再住宝墩,于是宝墩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最终于3700年前彻底废弃。
结语:
“三星堆”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的神权祭祀体系是二里头文明所不具备的,它是国家制度文明的象征。
从考古发现中,二里头遗址长期被主流界定为“夏朝晚期都城”,但若从铭文出发则还原出一个更加契合历史逻辑的说法:二里头不是夏人都邑,而是“殷契有方”的殷族初封之邑,是殷人在帝舜时期被赐予的商方国中心,也从侧证证实二里头建邑是早于夏王朝的。
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750—3520年,这与成都宝墩遗址文明荒废的时间3700年差别不大。
这又回到文章前,历史学界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中原中心论”“尊王攘夷”等传统思想,强化中原文化认同,对西部夷族及古蜀文化的排斥,从而认定“三星堆”属于中原文明的一个分支,这就使得夏朝文明至今没有历史溯源基因,岂不是可笑。
“三星堆”祭祀坑独一无二的王朝神权祭祀体系从何而来?“三星堆”如此完整的国家制度体系不是夏朝文明那又属于哪国文明?“三星堆”究竟被谁给全面毁灭?给历史留下这样一个断代文明,等等这些问题的揭秘我们将在下期继续推出《究竟是谁焚毁了三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