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二题
黄国钦
听林墉妙弹
五月的珠江,轻风静静吹来,五羊邨的灯火,在楼房和树梢上朦朦胧胧。在林墉那间点着檀香的画室里,我又好像回到了从前。潮州的木雕、潮州的茶壶、潮州的乡音,还有,那种炉子上咕噜咕噜一丝不苟的潮州工夫茶。
工夫茶是一种道,一种雅,一种闲。一个人端坐在工夫茶炉前,自然就是一种入定,一种静心,一种玄妙。看着眼前抚摸茶壶的林墉,我禁不住想,林墉是一个画家吗?不是!画家是专才。林墉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大大的艺术家。艺术家是通才,文学、美术、音乐、书法、历史、哲学、民间文艺……
林墉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就像他画室里照片上那个握着烟斗永远微笑的黄老头。这个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魅力是童真、童趣、童心。70岁林墉的魅力呢,是反思,是内省,是觉悟。他一个人企在哲学和美学的高处,不懈地思索和拷问。他率真地望着我的眼睛,说:“我搞不明白,为什么美术学院教学生画画是’准确’?!几十年来我一直呼吁应该是’生动’!”林墉这种离经叛道的质疑和大胆的反对立即让我开窍,“准确”是技术,“生动”是艺术,“准确”是肉身,“生动”是灵魂;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准确”,还能叫艺术、还能叫创造吗?
林墉已经进入了他的境界。他说:“现在,艺术界很多人都追求’第一’,这是错的。谁是第一?应该是’唯一’。一字之差,结果完全不一样啊。”我敏感到林墉话里的忧心和忧思,看看当下,社会转型,人心浮燥,商潮滚滚,艺海沉浮……
林墉的“生动”和“唯一”,是他几十年的悟,是他一生的艺术追求和自觉,更是一种普泛的艺术哲学的命题。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唯一”,是一个艺术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迷恋市场,盲目跟风,以相同的风格、用相同的笔法、画相同的题材,“复印”别人,也“复印”自己。看看林墉,他的“农讲所”系列是唯一的,他的“印度、巴基斯坦”系列是唯一的,他的“美女”是唯一的,甚至他的散文语言、散文题材、散文风格,也是唯一的。林墉的“唯一”,对我触动很大。闭起眼睛,叶浅予是唯一的,关良是唯一的,弘一是唯一的……这些忠实于艺术、忠诚于艺术的“唯一”,比起那些追名逐利的“第一”,论资排辈的“第一”,更让人顶礼膜拜,高山仰止。
硕大的画室里,滚水在水壶里咕噜噜地叫着,林墉的话题,却转到了“写生”。他说:“有人把写生夸大到了绝对,夸大到了一辈子的事,这是错的。写生只是一个画家的出发点。画家的生命是创造力。一辈子做’写生’?做到废寝忘食?不可能,这是沽名钓誉。这种人,对着国画家谈油画,对着油画家谈国画,看似好像最有说服力,好像很伟大,很深刻,其实无用。”我知道这个“写生’无用’”的意思,那是反对偏颇、偏激,更是批判肤浅,欺世。就像文学界写文章,素材是出发点,作品才是有生命的;形容词是出发点,有思想有感情有血有肉的故事情节才是持久动人的。
和林墉沏茶,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林墉说:“有人说我没有批判的意识,没有看见现实种种的丑恶,总是在热衷地美’画’(化)。我说,错了。我和你一样,正是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丑,所以,我才在不懈地寻找美,创造美,送给人。”
夜已深,茶还热,坐在林墉的书斋画室里,看着他背后画板上三张四尺拼起来的波涛翻滚的画稿,我的心,和林墉一样,波涛翻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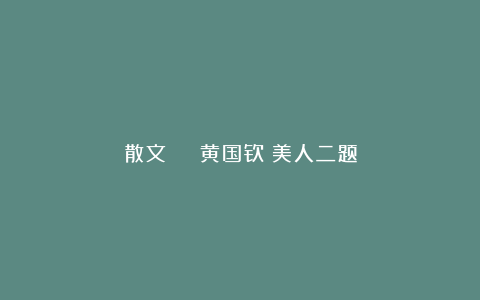
莽园不是园
莽园不是园,是一个人,一个十足的文人。在古潮州这片土地上,能称得上文人的人有好多人,但口才伶俐,妙语连珠,哲理禅意,诙谐幽默,出口能迷住我的前辈呢,不过三个人。一个是我曾经日日聆听的李前忠,一个是声名远播的林墉,一个就是郭莽园。
恰切地说,莽园是一个美人。因为李前忠有语录,写文章的人是文人,画美术的人是美人,跳舞蹈的人是舞人……一个美人,能够迷倒一个写文章的人,你说,他肚子里应该装有什么样的彩墨和智慧?
很多人说莽园是一个孤傲的人,尖刻、自负。我说莽园是一个寂寞的人,尖锐、自信。现在,很多画画的人不读书,从早到晚一支笔,就知道在画案上画啊画,没有学养的滋润,没有传统的熏陶,没有思想的磨砺,没有诗文的铸就。一个学中国画的人,没有学过芥子园,没有学过古体诗,没有学过毛笔字,不知道民国乃至清代以前中国画坛的样子,你说这样的人能画出什么画?
莽园呢?是读书读书再读书,思考思考再思考。他很奇怪,现在美术学院的国画系,为什么不考古文考英文?不考白描考素描?我击掌赞赏他的二句话:真艺术没有雅俗共赏,成功者没有中西合璧。想想是这个道理啊,你不走向极致和极端,你就达不到高峰;你和稀泥,你就什么都不是!
我知道莽园不是故意在孤独,他永远在寻找知音,他一辈子都在寻找知音,但是,莽园的知音在哪里呢?一个寂寞的人,是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想法,有别人没有的追求,有别人无法理解的艺术观和价值观。
在别人眼里,莽园是一个桀骜不驯的老人,那一头蓬乱的头发,那一部须髯飘飘从左腮连到右腮的胡子,就给人一副十足叛逆的形象。我和莽园促膝,却从来没有感到压抑和局促,都感到逸然随意和自由自在。尊重一个饱读诗书个性鲜明创意无穷的画坛前辈,理解一个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笔底不愿意重复自己的率真美人,他能不露出一脸天真灿烂的笑容?
看莽园画画,是一种真正的称心,他总是把一管长锋高高地提到笔端,一只手按在画案上,然后成竹在胸,从容地下笔。这完全不像现在的很多后生哥哥,开头几笔十分架势,但是画着画着,心里无底,画面芜杂,乱象丛生,又不懂得“收杀”,无奈之下,就只好淋水,倒色,把一个画面,弄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最后撕掉了事。
莽园是一个从生活的底层走出来的人,底层的苦难艰辛和穷愁潦倒,底层的人情冷暖和无依无靠,深深地刺激了他独树一帜的雄心和志气,他学习西画又跳出西画,学习海派又跳出海派,一生孜孜不倦转学多师,最终成就了大写意和指书画。我屈指算来,从清光绪三十年到公元2015年,历一百一十一年,大名鼎鼎的西泠印社仅有社员三百几十人。但是莽园,一个西泠印社的社员,就是这样给艰难困苦的生活逼迫和造就的。
我很喜欢这个有着和马克思一样头像的潮籍美人,他那种天真烂漫的像向日葵一样开心的笑容,不是每个人都能目睹的!
原刊于《散文》2011年第12期、《广州文艺》2015年第11期
黄国钦,广东潮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曾任广东省文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第六届主席团成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理事,第八、第九届主席团成员;潮州市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出版艺术散文《中国木雕·广东卷》、城市传记《潮州传》、作品集《心路屐痕》《梦年纪事》《青春笔记》《兰舍笔记》《花草含情》《拉祜的歌声》等10多部。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匈牙利、蒙古语。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