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淋漓绘荔枝,灵禽婉转立琼枝”。宣纸之上,墨色与胭脂交织,晕染出满枝沉甸甸的荔枝,果皮的褶皱不用细勾,只借浓淡墨色自然区分,朱砂点染的果尖带着水汽,仿佛刚从枝头摘下,还沾着南国的晨露。画家以泼墨法写叶片,浓绿中透着苍劲,叶脉藏在墨色里若隐若现,倒比工笔勾勒更显生机。
最妙是枝上那只灵禽。淡墨扫出羽翼,焦墨点首,喙尖微勾,似正侧耳听风。它不站在最繁茂处,偏选了枝桠转折的留白间,翠羽轻颤,与红珠般的荔枝相映成趣。这一静一动,让画面活了起来——仿佛能听见鸟羽拂过叶尖的轻响,闻见荔枝熟透的甜香。
“红珠璀璨丹青韵,翠羽轻盈画里诗”,说的正是这般意境。荔枝的“红”不艳俗,在水墨衬映下更显温润,是丹青晕染的含蓄;灵禽的“翠”不张扬,与枝叶的墨绿相融,似从诗行里飞出的灵动。画家没画满枝硕果,只取三五簇荔枝、一只飞鸟,留白处便似有清风穿过,让人想起岭南的夏日,蝉鸣里藏着丰收的欢喜。
这画里没有喧嚣,只有笔墨与自然的私语。红珠凝露,翠羽含情,在尺幅之间,晕染出一幅有声有色的南国小景,读来如品一首清甜的短诗。
宣纸上,半枝石榴斜斜探出,新枝带着嫩红,老干裹着苍墨,最惹眼的是枝头那簇花——画家以胭脂调了淡墨,层层晕染出花瓣的厚重,边缘却留着些飞白,像火苗跳动时的轻颤,果然如诗中所言,红得像团小火,映得整幅画都暖融融的。
墨色里藏着的“香”,原是这般模样。叶片用浓墨大写意,主筋以焦墨勾出,叶肉却晕着淡淡的水痕,像刚被晨露打湿,凑近看,仿佛能闻见雨后草木的清气。花蒂处用枯笔点了几点赭石,似有蜂蝶刚落过,把花蜜的甜香也沾在了纸上。这“流香”原不是真的香气,是笔墨勾连起的通感,让观者从色彩里嗅见了初夏的味道。
老枝的尽头,用浓墨稍顿,勾出个饱满的轮廓,墨色比叶片沉些,边缘晕着赭石,像颗半熟的石榴,正憋着劲儿要把皮撑裂。叶片间留了几处空白,似有阳光漏下来,落在那将熟的果上,暖融融的,让人想起秋日里,石榴裂开时蹦出的红籽,颗颗都像裹着蜜。
水墨的魔力,就在这“画里凝”的韵致里。不必真的画出满枝硕果,只需那团如火的花、那颗待熟的果、几道岁月的痕,便把四季的诗意都收进了尺幅间。难怪有人说,看这样的画,像读一首未完的诗,字里行间都是日子的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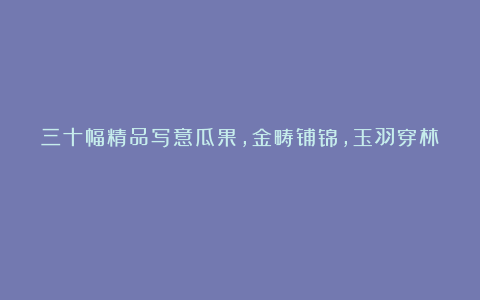
青葡萄串映双眸,水墨氤氲意自悠。
绿叶垂枝添雅趣,丹青妙笔韵长留。
水墨桃花映日辉,蟠桃硕果韵芳菲。
画中逸趣情难尽,诗意悠然醉不归。
水墨轻描枇杷黄,枝头摇曳韵飘香。
丹青绘就田园梦,静赏秋光意未央。
水墨葫芦意韵长,悬垂架下映秋光。心中若有田园梦,画里清风送晚香。
水墨氤氲绘翠屏,纤枝摇曳韵如铃。
田园意趣丹青里,蔬果清芬绕画庭。
画家/黄杰信,字乃三,号牡丹园主、梦染庐主、励精斋主、晚隆斋主等。诗、书、画、印冶炉自铸,立足传统而不为成法所囿,锐意创新而不为时弊所惑。作品气韵生动,墨色通透;格调高雅,构图新颖;以书入画,画里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