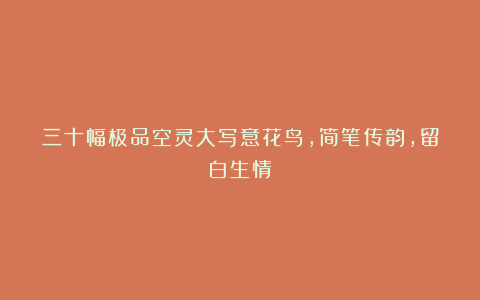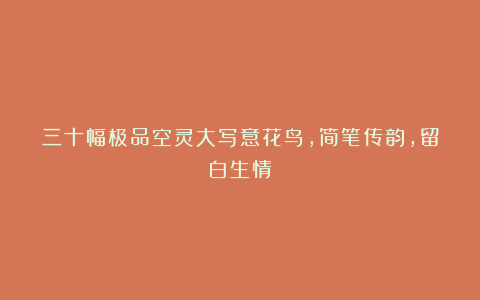|
观一幅写意花鸟小品,常于尺幅之间见天地。那些寥寥数笔勾勒的寒梅、浅墨淡彩晕染的秋菊、逸笔草草点染的雀鸟,往往没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却能让人在凝视间生出“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遐想。这便是写意画的至高境界——笔墨之内是形的收敛,笔墨之外是意的无穷。当“意境空灵”四字与花鸟小品相遇,便碰撞出超越技法的审美火花,让观者在虚实之间,触摸到艺术最本真的脉动。
写意花鸟的“笔墨之内”,从来不是技法的堆砌,而是“以少总多”的智慧。画师以简笔,绘四君子之神韵,不事雕琢而意境深远。画梅者,或用焦墨勾出老干,再以胭脂点染数朵,花瓣不必求全,只取“疏影横斜”的姿态;绘兰者,仅以淡墨扫出三五叶片,中锋拖出花茎,留白处便似有幽香暗度;写竹者,常以中锋立竿,侧锋扫叶,“个”字“介”字间便见劲节;描菊者,多以散锋点簇花瓣,墨色枯润相济,自有傲霜之姿。这些作品从不追求“形似”的周全,反而刻意删减细节:花瓣的纹理可以省略,叶片的锯齿可以模糊,枝节的皴法可以简化,但那股“凌寒独自开”的傲气、“空谷有幽兰”的清寂、“未出土时先有节”的坚韧、“此花开尽更无花”的优雅,却丝毫不减。
这种“克制”恰恰是写意的精髓。清代画家石涛曾言“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意思是笔墨的高低,不在数量而在“蒙养”与“生活”——前者是对自然的体悟,后者是对生命的感知。一幅优秀的花鸟小品,墨色的浓淡干湿都暗藏深意:用枯笔写竹,是为了显其坚韧;以湿墨画兰,是为了传其清润;焦墨点梅,是为了破画面的板滞。色彩的运用更是惜墨如金,有时仅用一点朱砂点睛,便让整幅画活了起来——那或许是梅萼的艳,或许是兰心的紫,或许是菊蕊的黄,在大片水墨的映衬下,反而比满纸重彩更显精神。所谓“意趣深厚原不在色量墨量”,正是这般道理:笔墨之内的“少”,是为了让观者的目光聚焦于“神”,而非被“形”所困。
若说笔墨之内是“有”,笔墨之外便是“无”。而写意花鸟的空灵,恰恰藏在这“无”中。中国画的“留白”,从来不是空白,而是“意到笔不到”的想象空间。一片空白,可以是寒梅背后的冷月,可以是兰草生长的幽谷,可以是修竹摇曳的清风,可以是秋菊傲立的霜天;一道飞白,可以是风吹梅枝的颤动,可以是露沾兰叶的晶莹,可以是雨打竹叶的飒飒,可以是霜覆菊瓣的清寒。这些“笔墨之外”的空间,让画面有了呼吸感,也让观者的思绪得以自由驰骋。
花鸟小品的“空灵”往往暗含时间的流动。一枝折梅,半开半谢,既不是含苞的青涩,也不是盛放的浓烈,却让人想到“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清雅;一丛幽兰,花叶相偎,似有若无的香气漫过留白,让人想起“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的静穆;数竿新竹,拔节而上,竹叶的倾斜里藏着风的轨迹,让人想起“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的哲思;几朵残菊,抱香枝头,花瓣的枯涩中透着霜的痕迹,让人想起“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的孤高。这些作品捕捉的不是某个凝固的瞬间,而是自然与生命的“转捩点”——从开到落的过渡,从静到动的切换,从有到无的留白,让画面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而这“未完成”,正是意境的无穷尽之处。
笔墨之内的克制与笔墨之外的空灵,最终都指向“意境”二字。对于花鸟小品而言,意境不是简单的“好看”,而是观者与画中物产生的生命共鸣。画面简洁空灵,正合四君子之质,淡泊、高洁、坚韧、优雅。
画家 :周墉/筠溪,字號:筠溪、老溪、筠廬、半壺、九儛山人。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