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编辑:马永清
文/庞晓飞
趴在我家院中的井台,望着圆圆洞口之下的水影,我想着心事。这是我这次回家第二次在井沿望井思索了。
在与父亲母亲商议后,终于做出决定,打一口新井。
院落的这口老井,诞生于我的爷爷辈,距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经过长时间的取水,水井底部水面以上周围的井壁,在无数次的绞水过程中,被木桶、铁桶磕碰得遍体鳞伤。紧挨着水面的井壁,在绞水时水波的冲击下,这两年坍塌面积不断增加。由于存在风险,已经难以下井修复。况且,这口水井北距我家老房檐墙仅仅两米多远,继续坍塌下去,对房子的墙基也会构成威胁。于是,在多次酝酿后,下了打口新井的决心。
新井的井口选在哪儿呢?我家院子比较大,眼睛扫过院落,停在大门口西侧离门楼不远的地方。
其实这地儿我早就有想法。这个“早”,是早在少年时代的“早”。当然,那个时候并不是要将井口放在这儿,而是一个儿童心中的许多构思,想要在那里实现。因为这里搞一个什么小建筑,放置一些玩耍的东西,还有什么常用的家什,出门取,进门拿,十分方便。大概是这个根深蒂固的因素在作祟,多年后为新井选址,目光兜兜转转,终究又落回到埋着童年念想的这块地儿。
我说,大门口那地方、距离房子远,咱一劳永逸,再也不怕安全问题。另外邻居们来挑水也方便一些。新井口就放在那儿吧。哎,父亲母亲竟然没有反对!
说这话时是一九八七年的夏季,已经参加工作的我请假回家帮父母收麦子。绞水时想到了井的问题。收完麦子,还有几天假,就想把井的事情也一并解决掉。
没有拖泥带水,划定了井址,马上开始动工。
时值夏忙,我们没有请人。其实我压根就没有请人打井的念头。还在少年时,心里就有亲手打井的想法,只是没有合适的机遇,当然也怕父母不会同意。那时候,仅在院落东边打了一个两人深的干窖,在窖底横向一侧挖了一个洞,用于贮藏每年秋末村集体分给我们家的红苕越冬。后来,应邻居叶二婆的要求,又在洞中挖出一个小洞,储藏她家的红苕。
我在地面画了一个觉得差不多大小的圆圈,铁锹楔入地表破土时,心里还有点小激动。好似终于实现了一个早已经设定的宏伟愿景。
像挖栽树的坑一样,我在圆圈内一层一层取土,并将圆圈周围壁土铲得光光亮亮。挖到半人高时,铁锹取土已经不太方便,我下到底部,改用短把小䦆头和小铲子挖土。深过一人高后,我在下面挖土,父亲在上边提土。深过两人高后,在地面支起三角架,用辘轳往上绞土。
我们村地处平原川道,附近又有河流,地下水位比较高。老井水面以上大约七八米左右,随着地下整体水位下降,到我打新井时也不会超过九米。
第二天,当我正在用小铲子刨土时,出现了沙土层。继续深挖了一尺左右,细沙变得湿润晶亮,有水珠儿在井壁周围沙层蠕动。再刨过几铲头,潺潺细水从沙粒间涌出。我运走几筐脚下的泥沙,井壁周围纯净的沙粒,就像早晨刚刚打开鸡窝门的鸡群,争先恐后涌出来填补坑位。我往下挖,它往上填,同时脚底以及井壁周围水源增加,水流渐大。不一会儿,水从脚面涨到小腿,而井壁泥土层下的细沙层,随水位增高出现坍塌。
挖家用饮水井时,最好在出水层部位有小石块之类的坚硬物质,它们能够保持井壁坚挺,为见水后继续深挖以增加水源,为后续加固水面下的井壁奠定基础。如果水面以下井壁有天然的石块支撑并且非常稳定,这样的良好条件下,甚至无须加固处理井壁。我们家老井的水线以下周围井壁,就是这样的构造。
我试着从地面放下来几块大石头,想拦住沙粒的涌出,但是毫无作用。因为井底地基是流动的沙粒,石头置于其上,无异于空中建楼阁。
我在沙水中拾起腰来,这口井只能放弃!
但是,新井还是需要打的。坐在院中的大青石上,我又重新扫视院落可以作为井口的地方。
经过多次取舍,比较斟酌,我在老井南五米处,与老井平行的地方,再次画了一个圆圈。这次,主要考虑了借助老井井底的砂石结构,避开纯细沙粒层的干扰,又与老井同在一条水脉。而且,距离房子也比较远一些。
重新开始挖掘。这一次,随着深度增加,我的心情进入了忐忑不安的状态。当泥土层与沙土层相交的时候,每一铲,都小心谨慎。
突然,小䦆头砸在一块石头上,碰出的火花在眼前溅开,我顿时紧张起来。
我的心中升起两种结局,一是遇到很大的石头。因为是直径比较小的家用饮水井,没办法处理,只能选择放弃。一是遇到的石头比井口小,可以将它吊出井外,或者留在井底用作加固井壁的材料。如此,水井打成功的希望就增加了几分。
我用小铲轻轻地剥离覆盖在石头表面上的黏土,继而再寻找石头周围的边沿,并一点一点撬动凝结在石头边际的沙土,石头亮出真身后,我放下了悬着的心。这块石头最长有三十多公分,试着摇动了一下,可以用双手抱起来。
这块石头移除以后,井底完全进入了沙石层。继续深挖半米,沙石潮湿起来,凭经验判断,距水层不远了。
相较于前日那口坍陷的流沙井,新井地质剖面堪称精妙。沙石层石块众多,个头大小匀称,砂质沉积物粗粝,孔隙率适中。咬合的石块既有支撑上边泥土层的承重骨架,砾石粗砂又起到了对水眼天然滤水的作用。看到这种地质结构,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我想起一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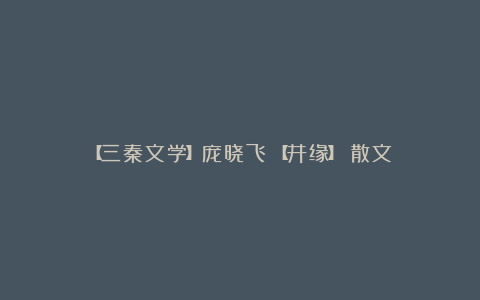
这则故事说的也是井。一户人家打井,当挖到渗水层,但还尚未发现水眼时,井主人想,不妨让打井师傅上井来饱餐一顿,这样就能够积蓄力量,趁着劲大精力强,多坚持一会,使得井挖得更深,找出更多水眼,保证水井有充足的水源。结果,吃饱饭的师傅刚下井,又上来了。主人疑惑,怎么刚用完餐就上来了。打井师傅说,不用下去了,井水渗出到半人腰了。
想起这则故事,主要是脚下这口水井即将挖到水源处。在水陆续涌出后,为了降低井底水的高度,方便继续向下挖掘,找出更多看得到的水眼,向地面吊沙石的频率肯定大幅度增加。而一直在井上给我用辘轳绞泥土的父亲,由于年事已高,不能让他继续承担接下来高强度高频率的吊沙石劳动。
正当我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瞌睡遇到了枕头,巧不巧地,我的二姐夫进了院子。哈哈,这下有了劳动力了。
两个青壮年配合,打井的速度明显加快。两个小时的功夫,地面已经堆出一大堆沙石,清水拘了半院子后,也从院墙底部的小水道流出墙外去,往井上盛水的水桶,已经远远跟不上井下水眼出水的速度了。
新井成功出水。砂石之间水眼众多,出水丰盈;而且,由于井下周壁石头的相互支撑,连加固水面以下井壁的工程也免除掉了。
绞上来满满一桶井水,父亲俯身啜饮后,评价道,水质与老井一样甘冽。看着桶中宛若一面镜子的清水,听着父亲点头肯定的评语,我心底享受着成功的舒坦。
打这口新井,我光着脚丫的脚掌,似乎读懂了泥沙深处的絮语。学习借鉴先辈们成功的实践,可以少走不必要的弯路。打这口新井,我握着铲头的手心,似乎摸到了生命轮回的桥廊,新井与老井一样丰沛、一样甘冽的水质,是不是老井的重生?而这,算不算是一种缘分?
多年来,我的心里一直觉得,井脉自会找传人。我在院子打的这口新井,是对存续半个多世纪老井脉搏的一个传承,也是对爷爷那辈人聪颖智慧的一种致敬。
本文图片来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简介
庞晓飞:男,陕西西安人。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大学文化,现已退休。退休前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渭南市分行。有多篇工作研讨及论文发表在国家核心学术期刊。爱好文字文学。有散文、诗歌在报刊及网络平台刊发。出版诗歌集《你是永恒的新娘》《芒种》。
往期精选
原创作品授权发布
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本公众号联系
投
稿
须
知
平台总顾问:边士刚
法律顾问:李木子
顾问:白忠德、邓汉章、罗旭初、束宝荣、史 波、孙德科
策划:李书忠
宣传推广:鼎 文、王宝群、孙传志、袁胜民
平台主播:梦锁清秋、英子、王迎旭、慧 质、晓 锋
总编:鱼儿姐姐、徐萱波
主编:谢亚红、初阳、谭文群
编委:刘旭平、唐桂英、吴远红、张晓强、刘马陵、梦而诗、喝 茶、南友锋、马永清、张兴军、吴风平、张巧莉 、秦岭人家、秋日私语、徵 蔚、党月琴、刘军英、米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