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5夜
读鲁迅|07
谁不是在明暗之间?
文 / 若文
《明暗之间——鲁迅传》本书作者是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他的老师增田涉曾在1931年毕业后不久来到中国。从那年的3月至12月回到日本的十个月间,增田涉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在拉摩斯公寓的鲁迅家中待上几个小时,是与鲁迅有过密切交流的人物。在增田涉眼中,鲁迅口中奴隶这个词频繁出现,就像长在了他的身上。甚至对于生活开支的细节,每月鲁迅的必需花销是400元,生活费200元,购书款100元,寄往北京的生活补贴100元,增田涉都是清楚的。
作为一本鲁迅传记,该书优点是内容严谨丰富,同时篇幅又不长。作为日本学者,作者对于鲁迅生命轨迹的考察,擅长论述传主外部环境的人事变迁,揭示传主转变的时空背景。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文书才弃用“夷”字,改用“洋”字,并兴办了一系列包括江南水师学堂在内的西式学堂,这就为日后家道中落的鲁迅提供了另外的一种人生可能。如八国联军促使了章太炎转向排满,前往日本,而章氏不畏牺牲的革命家人格与风度,最终深深地影响到了鲁迅。如1912年的蔡元培辞去教育部长,对于鲁迅实际上意味着辛亥的败亡。在7月20日陈公猛家中蔡元培的欢送会上,仅有许寿裳、蔡克清、鲁迅几人参加。当日大雨,鲁迅回家写出了《哭范爱农》。而1919年6月陈独秀入狱,李大钊与胡适爆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新青年》同人中出现了难以避免的对立。这些几乎都是别人身上的事件,看似与鲁迅无关,却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生活环境和心路历程。
尤其是《狂人日记》一文,作者指出文章背后世存在这一战后全世界的人道主义浪潮,并且联系到了日本的白桦派文学运动,以及小牧近江在法国参与了巴尔塞等人发起的“光明运动”,对于播种人运动的影响,这些观察往往是我们从国内视角中容易忽略的。
增田涉
鲁迅唯一的出国经历就是日本。1907年26岁的鲁迅有意识地开始创作,就是在东京留学期间。留日期间也是鲁迅思想形成的关键期。作者发现,鲁迅在1907年12月至1908年12月文章评论中,提到的欧洲书籍就有80多种。我们由此可知,鲁迅独到的思想形成,也有着一个广泛吸收外界知识的成长时期。那些被后世认为是鲁迅独创思想的文字中,很大部分是以日语、英语、德语写作的介绍、研究、概括书籍为材料,裁剪贴合而成的。作者也坦然承认,鲁迅收集翻阅这些材料,用剪刀加浆糊的方式构建自身的思想,这种强韧的原创性足以让我们瞠目。
对于鲁迅的留学生活,日本学者搜集资料与考证自然更为有利。书中提到鲁迅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衣着朴素,坐公交车,会被司机误认为是扒手。这与鲁迅在北京教书时穿得像“乞丐头子”何其相似。藤野先生曾想了解中国女性缠足具体如何导致畸形,让鲁迅一度非常为难。鲁迅在日本的最后时间是1911年5月,那是为了催促周作人回国,鲁迅待在日本大约半个月。在东京他没有会见任何朋友也不曾游览,只是看了看丸善书店。前些天,网上有人讨论鲁迅在日本的情感经历,信息来源多是来自国内。说实话这个问题,证据能够讨论日本学者早就做到“事无巨细”了,不至于到今天连个像样证据都看不到,大家只能凭空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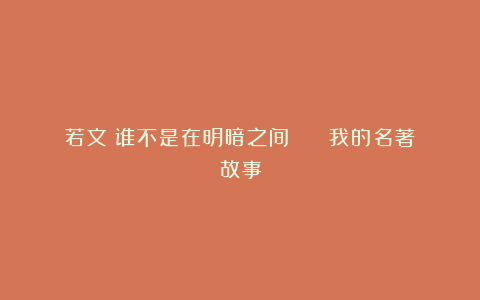
语言严谨之外,也有一点抒情的痕迹。据说鲁迅从日本回国的行李中,除了组织学标本还有一盆栀子花。1919年底,鲁迅从绍兴搬家到北京,把日本带回的栀子送给表弟,此后再未踏足故乡。到了1927年鲁迅在广州经历了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屋中仍然养着水横枝,即水中栽培的栀子。三处提到栀子,我想是有些情感寄托。
鲁迅医学笔记
我认为好的鲁迅传记不能绕开对作品的分析与阐释,作者眼中鲁迅的创作有着耻辱意识。绍兴本就有禹陵、卧薪尝胆的地方故事,在我看来大禹父亲治水失败,勾践卧薪尝胆都有一种忍耐耻辱的意味。中国自古就有“知耻近乎勇”的话。作者指出冲击鲁迅内心的是一种耻辱意识,为了自己对铁屋中的沉睡者置之不顾的耻辱,为了自己与沉睡者一同保持沉默而耻辱。
作者在解释鲁迅的《呐喊》时,指出这不是冲锋陷阵的呐喊,是挥舞旗帜、高声叫喊为战场中央交战的军人助威。鲁迅在《新青年》时期的作品可以称为“为了打破寂寞而发出的喊声”,那么其1922年的几部作品对应的说法是“寂寞本身化作的声音”。所谓“彷徨”,是指面对觉醒却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在荒野中徘徊以寻求道路。到了《朝花夕拾》鲁迅的内心姑且挺过了充满危险的“彷徨”,开始渴望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生”长社会与时代之中的意义。
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鲁迅、吴虞对于“孝”的批判,作者指出中国传统所谓的孝道已经不是家庭伦理,恰恰是“国家政治制度将原本属于家庭道德的孝装扮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通过将孝普遍化,为以皇帝为顶点的王朝国家建构道德上的支撑”。这些认识我认为是极为深刻的,也很好地解释了鲁迅高扬的“非孝”观点,同时又对母亲极为孝顺的生活表现。
增田涉所藏含批注的鲁迅作品《呐喊》
本书作为一本通俗读物,在章节上大大简化了鲁迅在上海的内容,我认为是一大遗憾。作者说鲁迅的思想在广州时期基本定型,又承认自己的研究还没有拓展到鲁迅的上海时期。众所周知,鲁迅在上海时期论战中,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很大的变化,这一点有必要进一步展开说明或者驳斥。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同时鲁迅根据进化论,视自己为一个过渡性质的中间物。因此鲁迅始终在生命的一次性和过渡性,寻找着自己“生”的意义。在时代加速发展的当下,我们每一个人,谁的人生又不是科技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过渡性质的中间物呢?鲁迅了不起的地方,正是在于既舍弃了希望的盾,也没用被绝望诓骗,而是确立了自己在“不明不暗”的世界中不断前行的立场。鲁迅四五十多岁还在不断地探索,我们还年轻,没有理由半道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