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9年,大宋帝国深陷“积贫积弱”的泥潭,一场由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拉开序幕。
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张国家积极介入经济,开辟财源,试图在不加重百姓赋税的前提下实现国库充盈。
然而,这场改革因触及权贵利益、执行偏差以及神宗皇帝的病逝,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便是在史册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却也充满争议的“王安石变法”。
说完了正史记载,我们不妨换个频道,走进罗胖子的《文明之旅1069》,听他以惯常的风趣幽默、略带夸张的语气,嘚啵嘚啵了近一个小时,描述出的“王安石变法”。
这这这,简直就是一场仿佛超前千年的“金融改革大实验”。
在这场大实验中,王安石宛如一位手捧“理财宝典”的穿越者,意气风发地站在了总导演的位置,信誓旦旦地宣称“给我20年,我会给你们一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大宋”。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让这场改革最终演变成了一出充满荒诞与反思的悲喜剧。
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在大臣中是既邋遢又固执的典型,隔三差五就要被好友们强行“拆洗”一番。
然而面对大宋的财政困局,他的“脑洞”却开大到了极致,其中最为人称道、当然也是最受诟病的,便是“青苗法”。
此法让政府摇身一变,成为帝国最大的“信贷机构”。想象一下,官员们不再终日埋首文书,而是化身“银行客户经理”,热情地向农民推销年利率40%的“惠民贷款”,美其名曰要打压民间高达70%的“高利贷”。
表面上看,这简直是一步妙棋:农民们的融资成本大幅降低,政府也坐收了利息,双赢局面唾手可得。
我们仿佛看到,头发乱糟糟、官服油光光的王相爷对着同僚们说:“瞧,我不用加税,国库也能鼓起来!”
然而,现实总是啪啪打脸,哪管你的初心是为何。
这场精心设计的“金融实验”在推行中迅速异化:“自愿贷款”成了强行摊派,“4分利”成了基层官员必须完成的指标。
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地方官们各显神通:有的专挑富户“薅羊毛”,不贷也得贷;有的则简单粗暴地将贷款额度直接摊入田税。
为何好政策会走样?根源在于,王安石可能低估了传统民间借贷高利率背后的经济逻辑。
插一句个人感觉:现在的很多利民措施,也总能遇到了同样的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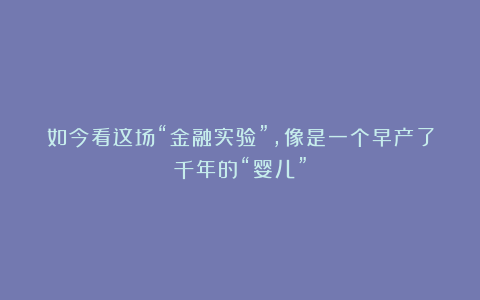
民间70%的利率,并非全然源于地主的“心黑”,而是高风险下的市场选择。
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违约风险极高;贷款额度小、审核成本大;缺乏现代征信体系……这些都推高了资金价格。
官府以40%的利率入场,从纯商业角度看,几乎注定亏损。地方官员们心明眼亮:照章办事,必然赔本!
于是,“对策”应运而生,好经硬生生地被念歪了。
更关键的是,传统社会自有一套运行逻辑。在熟人社会里,地主对村民知根知底,谁家勤劳、谁家靠谱,甚至谁家有个如花似玉的“喜儿”,都是那个时代最接地气的“征信系统”。
民间借贷也充满着弹性:今年收成不好?可以宽限至明年;没钱还债?可以用粮食、牲畜抵偿。
反观官府的“青苗贷”,却显得僵化而冰冷:到期必须还钱,只收现金,不收实物。
对此,司马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人无权,放贷已让穷人不堪重负;官府手握强权,再行强行放贷之事,百姓何以生存?
有人戏称王安石是“穿越者”,罗胖子却犀利地指出,“有人”既低估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也低估了传统社会的顽固性。
“有人”显然忽略了,现代银行之所以能低息运营,依托的是公民身份系统、税务体系、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大数据风控等一整套精密的社会基础设施。而传统社会则是一个“零增长社会”,财富基础是土地,暴力仍是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式,社会往往陷入相互伤害的内卷循环。
王安石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几项看似先进的制度设计,去轰击那座由千年传统筑成的铜墙铁壁。
但我们不能否认了他的伟大,他敏锐地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命题,已经触及了社会财富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只是没能抓到手而已。
这场发生在千年前的改革,犹如一场提前上演的现代金融“压力测试”,它告诉我们:任何制度的移植,都离不开与之匹配的社会土壤。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与共识,再完美的蓝图,也难免水土不服。
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这场改革,不由得恍然大悟:原来古人早已尝试过我们所谓的“现代金融游戏”,只是当时的“社会服务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缺乏现代治理体系的传统社会——还无法兼容这样超前的“程序运行”。
王安石变法留给我们的,远不止历史课本上的笼统总结。
它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改革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场需要深刻理解社会底层逻辑、精心培育制度生存土壤的系统工程。
这跨越千年的启示,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