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如何肆虐全球?冰桶挑战、MeToo活动如何引爆社交网络?推特、微博如何成为主流的社交产品?Labubu为何能一夜爆火?这些看似每天都在身边发生的现象背后,究竟是毫无章法可循的偶然,还是有一套可以不断总结并被人掌握的科学理论?总有人想要破解这些传播现象之下的谜题,戴蒙·森托拉在其《临界变革》一书中也尝试综合了多种社会理论,整理出了一套让人能看透本质的方法。
成功引爆传播的关键在于KOL(意见领袖)吗?
故事还是要从上个世纪二战前后说起,那个时候广播兴起,这种全新的传播工具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社会学家也仿佛获得了一个测度传播效力的好的载体,那时候的普遍的观点认为,媒体信息从广播电台传播到数百万人那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观点和行为。
但拉扎斯菲尔德并不这么认为,实际上,广播媒体只影响了它的一小部分受众,大多数人并没有被这些信息所左右。但一个核心群体——意见领袖在密切关注着媒体,他们影响了大多数人。1944年,他创造了“意见领袖”一词,他们是一个比其他人更能回应媒体的特殊群体,他们成为社会“影响力人物”,大多数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新的媒体内容。
后来基于拉扎斯菲尔德这种观点,即人脉通达的影响力人物是传播从社会运动到创新技术等一切事物的关键,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总结了“个别人无法则”,即一小群耀眼的社会明星,他们努力将新的思想和行为传播给其他人。依靠这种理论的传播,今天被称为“影响力营销”。
但这基于一种“影响力迷思”,每当我们想传播一个观点、一种趋势或一场运动时,我们都需要找到这群特殊的人,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也的确可以解释。但当它拓展到新闻的传播、社交媒体的火爆以及社会运动的发展时,就从事实变成了虚构,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在诸多的传播当中“失效了”。
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推动了一场认知革命,即受众广泛的社会明星不能解释影响力是如何传播的。相反,社会明星的联系人,其联系人的联系人以及这些人的联系人等,形成了一个巨型几何模式,构成了每个社会的基础。这种模式解释了媒体信号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为什么某些革新行动会成功或失败。
这种模式在技术上被称为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它对于深入解读社会变革至关重要: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如何以及何时成功;争议性的社会思想是否会进入主流视野;在什么情况下,文化运动会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在新的科学观点中,社会明星只是网络关系链条中的一环。有时,他们可以启动一场大规模的传播。但当传播的不仅仅是一则新闻,而是一场社会变革——一种面临未采纳者的影响力抵消因子的新想法或新行为时,社会明星就会面临挑战。正因为人脉通达的人往往很难参与变革运动,他们会在社会网络中形成障碍,减缓社会创新和新思想的传播。
通过信息时代对传播的更清晰的观察,可以发现促使变革发生的关键社会网络不是以人脉通达的影响力人物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发散模式,而是渗透社会网络边缘的连锁反应模式。如果变革要获得动力,它就必须从那里开始——从那些跟我们面临同样选择和挑战的人开始,这些人的协同和接纳形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形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从病毒传播到病毒式传播,弱关系的主导模式。
如果意见领袖的威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强大,那么又该如何去寻找传播的规律呢。不妨先从人类社会中最常见的传染病模式开始观察。黑死病是欧洲疾病传播史上最可怕的案例之一,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更便捷的交通网络,让近距离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的扩散更容易、更快。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凭借一篇论文《弱关系的力量》破解了传染病扩散的关键。
格兰诺维特区分了两种联系——强关系和弱关系。亲朋挚友是信任的牢固纽带,即强关系,他们构成了一个人的核心社会关系。而泛泛之交(就是那些在会议上、课堂上或度假时遇到的人)是弱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外层结构,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因为他们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轨迹之外,所以他们可以帮助人结识新的人。
虽然强关系非常适用于疾病传播,因为人们非常熟悉,并且接触很多。但是那也仅仅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如今现代交通技术改变了一切,如今,人们能够在任何时候与世界各地的人打交道,这些人存在于我们的直接社会网络之外,但与他们产生的任何联系都会让人与他们的社交圈——那些有可能永远不会相遇的人建立一种罕见的联系。
格兰诺维特发现,强关系的重叠结构使人们在传播信息和交流思想方面效率低下。因为关系的重叠导致冗余。如果你想通过强关系来传播一个新想法,你会发现你可能告知的是一位已经从你们的共同朋友那里听过这个想法的朋友。如果仅仅使用强关系传播,消息就在你的强关系网内传来传去,并不会大范围传播开来。
尤其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要让你的想法在众多想法中脱颖而出、备受瞩目,冗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每次有人把你的想法解释给一个已经听说过的人听,就浪费了一次传播机会。而弱关系的力量在于,它可以把我们的想法呈现于巨大的全球关系网内,呈现给那些我们可能永无见面机会的新面孔,使他们有机会了解我们的想法。
对此,格兰诺维特得出一个结论:弱关系是找工作、进行促销活动、完成产品广告宣传和开展社交活动的最佳途径。弱关系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渠道,它可以使我们与更多人联系起来,尤其是与不同类型的人联系起来。
而在格兰诺维特之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就通过一个寄送明信片的实验,提出了如今被称为“六度分隔理论”,即随意一个人,向完全陌生的一个人寄送明信片,中间平均转寄6次,就可以到达。
弱关系影响力的观点来自传染病学,当涉及生物病原体,与一个已经感染的人进行一次简单接触——握手或单纯的交谈,就可能感染病毒。一个已感染的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越多,这种疾病就越容易广泛传播。信息也是如此。几十年里,我们一致认为一切事物,不只是细菌和信息,还包括产品、社会规范、政治运动、大众技术甚至宗教信仰的传播方式,都和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一样。特别是现在,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世界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弱关系是创新技术和社会变革得以成功的关键。
烟花状的弱关系和渔网状的强关系。
虽然弱关系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当深入研究变革发生时,没有任何关于社交媒体技术、社会运动或社会规范传播的数据证实弱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恰恰相反,像社交媒体这种技术应用并不是通过弱关系迅速传遍全球的。它们通过相互重叠的网络传播,这些网络通常是地理意义上的强连接,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或者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
过去,社会关系学家一直认为“冗余”影响了有效传播,的确,冗余无助于传染病的传播,因为你不需要第二次接触。但当一个新想法出现时,你的强关系网络中会出现两个、三个或者更多人重复传播这个想法,使其变成规范。会改变你对它的看法和感受,这就是被忽视的冗余的力量。
为了更形象地呈现弱关系和强关系之间的差异,社会学家们采取了一种几何结构描绘的方式。
弱关系的几何结构看起来很像烟花,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爆炸”的中心,他们的弱关系向各个方向随机延伸。每一根关系线延伸到不同的,有时甚至是遥远的地方。在弱关系中几乎看不到社会冗余。弱关系中的个体与其他人的朋友也往往没有联系。
强关系的几何结构看起来则更像渔网。这些网络的外观是由三角形和矩形组成的连续序列。这种模式被称为网络聚类(也称社群网络结构),其独特之处在于内含大量的社会冗余。人们与其他人的朋友都有联系。
我们现实世界的网络关系是这两种模式的结合。事实上,我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这两种不同的模式里,只是每一种的影响不尽相同而已。
关于传播的新范式:简单传播和复杂传播。
既然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关系都是弱关系和强关系的组合,那么就不能简单的用这种划分来解释传播现象,我们需要一种更加有力的分析工具,来呈现传播的差异性。在《临界变革》中,就提出了一种新的传播范式:简单传播和复杂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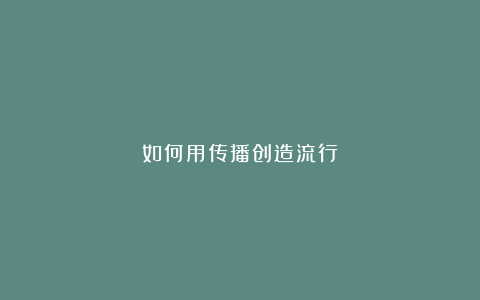
病毒式传播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简单传播,只需要简单的接触,就可以完成的“传播”。简单传播受益于社会网络的规模,一个世纪以来,简单传播定义了我们对社会传播的看法,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定义创新和变革运动发展的默认模式。但问题是,简单传播的动力学仅适用于简单思想的传播,而促使信仰和行为改变的则是另一种传播方式,即复杂传播。
对于创新来说,人们需要从众多采纳者处得到确认,才能被说服,新行为才能得以传播,一种新的思想或行为遇到阻力越大,就需要越多的社会确认来说服。我们平时关注的大部分行为——市场投资,选择政治候选人,做职业发展规划,选择生活的社区,使用避孕措施,购买价格昂贵的科技产品或者加入某一社会运动——都属于复杂传播。它们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涉及实际的风险。一个决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越大,人们在冒险之前就需要更多的“证明”,即来自许多周围的人的确认。
造成传播复杂性的的阻力,可以简单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即影响人们采纳新思想、新事物的四大障碍。
1、协调性。有些创新产品有吸引力是因为大家一起使用。如果一个创新产品或行为的价值取决于采纳它的其他人的数量,那么它的传播就需要社会确认。比如社交类产品。
2、可信度。一些创新产品会在效率或安全性方面遭到质疑。采纳某种行为的人越多,就越能证明这种行为不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危险。比如交通类产品。
3、正当性。一些创新产品在被采纳前要得到社会认可。这里的障碍是面临尴尬或名誉受损的风险。采纳一种行为的人越多,人们就越期待别人会赞成这个决定,面临尴尬或受到处罚的风险就越低。比如时尚类产品。
4、情绪感染力。一些创新产品和行为只有在人们相互激发情感时才具有吸引力。采纳某一行为的人越多,其他人就越对采纳者的行为感到兴奋。如体育赛事。
创造复杂传播的关键——创建“宽桥”与相关性。
不同社会集群之间的联系被称为桥梁,这些桥梁是弱关系的代名词,它们是一种不牢固的社会关系,将身处于不同群体的人联系在一起。早期的社会学家经常用桥梁长度来衡量其价值,前者也就是桥所跨越的社会距离,可以称其为“触达”。即使在今天,一个很普遍的假设是:触达是成功的关键。
但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桥梁,不是其长度,而是宽度——我指的是它们包含的关系数量。弱关系是窄桥。相比之下,宽桥则反映了真实的协作。宽桥不关乎触达,而关乎冗余。窄桥通过弱关系传递信息,宽桥通过强关系承担社会变革。
有了社会集群以及中间的桥梁,我们具备了传播的基本渠道,但引爆传播还需要更关键的一个要素,毕竟一种全新的理念或产品,是需要人的认可,如果我们把这种认可定义为成功的传播的话,那么建立一个成功的传播基础的重要理念不是相似性,而是相关性。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采纳者的相异性而非相似性是确定他们的相关性的重要因素。这完全取决于环境。
有三个原则确定随着环境的变化,什么将成为最具相关性的社会影响力来源。
原则1:当行为变革需要社会证明一项特定的创新对人们有用时,与采纳者的相似性就是创造相关性的关键因素。只有当人们看到和自己相似的人采纳了一种新的饮食、锻炼计划或美容方法时,他们才会相信它的有效性。所以要明确可信消息来源。
原则2:当行为变革需要一定程度的情绪感染力或忠诚感和凝聚力时,那么确认来源的相似性将有助于激发行为变革。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强调来自同一家乡的新兵的团结感,积极动员了应征入伍。所以要创造团结感。
原则3:当行为变革基于正当性,也就是基于相信行为正被广泛接受时,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确认来源的多样性是传播创新的关键。例如,人们是否愿意加入某一个社交媒体的运动,取决于它是否被来自不同社交圈的同伴所接受,这些人建立了运动给所需的广泛正当性。所以要关注并创造正当性。
社交互动是一场协调游戏,到达临界点之后传播就会被引爆。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认为语言是一种逻辑系统,能够揭开世界的奥秘。“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哲学无非是把问题讲清楚。语言就是一切,如果你理解语言,你就理解了这个世界。
而后,经过了一段避世的乡野生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依然相信语言是理解世界的关键,但他不再相信逻辑是理解语言的关键。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所以语言是社会性的,理解语言的秘密在于理解人们是如何与他人玩“协调游戏”的。
比如,你和我第一次见面,我伸出手,想和你握手,你却对我微笑,拒绝了握手。下次再遇到陌生人时,我还会伸出手去握手吗?要经历多少次失败的握手,我们才会停止对陌生人使用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如果停止了,我们会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每一个革新的观念,每一种创新的产品,都仿佛是“协调游戏”的工具,人们在这种社交游戏中反复的沟通和确认,直到自己愿意尝试那些新东西。每个协调游戏都有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一种新奇的行为一旦获得足够的吸引力,每个人对于什么是可接受的看法就会突然改变。《临界变革》中认为这个临界点大概就在25%左右。也就是一旦群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接受了一样新东西,那么就可能会进入这种新东西的爆发性裂变的节奏。
怎么办?猎枪策略、银弹策略和雪球策略。
了解了这么多,那么如果想要引爆一个观念或一个创新,我们该如何做?
《临界变革》中提出了三种策略,首先是猎枪策略,这是在病毒式传播原理的基础上上发展而来的。要使用这个策略,你要广泛地分配你的资源,就像用霰弹枪射击一样,最大范围的覆盖整个网络,并且选择的起始传播点彼此的距离越远越好,这将创造最大的曝光度。这种策略在传播病毒方面非常有效,但在推动变革上效果就差很多。
银弹策略是猎枪策略的通用替代品,它避免了资源分配过于分散的问题,相反,它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即寻找网络中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节点作为起始点。银弹策略也可以很好的传播病毒,但对于推动变革方面,在分散性上没有比猎枪策略好很多,同时那些具有影响力的起始点具有的多个连接点属性,也是阻碍传播变革的要素,毕竟,在变革传播的早期,更多的连接点,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不接受者,也就是影响力的抵消因子存在。
而雪球策略则是基于瞄准社会网络中能够使创新产品被广泛接受的特殊位置,它的目标不是说服所有人立即采纳创新,相反,它会逐渐为创新赢得支持,直到达到临界规模。雪球策略的关键是触达大量冗余,让创新先在小的强关系网络中发酵,随后通过宽桥不断地向外传递。
知易行难,传播也不例外。
传播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可以说有人类社会就有传播的存在。而传播学也并不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早期它更多被聚焦在如何通过媒体影响公众的政治和商业选择的说服理论上,如今伴随着更多媒介的产生,也验证了麦克卢汉所讲的媒介即信息,同时去中心化的网络、视频化的内容等也不断地改变和塑造着传播理论的形态。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进化,传播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演变,回到其根本目标,无非就是传递信息和改变或强化人的信念。而能够衡量这两个目标的显性方面的,就是信息传播带来的“知道”和信念改变带来的“行动”。这也是人们探讨了几个世纪的“知与行”。
正如那句话所说,知易行难,在传播中也同样,信息传递往往是简单的,但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并推动其行动,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具象到现代商业社会中,让别人知道一个产品,和让别人知道这个产品并愿意为其付费是两个难度等级的传播结果,正因如此,现代的传播理念中,也由此逐渐分离出两类不同的传播方式——简单传播和复杂传播。
要想引爆一个信息,使其变得无人不知是一种传播带来的结果。而要想引发一场观念的革命,让更多人为了某一个观念行动起来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只有认清了二者的区别,才能真正理解传播在商业、政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