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源,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等多重身份的创作者,李浩源在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中以苏轼《东坡志林》记游篇为书写内容,将魏碑《元桢墓志》的骨韵与唐楷的精妙熔铸于笔端。这场创作实践不仅是对经典碑帖的当代诠释,更暗藏着一位书家在传统脉络中寻找个人语言的探索轨迹。
初识《元桢墓志》时,李浩源被其刀刻痕迹下的笔墨韵律所吸引。这块北魏墓志以方劲雄强著称,然他并未止步于模仿刀刻的凌厉,而是试图剥离金石气的表象,探寻 “以笔代刀” 的书写性。“魏碑的魅力在于’险’与’稳’的辩证关系,” 他在临习中发现,《元桢墓志》的字势常以欹侧取态,却因重心的巧妙把控而稳如磐石,这种 “险而不落” 的张力恰是传统书法 “违而不犯,和而不同” 的美学体现。
为消解魏碑过于方切的刚硬感,他在笔法上进行了 “软化” 处理:起笔时藏锋入纸,以圆转替代方折,行笔中融入篆籀的绞转韵律,使线条呈现 “灵动圆润” 的质感。这种处理并非弱化魏碑的筋骨,而是通过笔墨的虚实变化,让刀刻的冷峻转化为书写的温度。正如他所言:“碑刻是静态的历史,唯有以笔墨激活,才能让古人的笔触在当下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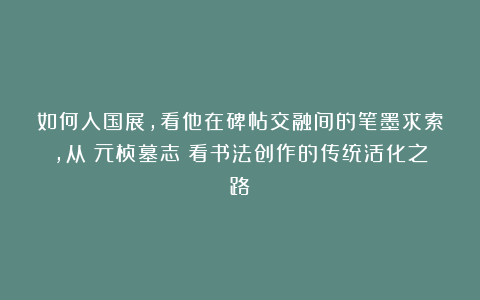
在单字造型上,李浩源将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的 “紧结” 特征视为破解魏碑结构松散的密钥。《元桢墓志》因刻工与岁月侵蚀,部分字形易显粗犷,而《九成宫》中宫收紧、四肢舒展的结体法则,恰好为其注入了 “稳而不滞” 的秩序感。他以《元桢墓志》的欹侧骨架为体,以《九成宫》的精密布白为用,在 “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的对比中寻求平衡。
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技法叠加,而是对两种书体精神内核的深度对话。“魏碑的’险’需要唐楷的’稳’来收束,唐楷的’板’则需要魏碑的’活’来破局。” 他举例说明,某字右部竖画故意拉长以造险,左部点画则以《九成宫》的短促笔法收紧,通过欹正相生的动态,让单字在稳定中暗藏机锋。线条粗细的处理亦服务于这种理念 —— 摒弃强烈的提按顿挫,以均匀的墨色铺陈,使整体章法呈现出 “冲淡平和” 的视觉节奏,避免因局部冲突破坏通篇的气韵流动。
回溯学书历程,李浩源坦言,对《元桢墓志》的突破始于 “背叛”。早期临帖时,他曾执着于还原碑刻的刀痕,却陷入 “状如算子” 的机械模仿。直至在一次创作中偶然以行书笔意书写魏碑结构,才顿悟 “以帖养碑” 的奥秘。这种转变不仅是技法的调整,更是对 “传统” 的重新认知:“经典不是固化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活水,唯有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才能让碑帖语言产生新的语义。”
在《东坡志林》的创作中,他将苏轼文章的洒脱气韵与《元桢墓志》的沉雄基调相糅合:书写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时,故意放大 “山”“月” 等字的欹侧角度,以魏碑的方折表现山的险峻,又以圆转的笔锋勾勒月的柔润;而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则通过线条的轻重缓急,在《九成宫》的结体框架中注入行书的节奏感。这种 “以文入书,以书显文” 的创作思路,让文字内容与书法形式形成了互文关系。
李浩源的创作实践揭示了一个本质:真正的创新从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在经典谱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他以《元桢墓志》为基石,以《九成宫》为桥梁,搭建起从碑到帖的转化通道,其核心在于 “活化”—— 让魏碑的骨力与唐楷的妍美在笔墨中完成基因重组,最终形成 “险稳相生、刚柔并济” 的个人风格。
“书法的传统如同一条长河,每个时代的书家都是河道的开凿者。” 李浩源的探索或许正印证了这一点:当我们不再将碑帖视为孤立的范本,而是视为可以对话的文化生命体,传统便不再是束缚手脚的枷锁,而成为激发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在这场跨越千年的笔墨对话中,他以《元桢墓志》为引,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一个 “以古开今” 的鲜活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