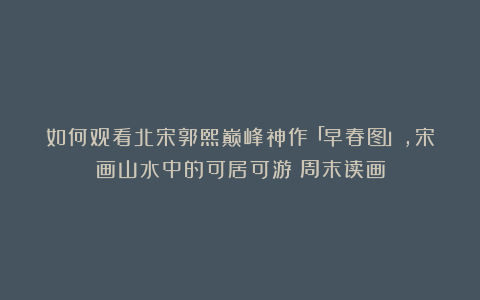
中国山水画写实一脉传统在宋代走向巅峰,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早春图》便是这一全盛时期的典范之一。
周末读画,一起翻开《读画》杂志最新第八期,跟随学者袁柳军细读这一了解中国山水画观看的理想范本。
–
讨论绘画,尤其宋画时,观众的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进入《早春图》之前,首先来看传为10世纪画家李成的《读碑窠石图》。仔细观察,画家给观众留出的最佳视角其实在画面中。一个平淡的读碑者的形象,将观画者视线引向那块巨大而精致的无字碑。
观赏《早春图》时体验到的观看位置,则是另一种“入画”——视角并不固定,随着画家制造的景观移步换景地观看。
正是观众观看位置的变化,让中国画家在处理画面空间时走向了与西方绘画截然不同的道路。作者借助唐代《宫乐图》,进一步揭示中国绘画构景的独特做法——画面采取了非常规高视点,以便观众获得完整的观看,与此同时,这些仕女并没有被塑造成俯视的效果,局部绘制视点并未改变,这与西方透视法中视点统一不同。
作者认为这种表达方式的目的或许是,画家并非向观众再现一个戏剧性的画面。同样,中国早期山水画画家努力用画笔构建的,是一个可以观想的场域,一片可以行走、居游的虚拟山水。
《早春图》特殊的观看方式包括两个层面:俯瞰式的“观”对照的是画面的整体布局和气韵;同时观众又可借助画中人的眼睛,以平视来满足对眼前之景更自由的“观想”。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总结归纳了山水画空间处理的三种典型方式“三远法”,这种样式化构图的价值也在此件巨幛山水中被充分发挥——主体部分采用高远,以主峰象征皇权,统领整张画面;走近画面,展开“小中见大”的近观,高远之境又将画面分作上下左右四个部分,错综复杂,互相关联,如同一部结构复杂的交响乐。
正如文章最后所总结,不同于西方人对“风景”概念的理解,山水画所描述的对象“山水”,强调的是“(成为伙伴的)对立因素之间无穷的互动”。山水的内部建立起一套相辅相成、动态调和的自足的世界,画面里偌小的局部都是无比鲜活的场景。
郭熙在《早春图》中表现的每一处细节与场景,都在应和画面整体气韵与结构的同时,满足着入画游观的观众每一次近在眼前的观看。
–
📒订阅最新《读画》杂志
相关作品
图1-5:宋 郭熙 早春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7:宋 李成 读碑窠石图轴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图8:唐 佚名 宫乐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