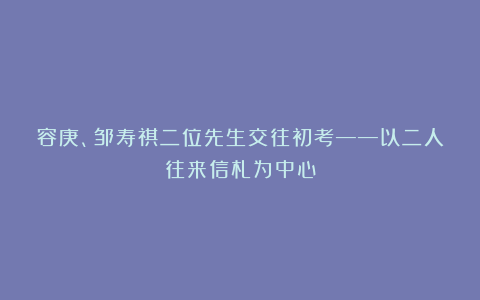▲书艺公社▲ 与万千书坛精英,
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本文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容庚、邹寿祺往来书札为中心,结合《容庚北平日记》等史料,对容庚与邹寿祺的交往过程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考察。两人的交往始于容庚在1921年初致信邹寿祺。此后两人书信往来频密,直到1932年5月停止交往。两人的交往主要以通信的形式进行,但曾于1925年、1930年在杭州有过两次晤面。文章还对两人关系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考察,认为在邹氏重要藏品的真伪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是导致两人停止交往的主要原因。
容庚(1894~1983),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曾任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邹寿祺(1860~1940),又名安,字景叔,号适庐,浙江海宁人。清光绪二十九(1903)进士。二位先生,同为近代重要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彼此曾有过一段较为频密的交往。但由于材料的限制,学界以往对此问题几乎不曾予以关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一批二位先生往来的信札,见证了他们当年的交往过程,其中涉及二人的行迹、学术讨论和藏品交流,还关涉不少金石学界的人和事,以及一些重要金石器物、拓片的流转、价格等,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研究民国时期金石学和收藏界的重要史料。本文拟以此批信札为中心,就邹、容二位先生的交往略加考证。
该批信札中,邹适庐致容希白的函件一共87通,其中86通由容希白亲手粘贴、装订成三册,大概依时间先后排列。每册封面均题“邹适庐尺牍,第※册,颂斋藏弆”等,第三册又有“一九五一年集存”字样,为容希白亲笔。其中夹杂有少量金石拓片、印蜕、诗稿等。另一件为明信片,系散件。从各函所涉及内容来看,现存此87通邹先生之信,似非其致容先生信之全璧,中间略有缺失,但仍能基本反映二人交往的整个过程。另有容希白致邹适庐的信札10通,亦由容希白手装成册,封面有其手书:“颂斋与邹安尺牍。一九七五集录。”此二项皆与其他颂斋友朋书札同为颂斋后人捐赠中山图书馆者。
容、邹二位先生最早交往的时间目前未见明文记载。《容庚北平日记》最早记录其与邹先生的交往,是在1925年3月25日写信,请邹先生为《金文编》作序。但《北平日记》的起始时间恰好是1925年,无法反映两人在此之前的交往情况。从两人往来信札和其他文献来看,容、邹二人的交往远早于此。
现存容希白所集邹适庐的第一函(图1,以下所称邹适庐信札的第某函,均据中山图书馆拟出版时所加的编号,大体根据装订顺序,再加以适当调整,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排列),篇幅不长,但内容非常丰富,特全文移录如下:
希白先生台下:顷自杭州来,得读手教,考定古文字,至为精审。学有自出,无任钦迟。奖饰殊不敢当。叔言自移家天津后,不通问已一年。静安则改入仓校教习,踪迹亦疏。晤时当一一作缘。前见法书小籀文,与愙斋中丞相同,已早神驰矣。大著亟盼成书,惟采辑不能不广。《汉金文存》今年本可印行,近宭事有收束之意,恐须另觅出资者。匆复,即颂春安。弟邹安拜上 新正廿日尔雅先生并问起居。
从内容看,此信应该是对容希白来信的回复。其写作时间为“新正廿日”,只记月日,未及年份。其中提到“叔言移家天津后,不通问已一年”。按,罗振玉于1919年春末携眷归国,与王国维相会于上海,五月,其三女嫁与王国维长子潜明。在女儿婚事后即去天津办理赈灾,并营宅为久居之所。此札言罗振玉“移家天津后,不通问已一年”,则应在1920年夏天或之后。结合落款的时间为正月二十日,则应迟至1921年春节后,公历的日期是2月27日。另外,王国维自1916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二日)携长子潜明自日本京都启程回国,于9日抵沪,随后进入哈同花园的“广仓学宭”任《学术丛编》编辑主任。1918年初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札中谓王氏“改入仓校教习”,或指此。
从此复信的内容,可以考知容希白来函的一些信息。“考定古文字,至为精审”“大著亟盼成书,惟采辑不能不广”二语,说明容氏在信中介绍自己对一些古文字的考释成果,并透露自己编纂《金文编》的信息。而罗、王二位“晤时当一一作缘”一语,则表明容希白希望通过邹适庐结识罗、王。“前见法书小籀文,与愙斋中丞相同,已早神驰矣”之语,可知在此之前邹先生已见过容氏所写的小字古籀,而容庚当时所写金文得力于吴清卿,且已有流传至外省者。邹适庐与容庚的四舅邓尔雅应为旧识,而此次容氏写信,很可能借重四舅的名头,故邹先生在信中称誉其“学有自出”,信末更有请容庚代向邓尔雅问好之语。
从此信还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这次通信主要是介绍自己的一些情况,其中多客套之语,未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犹如初次相识时之言谈较为拘谨。而随后的各函内容已大有不同:如容庚在随后的来信中就指出邹适庐的著作中收录器物的失误,并认为史兽鼎铭文中“爵”字似“觯”形(第三函则“说觯、爵通用而字遂相同”),还指出《专门名家》(亦名《广仓专录》)一书误收潍县陈氏簠斋旧藏伪汉“元凤残砖”等十砖。对这些问题,邹先生在复函中均做出了相应的回复。由此可反推现存邹适庐的第一函即是二人初次联系时他给容希白的复函。
据此可知,二人之间的交往,始于容希白给邹适庐写信。而此次给邹适庐写信,在其1922年夏天北上求学之前,是目前所知他与外省金石学者之间最早的通信。
容希白选择邹适庐作为自己最早求教的外地金石学者,最主要的原因是容希白在东莞编辑《金文编》的初期,就重点利用过邹适庐所编《周金文存》(从《艺术丛编》第一期开始连载,随后各卷陆续单独印行)。容肇祖曾回忆其兄早年编《金文编》的情形:
在邓尔雅的指导下,他根据拥有的材料,进行研究,编写了《金文编》。集录的字,以商周彝器款识为主,由于诸家著录真伪杂出,鉴定不易,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为据。摹写之字,先剪贴影印本罗振玉《殷文存》、邹安《周金文存》,然后再摹,以求逼真。暂时不识之字,附录于后。
除了《周金文存》,邹适庐在哈同花园所编的《艺术丛编》,尚发表有大量的金石文字资料,包括罗振玉、王国维的相关著述,这对初涉古文字领域的容希白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因此,当容希白在研习《周金文存》等文献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疑问和想法时,就直接写信向邹适庐讨教。当然,邹适庐与广东金石学界的交往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其中,邹适庐跟顺德名士蔡守的交往情况,已有学者曾加以考察。1916年,广州龟岗发现南越国时期大墓,当时被认为是“南越文王赵胡冢”,出土椁木上刻有标记次第的数字,并有不少明器。随后,邹适庐“得冢木全拓于粤中友人处”。1917年秋,哈同花园广仓学宭开会,发掘者香山李文枢携所藏该墓出土的明器数十事到会陈列。1918年出版的《广仓学宭艺术临时增刊》,主要刊登“南越文王冢”黄肠木刻字、明器以及潘六如所收集的部分南越残甓(当时误为砖,实际上是瓦)等拓片和照片。另外,邹适庐所编《专门名家》所收砖拓也有不少为蔡守、李文枢和其他广东藏家所提供。在第五函末,邹适庐还提到“贵处有罗原觉君,颇有藏帖。顷来沪上,曾见数种,有甚旧者”,说明其与罗原觉亦为旧识。容庚在来信中应该还提到邹适庐正在编辑的《汉金文存》,邹先生因此回复称“今年本可印行,近宭事有收束之意,恐须另觅出资者”,可知当时容庚对邹适庐的了解,有部分信息是从与邹先生相熟之人士获得,而非单纯得自相关出版物。
自此之后,两人通过书信展开了较频密的交流。在容希白北上之前,邹适庐给他的信尚有十二通,最迟的是“辛酉十二月”即1922年初所作,也就是说,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邹适庐给容希白的信就达十三通之多,而容先生给邹氏的信似乎尚不只此数(第七函有谓“两接寄件承刻印三,又书额,至谢、至谢”)。
1922年夏天,容希白兄弟联袂北上,在天津晋谒罗振玉之后不久即写信告知邹适庐,邹氏的第十四函即是对此事的回复。
由于容希白早年生活在东莞,1922年至1946年间定居北京,邹适庐则主要生活在杭州、上海,两人的交往只能主要以通信的形式进行。尽管早在容希白北上之初,邹适庐就曾邀请其到杭州游玩(第十四函:“西湖之胜,冠于东南。执事如惠然肯来,俾得一瞻风范,尤所欣幸”)。但直到1925年夏天,两人才在杭州首次晤面。据《北平日记》记载,1925年暑假,久居北京的容希白第一次回粤探亲。他在6月19日前往天津,24日乘船出发,于7月1日到达香港。在香港、东莞和广州等地探亲访友,一个多月后的8月15日,他和母亲、三弟肇祖搭船北上,16日十点到达上海。29日,“早七时乘火车赴杭,十二时到,寓西湖湖滨旅馆。面湖而居,步行至平湖秋月,并游西湖公园,雇小艇游湖心亭而归。访邹适庐”。31日“四时,邹适庐来”。至9月2日,上午游玉泉观鱼、栖霞洞等景点,“下午四时归。因火车六时快车开车,匆忙收拾行李,乘车赴宁”。这是《北平日记》中有关两人会面的唯一记载。这次杭州之行,容希白在南下之际似已有所计划,《北平日记》记其于6月23日在船上致信邹适庐,应是预先告知对方自己将有杭州之行。
在邹适庐的信中,也有这次会面的一些记载,可与日记所述互为补充。第三十八函(图2)提到:
十六日下午奉访不遇,当交扇页一,敬托书钟鼎(写在金面)。六时再访,知大驾奉高堂已趁车赴沪,怅怅而返。
十六日当为农历七月十六日,即公历9月3日,与《北平日记》所记9月2日下午离杭赴宁有左,应是邹先生的笔误。除了日期略有出入外,信中所述其他细节与日记所记相符:其当天下午第一次到访不遇,当是在四点前,容希白尚未回到旅馆;而六时再访时容先生已乘火车离杭,但邹先生并未清楚其直接赴宁,故称“赴沪”。而据邹函可知,此次因“暑疖初愈忌口,致未能一尽东道”。
《北平日记》仅记载了两人在1925年的这次见面,但此后两人实际上还有一次见面:
前接复函,知大驾即日北上,现想已到校矣。(第八十一函,六月廿九)
月初承顾,以适患暑湿,不能奉陪清游为歉。(第八十二函,七月十九)
前至杭,承嘱写屏二条,即日写寄广州。(第八十三函)
按,此数函均未署年份,但考察《北平日记》的相关记载,以及其前后各函的时间,可推知是在1930年夏天。在《北平日记》中,2月23日至8月1日等时间失记,不过仍有一些线索可查。该年“收支一览表”中记载4月的支出中有一项“十七日,往申船费36”,6月的支出则有“游杭20”一项。按,是年4月19日,容母邓琼宴太夫人病逝。而据日记,早在2月21日,容希白已经“接家电二封,云母亲有病。与八妹回家省亲,收拾行李”,次日即与容媛同行前往天津。当容先生办妥母亲的后事、重新北上时,应该仍是搭船经过上海,并在上海、杭州逗留,因此才有杭州之游。此次杭州之行仍往拜访邹适庐,但凑巧的是,邹氏依然因病无法陪其清游。这次见面,容庚请邹氏为其写两条书法屏条(八十二函“委书二件,即买纸写寄,特不工耳”),同时携去邹氏之《汉金文存目》稿本等。第八十二函称:“敝编目错误不少,还望于披阅时签出。如有漏列之件,亦祈注明。”八十三函又言:“又承携去《汉金文存目》及释文等,因拟秋凉即印,曾函索挂号保险寄转,以便理校付印,未蒙示复。”均涉及容希白此次杭州之行及其携走之《汉金文存目》。容希白于八月廿三日复函称“大著稍缓奉还”,至十月七日所写之信(图3)则“尊目奉还,敬希察入”,且谓:
大著《汉金文存目》,匆匆校对一过,为庚所见而未收者百数十器,兹将目录呈。尊目中颇有疑伪之品,不知尊意如何,故未签出。亦有尊目有而庚目无者数十器,意尊目所有不尽为左右所藏,故不复请检寄,以俟他日补遗可耳。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容希白请人过录了这份目录作为副本自存,并在其中详细标注所收存疑或伪作之器,以及该目著录而其本人失收之器。
1930年,在容希白夏天杭州之行后,两人仍有多次通信,其中邹适庐在第八十五函(9月23日)提及“前接手教,知《汉金文》尊编亦成,鄙辑并承改正未见各器”,“鄙辑希双挂号寄,庶免遗失”等语,当是对前引是年8月23日容札的回应。到了1931年,他们之间的通问渐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邹适庐当时患了一场大病,几至不起。第八十六函(1932年初)称:“前致函后,即病类中,至今方能起立握管,几与公等诀别矣。”同时还希望:“尊编《汉金》已印成,还希以一部寄我,该价示及奉缴。”直到1932年4月13日,容先生寄去一部《秦汉金文录》以作邹先生女儿出阁的礼物。是日日记载:“午作文。寄三弟《秦汉金文录》三部、邹适庐一部(嫁女礼)。”邹适庐在女儿婚事结束之后阅读该书,并作复长函(第八十七函,图4):
小女出阁,承惠《秦汉金文录》为纪念,至谢!此书颇以早睹为快。今以嫁事,至昨日始得展阅,收罗之富,鉴别之慎,似过他书。惟鄙藏小犛量,既已收入,复疑为伪刻诏书,未明尊旨。以为勺者,刘晦之所言。彼亦得一器,无背文,余未之见,兄以为加刻则不敢辩。至敝藏则经叔言一再索让(定三百元),弟不愿让,几因此绝交。后张修府、陶北溟均允五百元。晦之未得小勺前,亦曾索让。(王静安于赛会不止一见,亦以为精品。静安多疑,于此器独不疑后刻。)岂彼数人者,皆不能鉴定耶?若以旧拓只一“犛”字,安知非另一器?以为汉器只一“犛”字,犛,地名也,不知是汉何地?见于《汉书》何卷?还希有以教我。集中所登新郪虎符,定为秦制。查《汉地理志》,新郪是汉始名,则犛即为汉地,亦可谓仍秦之旧。(原器末一之字已蚀,实止四十字。既欲作伪,何不并刻之?且新刻与旧刻迥然不同,汉篆与秦篆亦显然相异。)吾兄见秦器已多,想必能会悟及之。诚如尊论,一器而数易主张者有之,弟为此论,非护己之短,且防他日出售之不利,实公意,非自以为是。如前代友人受过,未便一辩。大约见识与年俱进,若处穷僻之乡只有退步,正弟之谓矣……
此信主要针对容希白在《秦汉金文录》中将其所藏小犛量上的诏书铭文定为伪刻,反复强调该器经罗振玉、王国维、张修府、陶北溟等认可,力辩其非伪,其中“岂彼数人者,皆不能鉴定耶”“大约见识与年俱进,若处穷僻之乡只有退步,正弟之谓矣”等,言辞之激,此前各函未见。
据《北平日记》,容希白是年5月17日“寄邹景叔、张荫麟、叶慈信”。寄景叔此信,当系对邹适庐此第八十七函的回复,惜其内容不得而知。此后,直到1940年邹适庐去世,在《北平日记》中,未见再有包括书信往来在内的与邹先生有关的记载。因此,1932年可视为二人交往的最后一年,第八十七函也成了邹适庐致容希白的最后一封信。
容、邹二人在交往了十一年之后最终绝交,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二人在鉴定邹适庐重要藏品中所出现的争议应该是其中颇为关键的因素。
在交往过程中,二位先生表现出不同的处事风格,在鉴定藏品真伪的方法和结论方面也经常出现分歧。容先生为人处世的一贯作风就是比较坦率,对友朋的观点、藏器等有不同意见者都能直陈己见。从给邹适庐的第二封信开始,他就经常指出邹氏著作中的一些失误。如邹氏的第三函是对容希白来信中指出的《广仓专录(专门名家)》误收伪潍县陈氏簠斋藏十砖的情况进行解释;第六函“今又奉手书,并校定殷甲骨误处,容交静安后,并入校勘记”,当是容希白对王静安所撰《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所提意见的回复。这种情形几乎贯穿在二人交往的整个过程。而邹适庐在涉及对方藏品真伪问题时却显得较为委婉。如容希白曾从广东寄一旧拓《皇甫碑》给邹先生,请其帮忙出售。邹适庐先是说“碑拓甚旧,第不知何本”(第四函),后又称“《皇甫碑》如唐宋拓,足值二千金。此本则各藏家均不能定,只得挂号奉璧,以待识者”(第五函),并未直接指出其存在的真伪问题。对待各家藏品直抒己见,是容希白的一贯作风。他对邹适庐的藏品如此,对民国大藏家刘体智先生的藏品也如此。笔者在考察容希白与刘晦之两人的关系时,认为二人之间的关系堪称学者与收藏家的关系的典范,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容希白虽然对藏品直率、坦诚地加以品评,而刘晦之则采取各存己见的处理方式,使两人不致因此出现冲突。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刘晦之的这种大度。尤其是邹适庐,在离开哈同花园之后,经常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或收入不丰,经济比较困窘,日常家用需通过帮友人编书、销售藏品拓片乃至藏品作为帮补。在信中,他多次提及自己的窘境。如“弟家无儋石储,如闲居即须售去古物以为食”(第九函),所藏“各器售去者多……坐吃不能不售,亦境遇使然。今年度岁,明春仍此,势必并戈剑秦汉器而售之矣”(第二十函),“铜器迟早须让与友人,以充家用”(第二十一函),“下旬或至沪售去藏物,以充口腹”(第六十六函)。因此也导致在编书时虽明知所编器物有问题,但仍不得不有所迁就:
《获古》一编,内多缺憾,承示甚是。去岁无可为计,梦坡顾我,意在救穷,故不得不勉就,明知所藏不满人意也。(第六十四函,图5)
对其较为重要的藏器提出质疑,容易影响这些藏品的出售或价格(他本人在第八十七函中就明言“弟为此论,非护己之短,且防他日出售之不利”),这对收入不稳定、经常需要出售藏品以维持生计的邹适庐而言确是一个较大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在自家重要藏品的真伪问题上持一种较为较真的态度。他在第八十七函中这种较激烈的反应迥异于他往常对待容希白的其他观点或指谬时大度接受或坦诚说明其中委曲的做法,由此正好说明容希白在未见实物的情况下判断其重要藏品有问题对他本人可能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而容希白率直的性格则很难令其在重要藏品的真伪问题上作出有悖于自己判断的退让。因此,断绝交往似乎成了一种难以避免的结局。在第八十七函中提及之“刘晦之”,即刘体智先生,为民国时期海上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所藏甲骨、青铜器、书画、古籍等极夥。凑巧的是,在与邹适庐日渐疏远的同时,1931年,容希白结识了刘晦之,并逐渐成为挚友。刘晦之数量众多的藏品,无疑能够为容希白的治学提供更多更有力的支持。容、邹二位先生关系的疏远,与此或许不无关系。
容、邹二位先生的交往,具有较为典型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交往的特色。通观他们书信的内容,除了日常的互通信息、互赠著作、拓片及本人书、印等礼品之外,有两项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一是委托彼此代购或寻觅书籍、金石资料等,金石拓片是其大项;二是对金石器物的年代、真伪以及对某些文字的考释问题的讨论。
如前所述,容、邹二人书信往来超过十一年,期间曾有两次晤面。从其关系的变化来看,他们交往的这十一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1921年初首次通信,到1922年容希白进入北大国学门之前;第二阶段则从容先生进国学门后直到1930年;第三阶段为1931、1932两年。在第一阶段的通信中,邹适庐经常为容希白代购书籍或提供拓片(图6)等资料,如第八函(图7)就提到:
委购各书,兹照买奉。《学术》等四种,邮票五元冲讫……《周金》卷六、《草隶存》入四元八角,又挂号二角□分,净存四元。馀拟属拓工拓小屏幅四张……
反之,邹先生对容庚从未有此方面的要求。从第二阶段一开始,这种邹适庐单方面为容希白提供资料的情况迅速转变。容希白一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邹先生即托其觅寄相关章程,作为拟议中的浙江国学讲习所章程的“蓝本”(第十五函)。随着容先生在北京学术界尤其是金石学圈子人脉关系的建立和地位的上升,其所能接触到的金石资源日渐增多,尤其是北京,不但拥有故宫这一巨大宝藏,民间还有庞大的文物市场,经常可以见到新出之器,资源异常丰富。反观邹适庐,因上海住房租金较高等原因,在两人开始联系的那年,他便迁回杭州定居。但杭州的同行不多,资源也少,他曾多次感叹“杭城少古铜器,惟玉器有甚古者”(第十五函),“第此间文字之交不多,古物亦极销沉耳”(十四函),“杭州少好古者”(第十八函)。另一方面,在杭州,他也基本失去广仓学宭这一征集、接触包括金石拓片在内的各家所藏艺术品的便利条件和平台。因此,就需要更多地借重容希白为其搜集北京方面的资料。在第八十六函,仍委托容庚觅购宗周钟拓本;即使在最后一封信中,还是很客气地附言:“确当可收各器,俟有暇检数品寄上。”足见他非常重视与容希白的交往。当然,在这一阶段,容希白也经常借助邹适庐搜集浙沪方面的资料包括邹氏本人的藏品。因此,在第二阶段,两人之间在资料搜集方面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互惠的关系。到了第三阶段,两人的交往突然因各种原因变少乃至绝交。
尽管二人的关系客观上以绝交告终,但回望二人的早期关系,尤其是邹适庐对待容希白的态度,确实颇令人称道。
从第一函的内容来看,邹适庐虽然长容先生三十岁,但他对这位前来请益的晚辈非常重视,对其来信,大多数都能认真作复。如果说他在第一函中赞誉容希白的话语,或多或少有初次来往时的客套成分,但从随后各函就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同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所写的第六函中,邹适庐请容庚为自己刻印、写斋额:
新得建初尺一,又旧藏秦升量一(古以一手为一升,故升从手,《椒聊》诗“藩衍盈升”与下“藩衍盈匊”对咏。匊为两手,升为单手),颇思以“秦升汉尺”名斋。能为刻一章否?并书一额尤感。
仅此一事即可见其对这一未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偏爱。而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则一直平等视之,从未以成名已久的长辈自居,始终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
邹适庐对容希白慧眼识才,青眼有加,而容希白对邹适庐也颇为敬重。今仅举一例:如前所述,1925年3月25日,在《金文编》抄写接近尾声之际,他写信向邹先生索序。《金文编》初版时,除自序外,其他作序者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沈兼士、邓尔雅五人,此数人对容希白而言皆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容庚请邹适庐为《金文编》作序,足见当时邹氏在其心目中绝非泛泛之交。可惜当时被邹先生婉拒:
《国学》四册早读,内《金文编序》已见大概。印稿能全惠,自当竭其所知以尽忠告。至作序,恐不足弁冕,还请雪老为之。(第三十二函)
容希白亦曾请邹适庐为自己书写斋额(第七函:“委书二纸均极不佳,然额屡写不惬意,只得奉寄,以之覆瓿可也”)。他对邹氏的一些意见也颇为重视,如在书写时间为七月七日的信中提到:
齐侯中罍闻在沪某氏,器已破碎矣。承惠拓本,至谢。□□□诸字,向所未见。余方欲重订《金文编》,得此良佳。柱饰文曾见于《金石蕃锦集》,以左右言,故未收入。
而邹适庐早在二人交往的第一年即告知“《蕃锦》所收之多字器系伪作,汤某已自认之”(第十一函)。
由于二人的研究领域多有重叠之处,所以他们在资料的需求上也多有重合。对此,在交往过程中,两人能够互相交换信息、资料,彼此支持对方的工作。邹适庐编有《周金文存》,随后即着手编纂《汉金文存》;而容希白则先编有《金文编》,随后亦编《秦汉金文录》。在这过程中,两人经常互相交流,在材料上互通有无,这在二人来往信函中有大量的反映。1930年夏天,容先生在杭州之游后继续北上,即随身携去邹适庐之《汉金文存》目录稿本。经过认真的校对,将其本人所见而该目未收的百数十器开列成一目录寄回邹先生。容先生还请人过录了一份邹先生目录的副本自存,并在其中详细标注所收存疑或伪作之器,以及该目录著录而容希白本人失收之各器。由此一例,亦可见两人在治学中的相互帮助和影响。
当然,二人在交往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矛盾,其中最多见的是对一些器物或铭文的真伪判断出现分歧。多数情况下,邹适庐认同容先生的看法,但不时仍有较大的分歧。如第二十四函谈道:“去年承委拓敝件,匆匆倩工,并未审择,惟不佳者多,伪品颇少。贵同校诸君所见不多,但观拓本,何能定之?”第七十七函也委婉指出容希白未见原器即断其真伪:“前器确系周器,惟非即宫内之物……该器罗叔言亦以为真,来函云仿制,未见原器……”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两人在鉴定理念上的差异。如第六十四函在讨论有关器物真伪时谈道:“如平戎鬲均以为伪,而朱椒堂有释文,原器未见,鄙处有一未剔本,知决非宋仿。弟凭良心言,亦以近时流专以文字之精否定古器。”第六十五函:“以文字精否定古器真伪,此罗、王二君新见,弟不尽为然。”此罗、王新见,也就是容希白所采用者。两人之间的这种分歧一般不会导致严重的影响,但如前所述,当分歧涉及邹适庐自藏重要器物而且无法调和时,二人的矛盾就容易被激化。
容、邹二位先生的交往,无疑是民国时期金石学界和收藏界不容忽视的一段掌故。对于早年的容希白来说,邹适庐无疑是一位伯乐式的前辈。在其尚僻处东莞乡陬之时,邹适庐即能慧眼识才,对其才艺赞赏有加,虚怀若谷,与之平等讨论金石文字的问题,并为其提供或代买金石拓片和其他出版物,这对容希白早年的治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而通过研究二人初期的交往,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容希白北上之前的学术活动。由于二人的研究领域接近,因此彼此之间的金石资料交流和学术探讨活动对各自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二人在经过十一年多的交往之后最终断交,其间应有很多因素,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新老两代金石学者在治学理念等方面的分歧,尤为值得进一步的思考。限于篇幅,本文仅根据来往信札对二人的交往的大概情形作出粗浅的考论,期望抛砖引玉,能引起学界的关注,进一步研究容、邹二位先生的交往,同时对这批信函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图文综合来源网络,部分配图为编者所加。分享此文旨在传递更多有价值信息之目的。 和万千书坛精英,一起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原文不代表书艺公社观点、立场以及价值判断。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与书艺公社联系。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