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的记录,是从一份实验报告里发现的。
没人想到,这份编号模糊、格式混乱的手稿,最后成了731部队内部最沉重的一页。
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卷起,墨迹有些模糊。
最开始注意到这份档案,是因为最后一行手写的字。
不是医学术语,也不是实验数据,而是一句简短的感叹:“他是我见过最顽强的人。”
起初没人在意。731的档案那么多,活体实验、细菌培养、解剖记录堆成山。
可就是这句话,让人停了下来。
谁?为什么说“顽强”?这到底是哪一桩实验?
细查之后,才发现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记录。
时间是1942年夏天,地点在哈尔滨郊外的平房区。
那时候,731部队正处于所谓“研究高峰期”,日本军方急着要看到成果,尤其是针对鼠疫病菌的应用实验。
据档案所写,那天早上接收了一名“华北送来”的试验者。
没有名字,身份备注里只写了六个字:“敌后游击人员”。
也就是说,这人是从八路军控制区抓来的,具体是哪个地区、哪支部队,不清楚。
只有一句话反复提及:“感染后依然存活两周以上,器官无明显衰竭。”
这就不寻常了。731的那些“实验对象”,在感染鼠疫菌后,常常撑不过三天。
高热、败血、器官坏死,都是极其迅速的过程。
可这人,居然撑了十几天,还能进食,还能睁眼。
有个助手在记录边上写了一句:“注射樟脑液后,睁眼、转头、无言语反应。”
那会儿的解剖室,叫“特别班”,也就是731内部负责活体实验的核心小组。
执行手术的是中尉细岛,原是兽医出身,转来部队后一直在处理“特殊样本”。
他的助手是筱冢良雄,见习军医,才二十多岁,刚从军医学校分配来不久。
那天的细节在日记里有不少补充。
筱冢记得,那个被送上手术台的人,早上还跟他打过照面。
对方当时还冲他笑了一下,说了句:“你这药打得真慢。”谁都没料到,几个小时后,他就成了“解剖对象”。
手术开始前,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领导是少佐大木,直接下令:“用樟脑液,防止中途死亡。”按医学常规,樟脑液是刺激心脏、维持循环的药物。
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义就完全变了——是为了让人“在解剖中尽量活着”。
注射之后,那人猛地睁开眼。
不是痛苦的挣扎,也不是求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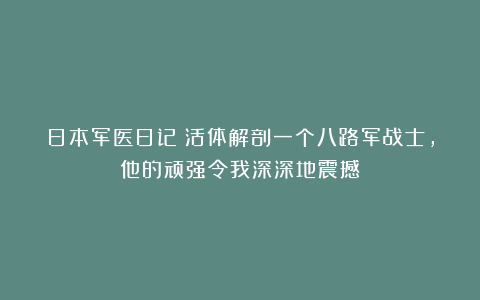
他只是看了一眼操作台上的人,没说话。
一个日本助手吓得差点掉了钳子。
“他一直盯着我看。”这是筱冢后来写下的。
他说那眼神不是愤怒,也不是恐惧,是一种…像是“看穿你”的冷静。
接下来的过程,残忍得不适合展开描述。
只说一点:他们用了六针强心剂,还是没能维持住心跳。
最后的记录是:“口角抽搐,终止呼吸。”
后来的分析报告指出,这人的心脏、肝、肺、肾几乎没有明显坏死迹象。
按理说,鼠疫到了这个阶段,早该五脏俱损。
可这个人没有。
更让研究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肌肉和神经系统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也就是说,他一直在强撑。
战后有些人说,这可能跟他的身体素质有关。
但筱冢在笔记里写得很清楚:“他不是靠身体,而是靠意志力坚持到最后。”他说自己当时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人,不是你用刀能征服的。”
这人究竟是谁?资料里没有名字。
后来有人查过731的转运记录,发现1942年6月,从河北冀中地区押送到平房基地的有一批人,其中一人登记为“八路军敌后联络员”,被标记为“重要对象”,编号是“476”。
但这个编号很快被涂改了,后面也查不到了。
那段时间,冀中平原正经历“铁壁合围”。
日军动用了十几个旅团,试图彻底压制八路军根据地。
根据《冀中抗战纪实》记载,很多交通员、地下联络员在那时失踪,很可能是被捕后秘密押往东北进行“技术处理”。
细岛中尉后来被苏联抓获,在哈尔滨受审,判处25年徒刑。1956年移交回日本,几年后病死。
他在审讯时只说了一句:“我当时以为他是死神本人。”
而筱冢良雄,战后在东京大学任教。
曾在一场讲座上,公开讲述过这段经历。
他说:“那个战士死后,我再也没敢拿手术刀碰活人。”
几十年过去,那个无名的战士依然没有墓碑,没有照片,连名字也没人知道。
可关于他的那页日记,被翻出来后,被复印、翻译,留存进了几本重要的战时档案集中。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那样写“马鲁他”这个词了。
参考资料:
石井四郎,《细菌战与731部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王选,《冀中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档案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