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Jan Zalasiewicz, Julia Adeney Thomas, Colin N. Waters, Simon Turner & Martin J. Head
虽然地质学家没有接受“人类世”(Anthropocene epoch)的说法,但二十世纪中叶地球发生重大转变的概念,在物理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政策领域仍然很有意义。
“人类世”的概念,意在代表人类对地球造成的巨大影响。来源:Bob Krist/Getty
2024年3月5日,国际地层委员会(ICS,负责地质单位定义的机构)宣布,它否决了正式采纳“人类世(Anthropocene)”作为一个地质纪元的提案,以体现人类对地球势不可挡的影响。ICS的第四纪地层委员会(SQS)2009年成立了人类世工作组(AWG),启动了这个流程,我们是这个工作组的代表。AWG的目的在于理清是否有充分证据正式采用人类世,这一过程包括了在特定地质层(地层)中确定一个精确的起始点。
这一否决引发了许多争论,双方都表达了强烈的观点。但过去十年间,人类世这个词已被广泛采用,用于描述、分析和解释人类如今生活其中的、已经今非昔比的环境。
目前,不同群体主要通过四种方式使用这个词。首先,这个概念出自地球系统科学界,该领域和相关科学学科用它模拟、评估和警告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对环境“地球界限”的逾越[1]。其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用它来理解人类影响如何最终压倒了许多强大的自然力量,以及这对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何种影响[2]。其三,人类世启发了许多博物馆和艺术界的工作。其四,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城市规划者等使用这个概念来理解人类对气候和生物圈的改变,这对制定和实施管理、缓解与适应政策是必需的[1]。
既然正式的“人类世”地质定义已搁置(至少目前如此),在此,我们探讨了如何能在考虑到这些广泛群体的情况下最好地理解和使用这个概念。从专门和一般用法上来看,什么是人类世的基本含义?
地质起源
人类世由大气化学家Paul Crutzen于2000年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一论坛旨在讨论全球变化。Crutzen意在使之代表一个与委员会目标一致的新地质时代[3]。其目的并不仅仅为了意指一个被人类改造的地球。地质学上,重要的人因影响可以追溯到全新世——我们仍生活在其后冰期地质时代,以及之前的更新世。全新世的典型条件包括相对稳定的大气和海洋化学物质及气候(尤其是温度),还有大约7000年前以来相对稳定的海平面。Crutzen提出,“人类世代表着地球系统从这些条件朝着一种不可逆的、仍处在演进中的状态转变,全新世这一名称已不再合适。”
各种环境标志物(如不同温室气体的含量)惊人相似的模式,见证了一个突然的转变,近似于在全新世纵横轴上从水平变为垂直。Crutzen起初认为,偏离全新世环境发生在工业革命的起始以及18世纪末欧洲燃煤增加[4],虽然他提出这一观点时,IGBP的数据还有没扩展到那么久之前。在获得更多数据后,20世纪中期的开端变得更明显[4],联系起了“大加速”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经济学驱动因素和地球系统反应。
对这一转变已有详细的阐述[6-8]。其主要特征包括:大气化学成分改变;气候变暖;如今已不可逆转的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加速侵蚀和沉积;工业产品激增,其中许多由塑料等人造材料制成;经由物种入侵、驯化和灭绝发生的生物圈改变;以及人类开发的技术系统构成全球互联的“技术圈”的迅速发展[9]。
提议的背景
这一初步研究推动了确定人类世起点的工作,即在一个称为全球标准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常被称为“金钉子”)的地质参考层确定其起始点。从2020年到2023年,12个研究小组在五大洲的8个不同地质环境中提出了候选GSSP和其他参考剖面。
经过多次讨论和正式表决,AWG选择了1952年加拿大克劳福德湖分开夏季与秋季的沉积物层的水平面。秋季层的特点是钚同位素明显上升,与第一次大气氢弹试验吻合[10]。这一信号在许多提议地点都清晰可见(见“一致的边界”)。克劳福德湖入选是因为它有不受扰动、季节性沉积的沉积层,保存下了精确、连续的历时记录,未来研究容易获取,而且位于保护区,处于受保护状态。每年解析的钚数据得到粉煤灰、氮同位素和生物标志物的支持。为了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日期,选择了与第一次大气层氢弹爆炸(称为Ivy Mike)相同的时间:1952年11月1日当地时间7:15(格林威治时间10月31日晚19:15),地点为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埃内韦塔克环礁(Enewetak Atoll)。
来源:参考文献7
通过大量地层信号,在全世界这些地层能精确地互相关联[6],某些地方能精确到最近的年份,使得人们可以在这些沉积所代表的时间界线前后的过程进行系统性的定量比较。这一提议已由工作组于2023年10月31日提交给SQS。
人类世的范围
在地质时间尺度定义人类世的想法,是为了给上述诸多现象的综合研究提供一个精确参照,将当代的变化置于深时背景中。但是,正是现世的、被体验到、观察记录下的现象,超出了地质学的范畴,引发了对人类世更广泛的兴趣:这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兴趣,因为最初的人类世指导概念应对的是地球的宜居条件。
在“人类世”时期,与全新世大部分时候相比,地球表面环境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地球更热、污染和生物退化更严重。这些负面趋势将会加剧并扩展到全新世包络线之外[1]。这当中有些变化会长期持续(如气候变化),有些不可逆转(如灭绝)。它们已经对政治机构、法律框架和经济关系造成了压力,这些都意在保护人类社区并赋予其意义。
代号“Ivy Mike”的第一个氢弹于1952年爆炸,标志着人们提议的人类世开端。来源:Bettmann/Getty。
在这些更广泛背景下讨论人类世,精确定义年、日、时通常不那么切题。我们也要指出,稍微改变较早地质时间单位的正式边界,通常不会导致对其基本理解的改变。例如,2008年,另一个SQS工作组改变了全新世的定义,从距今10000放射性碳年改成从地层学角度正式定义的距今(2000年)11700年前[11],但并未改变其作为最近一次冰期后的间冰期的基本定义。
第四纪的定义也值得参考。这个单位包括了更新世和全新世,设立于2009年,它开端于约260万年前,出于实用目的使用了此前存在的GSSP和地球磁场的大反转。实际上北半球冰川加强开始得稍早一些,大约270万年前,但这并未改变这一时期作为“冰期”的一般含义[12]。更早的时期可以发现其他类似的例子。控制地质年代单位概念的并非精确概念,而是它们所框住时期的基础特征。尽管如此,增加这些边界的明确性会让地质时间单位更一致实用。
我们在本文中认为,将“人类世”理解为20世纪中期地球范围变革的结果,在各个学科中仍然有用。这一时期与“大加速”(该术语由美国历史学家John McNeill提出)及其近义词(如1946-1990年间的“二战后经济腾飞”“日本经济奇迹”,以及描述法国1945-1975年间不断经济增长的“美好时代”等)紧密相关,许多描述人类影响的指标,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金属和矿物生产、肉类消费和使用塑料,在上世纪中开始显示出强劲的上升趋势(见“转折点”)。
“人类世”的概念,意在代表人类对地球造成的巨大影响。来源:Bob Krist/Getty
在历史学家看来,战后时期的特点是世界许多地方的社会价值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民主、社会福利计划和女性教育的广泛传播与普及。这些变化来自于全行业工业、贸易和商业全球化的增长。不同阵营国家尽管争夺权力,但双方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仍引领着这些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等机构通过国际协议建立起来。技术进步也带来了农业粮食生产,推动了人口全球高增长率[2,13]。
对人类学、政治学理论、国际法和伦理学的研究者来说,问题开始涌现:在此期间,人类力量开始支配生物网和非有机过程,这造成了何种影响。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应对一个已经改变的地球系统,其中不同文化根据自身世界观,体验、理解和做出应对。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能源、食物、住房和衣物的科技领域扩大,伴随着全球不平等的加剧,最贫困人口实际收入的增长非常微小。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关于无限增长能力的假设,也因人们认识到日益不稳定的地球系统和有限地球而受到了挑战。
有人曾提出更早的人类世开始时间,但我们认为,这些标准未能突出20世纪中期的变迁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迁可通过大范围指标来衡量。其他建议包括1610年前后的“世界指标(Orbis spike)”,对应着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下降约10ppm[14]。这一下降被认为是缘于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后,美洲原住民大量死亡,带来的人口下降、耕地减少和森林重新生长。但相较于过去两个世纪里二氧化碳140ppm的增长,这一下降幅度很小,时间很短,而这一增长趋势还将持续。在美洲和欧洲与物种的“哥伦布大交换”(如玉米花粉的存在)有关的地层学信号,则在数个世纪里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它们并未体现出与20世纪中期所见相当的那种突然的、根本性的全球变迁。
塑料产品和其他废物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为增长。来源:Jason Swain/Getty
基于地层学信号的其他边界也可能遭致类似的反对,例如,在欧洲泥炭沼泽和格陵兰冰层中,发现了约3000年前的铅冶炼迹象[15]。有人提出将“人类世”概念进一步上溯,包括了至少5万年前的“人类世事件”——这个定义覆盖了古希腊帕特农神庙、中国的长城、希腊的金字塔、早期森林砍伐、中石器时代的箭头,甚至包含了更新世晚期的大型动物灭绝[16]。
地质学上做出正式定义,将加强人们对20世纪中期地球重大变化的承认。但即使只是将之视为一个准正式边界,也反映出现实[17,18],并鼓励所有学科进行明晰的交流,其中“人类世”一词已被用于概括环境巨变。随着时间推移,对所有人类活动造成的重大影响的解释各不相同,如果都标之以“人类世”,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人类世是什么?不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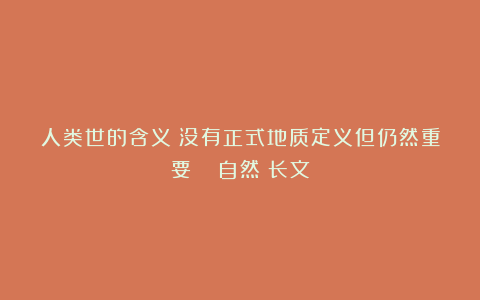
除了讨论人类世从何时开始最为有用,它在流传之中也被多种学科以许多方式加以阐释。在我们仍高度各自为政的学术环境中,问题常反映出日益歧异的观点和日渐消失的共同理解。这些差异应得到探讨,并在必要时加以挑战。
人类世是否罔顾社会政治不平等?在创造和使用“人类世”一词时,一些批评认为地球系统科学家和地质学家将责任一视同仁地加诸全人类,而非那些大举过度消耗资源的人——而他们正是主要造成(并仍在制造)地球状态改变的人。
会产生这一误解,是因为人类世物理科学的目标与过程与人文社科有所不同。物理学在此主要关注的是测量和描述如今压倒性的人类影响在地球上造成的反应。研究者通常不关心将责任归诸特定人群或特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尽管自这一概念提出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人为变化的责任严重不均,一些研究[5]也纳入了这些关联。物理科学也很少探讨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反应,或人们渴望和希望背后的价值。
因而,在人类世研究中,存在一种学科工作的分工或谱系。物理学家研究人类世期间地球对人类影响的反应,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研究这些影响背后的人与社会。对大多数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来说,不平等是人类世社会政治学分析的核心。这些方法并无对立;这里理解的人类世提供了一个框架,指向互补和多学科性。
人类世是否等同气候变化?大气中温室气体上升导致的近期快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提出了明确威胁。尽管存在控制排放的努力,每天仍有超过1亿吨二氧化碳加入地球大气。虽然气候变化现在是使地球系统陷入不稳定的最重要力量,人类世也包括了许多其他物理、化学和生物变化,与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现象相关联。
采矿业等不断扩张的活动在地球上留下了印记。来源:Anton Petrus/Getty
2000年Crutzen提出这个术语的时候,大气二氧化碳水平“仅”约370ppm,比工业化前最大浓度高85ppm。平均全球气温大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0.5 °C(以1850-1900年的平均值为标准),因此仍处于全新世其他时期达到的气候条件范围内。2000年,变暖可能被认为才起步:但彼时的地球系统整体改变也已经支持了Crutzen提出新地质世的提案。到2022年,大气二氧化碳水平接近420ppm,平均升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 °C。考虑到其他温室气体的影响(尤其是甲烷、二氧化氮和氯氟烃),使2022年大气CO2当量达到约523ppm,这一水平自中新世中期(约1700万年前)以来未见。因此不奇怪地球整体上比全新世任何时候都要热。同时,生物多样性损失和地球曾经独特的生物地理组合日益同质化,也构成了人类世的另一重要方面[19]。气候变化是人类世的一个重要组成,但并不能定义人类世。
人类世是否与它的成因同时开始?地质世的边界一般不从行星转变的起点开始,而是从能够很好识别和操作性使用的点开始。许多不断演进的发展、活动和观点最终带来了地球系统在20世纪中期的变化。它们能追溯到智人(Homo sapiens)的兴起、掌握火的使用和复杂交流技巧,以及动物驯化、农业、城市社会、书写系统、全球贸易、蒸汽机、资本主义、哈伯-博世肥料生产工艺等等。人类世的原因必然早于这个世的开端。作为类比,11700年前全新世的正式定义,是一个漫长、复杂、阶梯模式的变暖和冰川消融带来的海平面上升走向终结,冰川消融开始于约8000年前[10]。随后,全新世作为一个间冰期与此前的间冰期并无太大不同,它为文明发展提供了物理条件,而人类世正在推翻这些条件。
共识
人类世最初被Crutzen理解为不仅代表人类对地球地质记录的影响(他很清楚早期人类活动的影响),还反映出自广泛的工业化以来,一个系统的物理特征已经偏离了全新世长期相对稳定的条件。
人类世概念可以锚定开始于20世纪中期,与“大加速”和地球根本状态转变相吻合。以这一方式理解人类世,将避免当前这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中指向不同含义的混乱。它符合这个术语起初试图表述的含义,也反映出清晰的基于证据基础的地质特征[20]。这个概念与地球系统科学中这一术语的使用一致[21],也符合更广泛的使用,如新兴机构(如韩国大田韩国科学技术院人类世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皇家理工学院人类世历史卓越中心和德国耶拿马克斯·普朗克地球人类学研究所等)对术语的使用。它强调了应对社会忧虑的问题时地质学的作用,也可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讨论已经发生的重大社会动荡、能源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变化。政策和国际法也能受益于一个明确的定义,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里,地球的运转已经由于压倒性的人类影响而发生转变。
参考文献:
1. Rockström, J.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21, e2301531121 (2024).
2. Thomas, J. A., Williams, M. & Zalasiewicz, J. The Anthropocene: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Polity, 2020).
3. Crutzen, P. J. Nature 415, 23 (2002).
4. Zalasiewicz, J. et al. Quat. Int. 383, 196–203 (2015).
5. Steffen, W., Broadgate, W., Deutsch, L., Gaffney, O. & Ludwig, C. Anthropocene Rev. 2, 81–98 (2015).
6. Waters, C. N., Turner, S. D., Zalasiewicz, J. & Head, M. J. Anthropocene Rev. 10, 3–24 (2023).
7. Waters, C. N. et al. Preprint at Earth ArXiv https:///10.31223/X5MQ3C (2024).
8. Zalasiewicz, J., Waters, C. N., Williams, M. & Summerhayes, C. P. (eds) The Anthropocene as a Geological Time Unit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9).
9. Haff, P. K. in A Stratigraphical Basis for the Anthropocene (eds Waters, C. N., Zalasiewicz, J., Williams, M., Ellis, M. A. & Snelling, A. M.) 301–309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2014).
10. McCarthy, F. M. G. et al. Anthropocene Rev. (in the press).
11. Walker, M. et al. Episodes 31, 264–267 (2008).
12. Head, M. J. & Gibbard, P. L. Quat. Int. 383, 4–35 (2015).
13. McNeill, J. R. & Engelke, P.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 (Harvard Univ. Press, 2016).
14. Lewis, S. L. & Maslin, M. A. Nature 519, 171–180 (2015).
15. Wagreich, M. & Draganits, E. Anthropocene Rev. 5, 177–201 (2018).
16. Gibbard, P. L. et al. Episodes 45, 349–357 (2022).
17. Syvitski, J. et al. Commun. Earth Environ. 1, 32 (2020).
18. Syvitski, J. et al. Nature Rev. Earth Environ. 3, 179–196 (2022).
19. Williams, M. et al. Palaeontology 65, e12618 (2022).
20. Kuwae, M.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in the press).
21. Steffen, W. et al. Earths Future 4, 324–345 (2016).
原文以The meaning of the Anthropocene: why it matters even without a formal geological definition标题发表在2024年8月26日《自然》的新闻评论版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