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齐白石(1864—1957)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以“衰年变法”突破传统束缚,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大写意花鸟画风。晚年的齐白石,虽体力渐衰,但艺术创造力却臻于化境,其作品展现出返璞归真、浑然天成的气象。其中,关于他人生最后的画作,学界曾有过争议,但近年研究证实,一幅名为《葫芦》的作品被公认为其绝笔。本文将从绝笔之谜、艺术特色、文化寓意及晚年创作状态等多角度,解析齐白石晚年艺术的“人画俱老”之境。
一、绝笔之谜:从《风中牡丹》到《葫芦》的考证
齐白石的绝笔之作,不仅是艺术史研究的焦点,更是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化公案。坊间关于其最后一幅画的争论,既涉及家族记忆与学术考证的碰撞,也折射出大众对艺术家生命终章的浪漫想象。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绝笔之谜”,最终在多方证据的交织下,指向了一幅看似平凡却直抵艺术本质的《葫芦》。
1. 争议的缘起:家族记忆与历史迷雾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世于北京。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最富盛名的画家之一,他的离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悼念,而关于其“绝笔”的讨论也悄然兴起。其子齐良迟曾在回忆录中提及,父亲生前最后一幅完整作品是《风中牡丹》。
这幅《风中牡丹》以大写意手法绘制:画面中央一株牡丹迎风而立,花瓣以洋红泼洒,叶片以浓墨挥就,枝条的倾斜角度极具动感。齐良迟认为,此画完成于白石去世前三天,牡丹的“风中之姿”暗含艺术家对生命最后时刻的坦然与礼赞。家族成员的支持,加上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使《风中牡丹》一度被公认为绝笔。
然而,质疑声很快出现。有研究者指出,齐白石晚年因体力衰退,已极少绘制结构复杂的牡丹题材,且《风中牡丹》的笔力雄健程度与同期作品存在差异。更关键的是,该画题款仅简单标注“九十七岁白石”,未提及具体创作时间,难以作为确凿证据。
2. 学术考证的突破:王鲁湘与《葫芦》的铁证
2005年,美术史家王鲁湘在整理张仃(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奠基人之一)遗物时,发现了一幅从未公开的齐白石画作《葫芦》。张仃之子张郎郎回忆,父亲晚年常凝视此画,称其为“白石的最后一口气”。
通过比对文献与实物,王鲁湘还原了《葫芦》的创作背景:1957年5月某日,张仃携纸拜访齐白石。此时的白石已无法站立,需由人搀扶至画案前。据李可染亲历者笔记记载,白石提笔时手颤明显,画藤蔓时甚至将叶片误作葫芦轮廓,但笔触中仍有一股“倔强的生命力”。题款时更出现耐人寻味的细节——白石反复询问旁人“九字往左拐还是右拐”,最终将“九十七岁”写成“九十岁”,又补添一“七”字,墨迹重叠处清晰可见。
这幅“错误百出”的《葫芦》,却成为推翻《风中牡丹》绝笔说的关键证据:
时间逻辑:齐白石逝世于1957年9月,而《葫芦》完成于同年5月,晚于《风中牡丹》传闻中的创作时间(8月)。
生理状态:题款的记忆混乱与笔迹颤抖,与齐白石临终前数月的健康状况高度吻合。
见证人链:李可染、张仃、邹佩珠(李可染之妻)等多位艺术家的口述记录相互印证。
3. 艺术本体的对决:两幅画作的风格密码
要解开绝笔之谜,还需回归作品本身。通过对比《风中牡丹》与《葫芦》的技法特征,可窥见晚年齐白石艺术演变的终极轨迹。
《风中牡丹》的“强弩之末”
此画虽具视觉冲击力,但细节处暴露力不从心:
花瓣的洋红色彩饱和度极高,却缺乏晚年常见的“破色”层次(即色墨交融的斑驳感);
叶片勾勒的线条略显僵硬,与藤蔓的飘逸形成矛盾;
题款书法中“石”字的最后一竖明显虚浮,与齐白石晚年“铁划银钩”的典型风格不符。
这些特征暗示,《风中牡丹》可能是齐白石在体力尚可时的作品,而非真正的“最后一笔”。
《葫芦》的“返婴之境”
相比之下,《葫芦》的“不完美”恰恰成为其真实性的佐证:
造型的“误笔”:叶片被绘成葫芦形状,藤蔓交错如孩童涂鸦。这种“错误”实则是艺术家放下技法包袱后,对物象本质的直觉捕捉。
笔墨的失控:浓墨挥洒的藤蔓中,枯笔与涨墨自然交融,形成“屋漏痕”般的肌理。这种效果无法通过刻意模仿获得,唯有在手腕无力控制笔锋时方能偶然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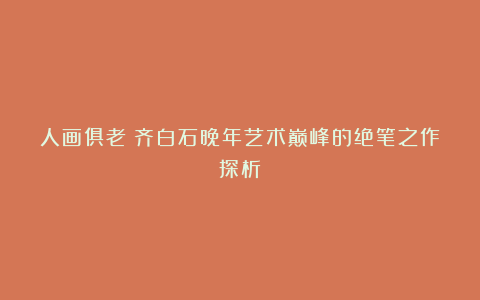
题款的“天真”:将“九十七岁”误写为“九十岁”并修改,墨迹渗透宣纸的痕迹,成为艺术家生命最后时刻的“生理性留痕”。
4. 争议背后的文化心理
绝笔之争的本质,实则是两种艺术价值观的碰撞:
《风中牡丹》派:倾向于将绝笔视为艺术家“巅峰状态的延续”,强调作品的完整性与视觉震撼力;
《葫芦》派:更看重艺术与生命的同构关系,认为“衰年变法”的终点应是超越技法的纯粹精神表达。
正如黄苗子所言:“看《葫芦》如见白石老人最后一口气吐在纸上。”这种将艺术与生命等同的东方美学观,最终让《葫芦》在学术与情感双重维度上获得认可。
5. 谜题的意义:艺术史研究的启示
绝笔之谜的破解过程,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多重证据法:需结合实物分析、文献考据与口述史记录,避免单一视角的局限;
“不完美”的价值:艺术家晚年作品中的“衰颓”痕迹,往往是理解其精神世界的关键入口;
接受争议的常态:艺术史本就是不断被重新书写的动态过程,存疑与探讨本身即具学术价值。
二、晚年艺术特色:返璞归真与笔墨升华
齐白石晚年的艺术风格可概括为“从有法到无法”,其创作逐渐脱离形似追求,转向对神韵与生命力的极致表达。
1. 题材简化与情感凝聚
晚年的齐白石偏爱绘制最熟悉的题材,如葫芦、寿桃、虾蟹等。葫芦因其谐音“福禄”而寓意吉祥,且造型简单,适合衰年体力有限的创作。而寿桃则成为他表达长寿愿景的载体,采用“红花墨叶”技法,以洋红泼染桃实,花青勾勒枝叶,色彩对比强烈,既艳而不俗,又充满世俗的喜庆。
2. 笔墨的“糊涂”与本能
《葫芦》的创作过程堪称“以无法为法”的典范。画中藤蔓线条看似随意,实则蕴含数十年功力,墨色浓淡相宜,笔触如篆书般浑厚。李可染评价其“绝了”,正是因为这种“糊涂”状态下的本能挥洒,让作品超越了技巧层面,直抵艺术本质。
3. 形神兼备的极致平衡
即便在晚年,齐白石仍坚持“写生不求形似”的理念。例如他笔下的虾,腹部从五节简化为三节,长须的摆动却更显灵动,达到“形减神增”的效果。这种对物象的提炼,源于对自然观察的终生积累,亦是对传统文人画“重意轻形”的革新。
三、文化寓意:生命礼赞与世俗情怀
齐白石的晚年作品不仅是艺术探索的结晶,更是其人生哲学的体现。
1. 长寿与吉祥的世俗寄托
寿桃、葫芦等题材承载着传统文化中对福寿的追求。例如《益寿图》《寿桃图》中,桃实饱满艳丽,枝叶繁茂,既是对生命的礼赞,亦是对观者的美好祝愿。
2. 乡土记忆与童真趣味
齐白石晚年常描绘白菜、萝卜、小鸡等日常之物,赋予平凡题材以诗意。如画中两只争夺虫子的公鸡,或藤蔓下嬉戏的葫芦,皆透露出质朴的乡土气息与老顽童般的幽默。
3. “人画俱老”的生命境界
《葫芦》的创作,恰是齐白石“人画俱老”的写照。体力衰退反而催生了艺术上的纯粹,笔墨中的“稚拙”与“天真”,成为其生命最后阶段的至高境界。
四、艺术史价值:从争议到封神
齐白石的绝笔之作曾长期秘藏于张仃家中,仅在小范围艺术圈内流传。李可染、黄苗子等人常聚于张宅赏画,如痴如醉,视其为“精神解药”。这种私密性反而强化了作品的传奇色彩,使其成为艺术史上“未被展示的经典”。
此外,齐白石晚年作品的市场价值亦印证了其艺术地位。2017年,其《山水十二条屏》以9.315亿元创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而晚年小品如《寿桃》《葫芦》等,虽未公开交易,但被学界视为无价之宝。
五、结语:艺术与生命的终极合奏
齐白石的晚年创作,是一场艺术与生命的合奏。他以“糊涂”之态突破技法藩篱,以童真之心拥抱世俗烟火,最终在《葫芦》中抵达“天爵”之境——即超越肉体局限,以笔墨直抒性灵。这种境界,不仅属于齐白石个人,更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人画俱老”的永恒注解。正如邹佩珠所言:“隔日子长了没看这幅画,就像得了病似的。” 这或许正是伟大艺术的魔力:它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灵魂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