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项目阶段性成果,是课题组成员任宏副教授发表于2024年第6期《戏曲艺术》的论文。文章围绕不同版本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编,从创作原则、音乐设计、音乐功能拓展等多维度切入,论述了特殊时代文艺创作的探索实践,对当下戏曲音乐创作发展也颇具启示。
摘要:伴随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所受到的重视程度的渐趋加强,其剧本的改编与创作、音乐的构思与编创、舞美设计与表演实践等多个方面均有着不断的修正与打磨,并先后产生六个版本。不同版本的唱段分布并不相同,在历时的变化中逐渐呈现出对特定时代创作原则的遵从。在这个越来越突出主干、削弱旁支的唱段设计框架中,对人物形象的音乐塑造能力、场景的音乐描绘能力的要求,促进着诸多参与设计与编创者全力探索,并在音乐形象的构建与书写、场景音乐的戏剧性效果等方面取得了较多的经验与实践成果。
关键词:特殊创作原则,人物形象塑造,音乐功能拓展
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下文简称《智》剧),曾在1958年至1970年期间逐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在剧本创作、唱腔设计、音乐设计、舞美设计等方面均经历过无数次的打磨和调整,先后产生过六个版本。
1957年秋,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正式出版,1958年5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演出了根据该小说改变的话剧《智取威虎山》。同年8月,上海京剧院一团的陶雄安排编剧申阳生,将黄正勤、李桐森、曹寿春三人拟定的提纲再度整合,形成《智取威虎山》剧本初稿,并在南京中华剧场首演,后于9月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公演。导演陶雄、李桐森、李仲林,纪玉良饰少剑波、李仲林饰杨子荣、贺永华饰座山雕、王正屏饰李勇奇、贺永华饰座山雕、李桐森饰定河道人,刘斌昆饰一撮毛,曹寿春饰栾平、赵晓岚饰栾平妻。[1](下文简称此版本为58版)
1963年1月,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再次上演,曾取名为《林海雪原》《智擒座山雕》等。[2]因北京要于次年组织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下文简称“观摩大会”),时任院长的周信芳提议修改此剧后参演,遂安排陶雄、刘梦德作剧本修改加工,由辛清华、张鑫海、陈立中和邵水泉担任唱腔和音乐设计,调请上海电影制片厂应云卫担任导演。上海市委很重视这项工作,由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亲自主管剧组工作,后因工作变动,改由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接替剧目主管工作。[3]1964年5月,修改后的《智》剧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6月赴京参加“观摩大会”,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前来观看演出,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同年12月,该剧剧本正式发表。[4](下文简称此版本为64版)
从北京返沪后,剧目仍旧不断的打磨,并于1965年1月出版修改本(下文简称此版本为65版)。[5]
1965年3月,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戏改”小组的规划下,由章力挥任编剧组组长和组织负责人,由章力挥、陶雄、刘梦德、丁国容、高义龙组成编剧组,李仲林、关尔佳任导演,调刘如曾、黄钧,会同陈立中、高一鸣、黎秋觉、王正屏、童祥苓组成音乐组,调胡冠时担任舞美设计。在不断修改过程中,唱腔的调整曾先后增请来沪演出的《沙家浜》唱腔设计李慕良、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沈利群等人协助。演员方面也经调整,改由童祥苓饰杨子荣,沈金波饰少剑波、孙正阳饰栾平,增加齐淑芳饰新增人物常宝。[6]1966年4月,修整后《智》剧在儿童艺术剧院演出,并于1967年5月再度赴京,参加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而举行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汇演,[7]剧本发表在同年第8期的《红旗》杂志上。[8](下文简称此版本为67版)
1968年夏秋之交时,该剧组全班人员晋京参加电影拍摄,直到1970年结束。在此期间,该剧仍处在不断打磨中。1969年国庆节期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修改本再度与其他几部“样板戏”再度于北京会演,剧本再次发表于同年第11期的《红旗》杂志上。[9](下文简称此版本为69版)
此外,经过不断修正打磨,在音乐设计上有所创新的《迎来春色换人间》《胸有朝阳》《誓把反对派一扫光》等采用中西混编乐队伴奏的唱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该总谱也于次年正式出版。[10](下文简称此版本为70版)
十余年的光阴,诸多参与者的竭尽全力造就出的六个版本,记录着那个沉重岁月中的艰苦探索与不断实践。重新翻阅这些资料,认真省察其蕴藏着的编创构思与手法,是对这份智慧结晶的最大尊重。
一、创作原则与唱段布局的历时变迁
十余年当中的不同版本所记录下来的唱段布局结果并不相同,却因剧情改编过程的连续性,而成为了解京剧现代戏《智》剧的人物唱段安排历时变化的重要切入点。
依照剧本改编的阶段性,可将六个版本分为三个阶段,58版是第一个阶段,64版和65版是第二个阶段,67版、69版和70版是第三个阶段。
上图具体说明见注释[11]
对比可见,58版中的少剑波和杨子荣的唱段布局安排错落有序。其中,少剑波的唱段分别安排在序幕、第一、二、三和六场,独立唱段集中在前三场。杨子荣的唱段安排在第三、四、五、七、八和十一场。两个人的唱段布局与剧情安排相呼应,唱段的数量比重相当。
其他人物的唱段安排则各有侧重。李勇奇和李母各有独立唱段,安排在第六场。老猎户与妻子各有干念段,不唱。孙达得、刘勋苍、白茹分别在第三场、第六场各接唱1句。战士群体分别在序幕、第一、九、十和十一场,安排齐唱唱段。
反面人物当中,一撮毛的唱段较多,在第一、三场有独立唱段,第二、三场有干念段。定河道人在第二场有唱段和干念段。座山雕在第五、七和十一场有独立唱段。栾平在第十一场有唱段。
整体上看,正反面人物都有唱段,其中少剑波和杨子荣的唱段最多,其他人物次之。反面人物当中,依唱段数量依次递减排列为:一撮毛、定河道人、座山雕、栾平。可以说,58版的唱段安排与布局,是以剧情需要为核心,相对均衡的布排,并依照人物定位灵活选用唱、干念等形式,其中唱段可进一步区分为独唱、接唱与齐唱,舞台表演唱的形式相对多样。
64版以58版为基础,对剧情有所调整,人物出场、唱段布局也就有了相应的变动。序幕删去唱段,改为吹打上场,在文、武场伴奏的映衬下完成剧情表演。第一场改为只有众战士们急行赶路唱牌子曲,杨子荣等奉命侦察。将58版一撮毛夺图杀人的情节挪至第二场,压缩为过场戏,杨子荣、少剑波等雪地救起栾平妻。第三、四场改为杨子荣等追捕一撮毛、会定河道人、押审栾平和一撮毛,得知威虎山上百鸡宴情况,缴获联络图,众人商定剿匪计划。因此,第二至四场的唱段安排随之变化较大,其中第四场当中,少剑波、杨子荣、孙达得、一撮毛都有数量不等的唱段。58版的第四场是杨子荣打虎上山,64版调整为第五场,此后的剧情调整大致包括删减玫瑰花和定河道人上威虎山的戏、加强杨子荣和少剑波的多角度塑造,例如,少剑波在情报收回、栾平逃跑时的沉着机智应对与安排,以及在匪窝中英勇无畏对敌斗争的杨子荣等,都是着力刻化的重点环节。
与此相关,少剑波的主要唱段分别安排在在第二、四、七和第十场,杨子荣的则安排在第三、四、五、六、八和第十二场,但在数量上,少剑波的唱段要多于杨子荣,体现出布局思路上的侧重。对于反面人物,座山雕、定河道人、一撮毛、栾平等人的唱段被削减的很多,一撮毛只在第四场有2句唱,在第二、三、四场均处理成“干念”段。栾平的唱段缩减为两句。65版基本上是以64版为基础,仅是在部分细节上做出调整。
70版《智取威虎山》 沈金波 饰 少剑波
与58版相比而言,64版和65版在唱段安排上,构成了正面人物数量多,反面人物少的鲜明对比。其中,少剑波被视作主要人物中的核心。
上图具体说明见注释[12]
与65版相比,后三版在剧情、人物的安排上又有了较大调整。67版新增猎户老常父女,将65版的序幕内容整合编入第二场《夹皮沟遭劫》,将一撮毛夺图杀人情节编入第三场《深山问苦》,删减神河庙追捕一撮毛、会定河道人等情节。与此相关,不同人物的唱段安排又有了较大的调整。
在保留原有唱段的基础上,在第一、四场新增少剑波唱段,在第一、三、四、五、六、八和第十场新增杨子荣唱段多个,用新创的《打虎上山》唱段14句替换掉65版原有唱段。在第二场中新增李勇奇和座山雕唱段,新创第七场的李母、李勇奇、张大山、少剑波的唱段。以此为基础,69、70两版有着较大的改动,在唱段安排上,着重删减少剑波、座山雕的部分唱段,在第九场新增常宝唱段。还对全剧的绝大多数唱段的板式有着非常细致的打磨和完善。此外,因伴奏乐队编制的改变,全剧的音乐设计及与唱腔衔接上的处理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修整。
从69版和70版的人物唱段安排与布局上看,正面人物只有杨子荣、少剑波(参谋长)、李勇奇、李母、常宝有唱段,其他人都不再安排唱段。其中,杨子荣的唱段数量达少剑波(参谋长)的两倍,另外几个人的唱段依数量排列为:李勇奇、李母、常宝。反面人物仅有座山雕有唱段,其他人均无。经过后三版的删减,座山雕只有在第六场有两句唱。此外,群众与战士们的唱段被压缩为接唱形式的1-2句。
70版《智取威虎山》施正泉 饰 李勇奇
从1958年排演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算起,到1970年拍成电影为止,长达十余年的不断打磨,在人物唱段的安排上,逐步形成了正面人物中以杨子荣为核心,少剑波次之,李勇奇等其他人物为辅,反面人物尽量不唱的布局结构。很显然,此类编创实践及其成果样态,体现出对“三突出”“三陪衬”“三打破”和“三对头”等创作原则的遵从。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用反面人物的陪衬、其他正面人物的烘托和环境的渲染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守的一条原则。”[13]在此原则的规约下,人物的唱段分布、规模,以及板式安排等细节,均要为塑造主要英雄人物而服务。
二、多重桎梏下的唱腔设计“突围”
在遵从此创作原则的基础上,探索出既能符合人物塑造需要,又能符合“推陈出新”要求的编创手法来,这是摆在当时所有参与编创排演该剧的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并且无法推却与退后。事实上,对于舞台表演来说,在既往形成的唱、念、做、打浑然一体的程式表现体系当中,音乐(包含唱腔与伴奏)的实践又是关乎上述方面的关键枢纽,甚至可以说,舞台上的“动”态的推衍与作为整体的音乐的衍展密不可分。因此,《智》剧,甚至处在当时这种境况下的其他几部“样板戏”,都面临着音乐上的“突围”难题。
十余年的打磨,汇聚诸多参与者的智慧结晶的《智》剧,在用音乐编创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构筑情境与助推剧情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可圈可点的收获。本文不可能详尽叙谈全部,仅择其最为突出之处分述如下。
1.成套唱腔设计与人物形象的“统合”塑造
在长期的打磨过程中,以皮黄为主要声腔的唱腔设计得以延续,在唱腔的形态方面则依照剧情发展与人物形象塑造的要求展开探索。
在后三版中,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杨子荣的唱段的规模与数量逐步成为重点打磨的对象。69版和70版中,杨子荣的唱段分别安排在第一、三、四、五、六、八和第十场中,共有12个唱段,其中第三场的《管叫山河换新装》(即67版《激起我仇恨满腔》)、第四场的《共产党员》(即67版《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在第五场中的《迎来春色换人间》(即67版《火海刀山扑上前》)、和在第八场的《胸有朝阳》(即67版《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都是精心安排的重点唱段。
这四个重点唱段的唱腔与板式安排的规模、所处剧情位置以及对于人物刻化的角度各有不同。第三场《深山问苦》的剧情涉及深入山坳追查一撮毛踪迹、再遇猎户老常父女并问苦、诉苦,第四场《定计》是审问栾平和一撮毛后制定剿匪计划,第五场《打虎上山》和第八场《计送情报》则是身在匪窝执行剿匪计划。可以看到,这既是本剧的重要发展线索,四个唱段所处位置均为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人物在面对同胞苦难生活、土匪凶残暴行的对比后,内心革命斗志愈来愈坚定,进而可以机智勇敢的打入敌营完成剿匪计划的过程,四个唱段恰处不同心理层次,展现不同阶段的内心变化。其中,《迎来春色换人间》和《胸有朝阳》均为二黄成套板式组成的大段唱腔,依照不同情境,板式转换与节奏的细节处理均有差别,但整体上的由【导板】-【回龙】组成的开放性结构中,舒展的革命情怀、铿锵而坚定的革命意志等情绪情感变化,尽在【原板】【散板】或【垛板】或【快板】的切换中游刃有余的得以表现,最终在激昂的唱腔中收拢的处理思路,是相同的。当然,无论是剧情发展的高潮设置,还是人物身处复杂环境的双重身份刻化,《胸有朝阳》唱段均是四个重点唱段中的核心唱段,所以在67、69和70版中,该唱段的板式细节曾经历过相当的打磨和修整。
虽然,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所遵从的特殊创作原则,导致曲腔种类的选择并不自由,但依照剧情铺叙来安排人物唱段的位置与规模,在全局的广度上统合性的构建多侧面、多角度刻化人物形象的“连缀式”唱腔设计构思及分层处理手法的不断实践,均成为重要的经验,伴随“样板戏”的推广而形成较大影响。
2.唱腔板式的反复锤炼与精细打磨
在唱段的不断修整过程中,逐步呈现出对唱词语义内涵的形象建构、利用特殊曲调贯串来“深描”人物细节,以及加强唱腔设计与舞台表演的融合等方面的的主动追求。
67版新增常宝父女,但只有常宝有唱段,其中在第三场唱的“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在板式上采用【反二黄导板】转【反二黄原板娃娃调】转【快二六】转【快板】,末句转【摇板】【散板】结束,这里的【反二黄】唱腔的苍凉与悲壮,再吸收【西皮娃娃调】【高拨子】【二黄】的行腔及旋法,创造出的【反二黄娃娃调】,就是因常宝而创造性的设计而来。以一泻千里、激昂又不失悲怆的唱腔,在多层次的板式转换当中,塑造出由长期思念而带来的深度忧伤、强烈愤怒引发的刚毅、倔强、果敢集一身的16岁女子的形象。[14]该唱段在69版和70版中曾经历过板式上的反复打磨,形成了【反二黄导板】转【快三眼】转【原板】转【垛板】的结构。也在“女扮男装”唱腔后的过门、“父女打猎在峻岭上”唱腔上经历过音区、旋律上的调整,突出对“峻岭”的险、陡的“立体形象”的勾勒。[15]
70版《智取威虎山》常宝选段“八年前风雪夜”
后三版的唱腔细节打磨中,在杨子荣的《管叫山河换新装》【西皮原板】的第三句“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帐”,和《胸有朝阳》的【慢板】第三句后半段与第四句唱腔“一颗颗火红的心暖我胸膛”的旋律处理上,均采用了属方向离调的旋法,体现出在特定位置贯串再现人物的“专属曲调”,进而构成对人物形象的深度“描绘”的构思与实践。[16]
67版新增杨子荣《打虎上山》场的“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段,是由极其舒展又豪迈的【二黄导板】转相对紧凑的【回龙】,转稳健而有气魄的【慢原板】,转高亢而振奋的【西皮快板】结束。[17]69版和70版在部分唱词、板式上反复调整,尤其在【导板】和【回龙】之间增加马舞身段表演,并因此重新创作了与之相关的配乐和其他音乐,使得该唱段呈现出与之前大大不同的效果。[18]
67版在《打进匪窝》场新增杨子荣的“提起栾平气难按”唱段,将65版的对白叙述方式改为唱念结合的形式,促进了杨子荣的机智和勇敢形象的打造。这段唱同样经历过板式的精细打磨,最终在70版呈现出【西皮小导板】-【原板】-【流水】-【摇板】-【流水】-【摇板】-【流水】-【快板】的板式结构。[19]被反复斟酌的是最后的六句,最终定版的是将这六句精细的处理成【流水】-【摇板】-【流水】-【快板】,其中“栾平他醉成泥一滩”改唱【摇板】,与舞台表演的模仿栾平醉态相呼应。[20]
本剧中还有很多唱段都是经历过反复琢磨的,此处就不再赘述了。需要追加提及的是,这些反复斟酌和细节上的不断修整,尽管带着较大的政治压力,却是汇集了编创与表演者们的集体智慧与辛勤汗水,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的探索与实践着音乐的戏剧性的表现手法,并取得了较多的收获。
三、多种设计手法与音乐功能拓展
20世纪中叶以来,当传统戏曲被作为整改对象,其原有的曲腔形态、结构方式及相关的表演模式等面临着新的挑战时,向其他不断发展起来的有着“新音乐”文化特质的音乐形式、形态及其编创手法学习,是许多编创者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智》剧也不例外,并在以下方面取得若干收获。
1.创造性的建设混合编制乐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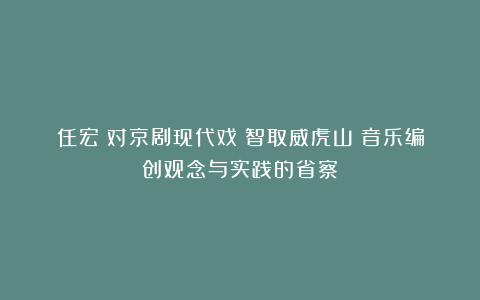
在音乐设计方面,由于采用了中西混编乐队,使得多声部配器、和声等作曲技法有了较大的表现空间,为探索音乐戏剧性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在民族乐队的基础上加设西洋乐器的做法,在五十年代前后就逐步被许多剧团采用。但是,以成编制的中西混合乐队用于京剧伴奏,是在1969年才开始,并且以《智》剧为首创。
经过不断的调试,综合音量、音色,甚至舞台台侧的空间等因素,最终将编制定为由四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和琵琶)、弦乐组(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板胡)、木管组(长笛、单簧管、双簧管、短笛、曲笛、海笛、唢呐、竹管)、铜管组(小号、圆号、长号),以及打击乐组(定音鼓、板、鼓、大锣、铙钹等)、键盘排笙、铝板钟琴组成的中西混编乐队。[21]
此编制的设定,是本着兼合传统文、武场与西方管弦乐队为一体的构思而展开的,为了更好的消弭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导致的音色、音准方面的差异,在板胡与第一小提琴,长笛与短笛、曲笛,双簧管与海笛、唢呐,单簧管与竹管之间打通演奏技法的“壁垒”,即安排同一个演奏者兼顾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乐器演奏,这样的“兼顾”并非易事,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实则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演奏效果。
70版《智取威虎山》杨子荣选段“迎来春色换人间”
2.歌曲“嫁接”与精神主旨“点睛”
被作为“样板”的《智》剧,并非简单的讲述人民解放军与匪寇斗智斗勇的故事,而是承载着更多的精神内涵,在向全国宣传开来的过程中完成它被赋予的政治使命。因此,对于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与革命英雄的形塑的手法,就需要谨慎选择与采用。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逐步找到了一种良策,即借用已经传唱开来、具有较大影响力,甚至具有专曲专用特征的歌曲旋律,作为特定形象的“代言”,经过处理嵌入在唱腔或伴奏当中,起到革命精神主旨的“点睛”作用。
《智》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设计了两种音乐形象。第一种是借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公木词、郑律成曲[22],下文简称《解放军进行曲》)的主题旋律展开编创,意在展现战士们的顽强、拼搏、不畏艰险的革命斗志。此音乐形象是有所侧重的分别铺叙开来的。首先在《序曲》中巧妙的借用原作品中“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及“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歌词对应的曲调,以原样借用、变奏处理等手法,置入《序曲》的旋律曲调当中,具有提纲携领、点明主题的作用。这些曲调素材,在第一、三、九和十场中采用多种处理手法再现,着力展现人民解放军形象的不同面向。
第二种是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程坦编词、集体改词[23],下文简称《三大纪律歌》)的主题旋律展开的创编。这首歌曲的旋律曲调朗朗上口,具有反复咏唱的特点,节奏鲜明,律动感强。在第四、七和九场中嵌入使用,主要展现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的整体形象。
除此之外,该剧还借用歌曲《东方红》(陕北民歌、李有源词[24])的骨干旋律,作为党的光辉指引的音乐象征,在第三场《深山问苦》杨子荣的《管叫山河换新装》的【西皮流水】段落,“深山见太阳”后拖腔的伴奏中,以及第八场《计送情报》杨子荣的《胸有朝阳》唱段中出现,分别与唱词中的“太阳”“朝阳”暗应。
必须承认,这种借用特定歌曲的曲调旋律,迅速引起观众、听众的情感共鸣的处理手法,是极具智慧的。只是当这种做法被作为范式广泛采用之后,其能引发的共鸣的强度随着重复的次数而渐趋下降时,便不再具有太多新意了。
3.主题曲调转换与人物双重身份“书写”
杨子荣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为了完成剿匪任务,孤身上威虎山作卧底,与少剑波等里应外合顺利完成这项原本困难重重的斗争任务。在剧中他具有双重身份,以剧情叙述的视角而言,在第一、三、四场和第十场,杨子荣是以正面身份亮相;而在第五、六、八和九场当中,则是以“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胡标”的身份来面对土匪,以杨排长的身份来面对党的工作。在音乐形象的构建中,此双重身份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其正面形象,首先在《序曲》中被定性,即《序曲》的首句,也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首句“向前、向前、向前!”的乐句。这是一条节奏铿锵有力的同音重复形态的乐句,具有较强的驱动力,和较大的可延展性。其伴随杨排长的行动,分别出现在第一、三、四和六场,和第十场剿匪成功欢庆胜利时。
其卧底形象的音乐书写,定位于第五场《打虎上山》的《幕间曲》的锣鼓点之后,是在阵阵的马蹄声中出现的激昂而流畅的新创的曲调,具有鲜活、开拓、披荆斩棘的特点,在此处与策马上山的“胡标”同登场后,又分别于匪窝中和座山雕讲述联络图、巧妙化解座山雕试探等处,与正面形象形成对比,还成为人物双重身份切换的音乐提示。
4.熔炼音效参与场景“叙事”
出于上述新的乐队编制,以及极富创造性的训练手法,使得这支乐队的演奏能力大幅度提升,为实现音乐设计中的特殊音效提供坚实的基础。
《智》剧中不同场次的《幕间曲》、唱段的间奏与过场音乐的设计,都比较重视音色、音效的描绘作用。例如,在第五场《打虎上山》的《幕间曲》,由锣鼓点模仿马蹄声,弦乐组、琵琶、键盘笙和木管组按照配器合作演奏的快速、不断迂回前进的旋律,与铜管组吹奏的舒展、律动感强的辽阔旋律,将策马扬鞭奋力奔驰在皑皑雪原的英雄形象,表现得生动而鲜活。这段极富想象力的曲调及其乐思,与【二黄导板】“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连成一体,并在马舞的配乐中再度延展开来,连接【回龙】与【原板】唱腔。在【原板】唱段中的“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唱腔前后,由木管组、弦乐组演奏的明媚、温暖的曲调,尤其是此处用到了铝板钟琴的特色音效,其斑斓而灵透的音响,生动的展现出“春水、春色、换人间”的美好景象。
从音乐效果的整体性上讲,本场的《幕间曲》的音乐构思在随后的多板式转换的间奏以及《闭幕曲》中得以不断的铺陈,进而将本场的唱、奏、舞全面统合起来。在这个整合性较强的舞台表演空间当中,音乐描绘出来的场景,在视觉、听觉的联觉通感中,创造性的实现了空间的移位与建构,突出的展现出音乐的场景描述功能。
诸如此类的处理还有很多。例如,利用竹管的呜咽音色来表现座山雕的阴险狡诈,以中提琴的低沉、琵琶的特殊演奏技法形成的凄婉音色来表现李勇奇母亲心中的悲凉与无助,以海笛、板胡和琵琶等乐器演奏出来的具有浓郁东北民间风格的乐曲来展现群众喜迎新年的热腾景象等。如此音乐设计均成为不同场次中的独特的叙事手段。可以说,囊括了唱腔设计与场景音乐设计的音乐编创,已经成为剧情叙述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总体看来,十余年的反复探索与实践,促使这场音乐的“突围”工作获得了很多收获。在带有较强的政治“宣传工具”作用的“样板戏”剧目文本写作的框架中,用唱腔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以及音乐的戏剧性表现手法及其功能的不断拓展,成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取得创作成就最高的部分。这是那段沉重岁月对音乐的特殊关注所致,更是所有参与编创排演的人们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注释】
[1] 上海京剧院一团:《智取威虎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12月版。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2] 《上海京剧志》编辑部:《上海京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3] 戴嘉枋:《<智取威虎山>台前幕后多磨难》,《乡音》2012年第12期。
[4] 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本》1964年第12期。
[5] 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年1月版。
[6] 戴嘉枋:《<智取威虎山>台前幕后多磨难》,《乡音》2012年第12期。袁成亮:《<智取威虎山>诞生记》,《党史博采》,2005年第10期。上海京剧院集体改编:《智取威虎山》,《红旗》1967年第8期。李晓天:《情系国粹意隽永 乐载皮簧唱英雄》,《京剧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875-882页。
[7] 《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
[8] 上海京剧院集体改编:《智取威虎山》,《红旗》1967年第8期。
[9]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智取威虎山》,《红旗》1969年第11期。
[10]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智取威虎山》,人民出版社1971年7月版。戴嘉枋:《论京剧“样板戏”的音乐改革》(下),《黄钟》2002年第4期。
[11] 说明:为简洁醒目,表格中采用简称,其中“众”代表众战士与群众,“少”代表少剑波,“毛”代表一撮毛,“道”代表定河道人,“杨”代表杨子荣,“雕”代表座山雕。“孙”代表孙达得,“白”代表白茹,“栾”代表栾平,“张”代表张大山。下表同。本表所依据材料为:上海京剧院一团:《智取威虎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12月版。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本》1964年第12期。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年1月版。(为避免繁冗,下文与此相同处不再出注。)
[12] 说明:该表中的人物称谓用简称代表,与上表同。新增“宝”代表常宝,“参”代表参谋长(少剑波)。本表所依据的材料有: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红旗》1967年第8期。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智取威虎山》,《红旗》1969年第11期。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智取威虎山》,人民出版社1971年7月版。为避免繁冗,下文与此相关的内容,除特殊需要之外,不再出注。
[13]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红旗》1969年第11期。
[14] 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红旗》1967年第8期。《智取威虎山》选曲,上海文化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4-9页。
[15]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智取威虎山》(总谱),人民出版社1970年8月版,第39-45页。
[16]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智取威虎山》(总谱),人民出版社1970年8月版,第62、287-289页。
[17] 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红旗》1967年第8期。《智取威虎山》选曲,上海文化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34-40页。
[18]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智取威虎山》(总谱),人民出版社1970年8月版,第130-170页。
[19]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智取威虎山》(总谱),人民出版社1970年8月版,第182-205页。
[20]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北京电影制片厂1970年版。
[21]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智取威虎山》(总谱),人民出版社1970年8月版,扉页2。
[22] 此作品原名《八路军进行曲》,公木词,郑律成曲。曾于1951年2月1日、1953年5月1日,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文件的附录二中,先后以《人民解放军军歌》《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之名刊登。1957年11月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文件附录二,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之名刊登。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公木 郑律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音乐》1977年第4期。《中央军委决定我军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日报》1988年7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人民音乐》1988年第8期。)
[23] 此作品的歌词,是1935年11月,程坦同志依照《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全部内容编写而成。在时任军团宣传科长刘华清同志的协助下,将歌词填入原在鄂豫皖根据地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中,经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同志批准,油印刊登在军团的《红旗报》上。此后,该作品广为流传,其作品名、歌词内容曾经过修改。1950年、195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1947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组织专人对这首歌的歌词进行过修改,并于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1957年《解放军战士》杂志第14期上,两次正式公布。(《解放军歌曲》编辑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解放军歌曲》,1981年第3期。程沐雨《父亲留下一支歌》,《我们的父母——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2007年版,第138-146页。)
[24] 陕北民歌 李有源词《东方红》,《<解放军歌曲>百期选》,音乐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
请上下滑动阅览
作者介绍
任宏,女,汉族,党员,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副教授。先后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国传媒大学出站博士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中国音乐史学会会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委会会员,编钟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教育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虚拟教研室成员,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邀访学者。
长期致力于中国音乐史、音乐考古学与戏曲音乐史论方面的研究。已有出版著作3部,在音乐类、考古类与戏曲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论文先后被多种文集收录。主持课题有:文化旅游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项目《中国戏曲音乐元数据库建设》,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两周乐悬制度演生及社会功能研究》,北京社科基金《清代宫廷昆腔承应戏曲牌音乐研究》,北京市委教工委、北京市教委双百计划项目《北京戏曲音乐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调研》等。参与课题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曲音乐传承发展研究》、《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戏曲史(北京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刘家洼芮国都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等。
制作:黄若熙
责编:孔培培 陈晓娟
编审: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