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午后,阳光透过客厅的窗户,在摊开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封面上投下温暖的光斑。我悠闲地翻阅着,不是为了解决某个迫在眉睫的困惑,而是纯粹享受着与这些思想对话的乐趣。忽然间,一个念头击中了我:曾几何时,我手中紧握的心理学,是一把在寒风中也要紧紧握住的手术刀,而今却成了可以悠然欣赏的艺术品。这种转变,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2年开始,我的人生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从学生到辅导员,从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每个新身份都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让我在角色转换中步履蹒跚。在那些深夜里,我常常独自流泪,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能从容应对的生活,对我来说却如此艰难。后来才知道,那是产后抑郁如跗骨之蛆一般在追赶我。
2020年冬天,一名学生的突然离去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感觉,像是我精心构建的大厦,被瞬间抽走了承重墙,轰然倒塌的瓦砾将我掩埋。自责、无力、对生命无常的巨大恐惧,成了我呼吸间的尘埃。在那片废墟里,我几乎窒息。就是在那时,我几乎是本能地抓住了心理学这根救命稻草。贾杰老师的《心理咨询100讲》成了我的急救手册,每一个失眠的夜晚,我都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贪婪地吸收着每一个知识点。
我系统性地学习心理咨询中的11个理论流派的知识,并且像一名执刀的外科医生,先对自己进行一场艰难的手术。最难忘的是用贝克疗法给自己”做手术”的那个夜晚。当”我为什么会愤怒”的念头再次袭来时,我第一次拿起笔,像医生执刀般冷静地开始解剖:”我的自动化思维是什么?核心图式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知偏差?”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泪水却止不住地流淌。那一刻,心理学就像急诊室里的无影灯,照亮了我内心最隐秘的伤口。
三年来,除了自己学习外,我还带领团队组建了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完成了课程建设,编写了教材,站上了讲台。可当这些目标一一实现后,我却陷入了新的迷茫:那个被问题追着跑的自己消失了,学习的热情也随之消退。我开始怀念那个”无知”却充满激情的自己,那个把所有碎片时间都用来学习的自己。
完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的那天下午,我独自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望着窗外熟悉的校园,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就像久病初愈的人,突然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康复后的身体。心理学这把陪伴我多年的”手术刀”,忽然不知道该指向何方。
就在这个迷茫的时期,我遇见了维克多·弗兰克尔。读着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经历,我被他那句话深深震撼:“一个人可以被剥夺一切,除了最后的自由——选择自己对境遇的态度。”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我合上书,内心却燃起一团火焰。原来,心理学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是指引人生方向的明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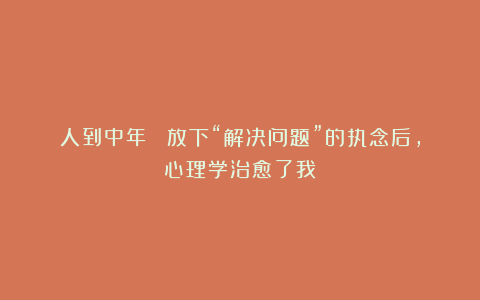
从那时起,我开始好奇:”如果不为治病,心理学还能带我看到怎样的风景?”这个问题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发芽。心理学于我,正从支撑我行走的”拐杖”,慢慢变成助我攀登的”登山杖”。
转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最明显的标志是,我看待母亲的目光完全不同了。
从小令我最痛苦的是为什么我没有一个温柔可亲的妈妈,对母亲的质疑带给了我对自我的怀疑。三十五岁那年,我的孩子7岁。某个疲惫的傍晚,看着镜中与母亲越来越像的眉眼,我突然理解了她。那个在我记忆里永远强悍、从不温柔的母亲,假如我是她,能在那个贫瘠的年代,独自挑起养育五个子女的重担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从小如野草般长大的女孩,又怎能奢望她成为温柔得体的母亲?这个顿悟的时刻,心理学不再是手术刀,而是一副度数刚好的眼镜,让我看清了生活的真相。
这份理解也延伸到了工作中。曾经,我对那些”问题学生”总怀着”怒其不争”的愤慨。直到我遇见小陈——一个整天沉迷游戏、屡教不改的男生。通过多次谈心,我才知道他的童年是在父母的争吵和冷暴力中度过的。我对他说:”让我们一起去找到当年那个受伤的小孩,告诉他别怕,现在有一个长大的你来找他,我们一起带他回家。”那一刻,我看见他眼里的光。心理学让我明白,每个”问题”背后,都藏着一个渴望被看见的灵魂。
就连追剧也成了新的学习场域。《苍兰诀》里,当大魔头东方青苍紧紧抱着儿时与父亲一起玩过的木鞠泣不成声时,我立刻意识到:他的内心还住着那个曾经被父亲伤害过的小孩。这种用心理学眼光解读人物的能力,让平凡的娱乐活动也变得意味深长。
最大的礼物是与自己和解。我接纳了自己是个平庸的普通人,会消极、会逃避、会三分钟热度。那些立了又倒的flag,不再是我的罪状,而是我探索世界的足迹。心理学帮助我成为了自己的守护者、养育者、朋友与爱人。
回首这段旅程,从紧握手术刀到欣赏艺术品,意味着我的生命重心从”生存”转向了”生活”。我不再忙于修补生命的裂缝,而是学会欣赏裂缝中透进的光,甚至爱上裂缝本身构成的独特纹理。
这把曾经的”手术刀”已内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观看世界的底色。如今,我与心理学的关系,不再是医生与手术刀,而是旅人与风景。前路漫漫,但我已握有一张通往心灵深处的 map,这场审美之旅,才刚刚开始。
END
文字:白云贵
编审:范蕊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