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禳盜刻石》,又稱《魚山刻石》,國家一級文物,是刊刻於西漢時期的一方墓門碑,無撰書者姓名,屬由篆書向隸書過渡的書法作品。
考古、書法界素有「西漢刻石三字成寶」之說,金鄉縣胡集鎮魚山集出土的《禳盜刻石》共有138字,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西漢刻石」、漢碑「寶中之寶」。
刻石現存兩殘段,分別藏於濟寧市博物館(第一殘段)、金鄉縣博物館(第二殘段)。
關於《禳盜刻石》的確切年代,因殘存部分無紀年,加上墓室已毀,無法確定,僅能根據刻石形製、書體風貌推斷大體年代。
其形製與 ☌《萊子侯刻石》 等相同,書體總體上具有古隸的特點,筆畫無明顯的提按變化,其中不少字帶有濃厚的篆意。有些偏旁的寫法,似乎還沒有定型,例如「言」字旁,有的寫四橫畫,有的寫五橫畫,「口」部作三角形,「幺」作雙疊三角形,從鑿刻技法看,單刀直取,極少修飾。如以形製相近的《萊子侯刻石》(新朝天鳳三年,公元16年)比較,則《萊子侯刻石》的波挑明顯,字型也較整齊,而《禳盜刻石》則更富質樸之感,無疑《禳盜刻石》早於《萊子侯刻石》。此外,「禳盜刻石」部分字寫法有幾分簡牘書風之意,如「思」字寫法與 ☌《睡虎地秦墓竹簡》 字法一致,結構相識,書風古樸,顯然可以推出年代應早於《萊子侯刻石》。
未脫秦簡意,又早於《萊子侯刻石》,因此,《禳盜刻石》應為西漢早中期作品。
圖丨郭紹瑞《禳盜刻石》抄錄稿。
山東濟寧金鄉縣胡集鎮西郭村村北的魚山南邊開山釆石時發現一座漢墓,村民郭紹瑞發現墓門上方門楣石上有字,石頭上面的字跡略有模糊,極難辨認,黃昏後郭紹瑞拿了一個手電筒、一個寫字的本子、一支筆,依樣寫樣用時兩個余小時,才把門楣石上面的字抄錄下來。翌日,墓室被洗劫一空,刻有文字的門楣石也被拆下來了。郭紹瑞決定找開山的工頭買下這塊石頭,商議後價格是十元,郭立刻交完錢,轉身便回家拉車。然而,等到郭紹瑞拉車從家返回之後,石頭已從六米高的石崖上被推到地面上,石頭被摔成了四段。斷後的石頭在農村也沒大的用途,便放棄了購買。
圖丨《禳盜刻石》,第一殘段。
1980年 濟寧地區開展文物普查工作。宮衍興、顧承銀在魚山坡石料堆中清理出一塊長41厘米、寬35厘米、厚23.5厘米的帶有文字的殘石(第一殘段),這塊殘石便是四塊斷石之一。隨後濟寧市文物管理部門依據該段刻石前五行文字內容,命名此石為「禳盜刻石」。
圖丨《禳盜刻石》,第二殘段。
1990年3月 山東省金鄉縣文化館副館長李登科、文物幹部卓先勝去魚山一帶征集因開山打石而出土的文物,發現一塊帶字刻石,其字體風格、刻工技法都絕類《禳盜刻石》的第一殘段。一個星期後,宮衍興等人再去調查,在魚山北坡郭山口村村民郭紹瑞手中發現1980年《禳盜刻石》出土時由他抄錄的石刻全文。經核對殘石,發現這塊帶字刻石為《禳盜刻石》的中間一部分(第二殘段),後入藏金鄉縣博物館。
《禳盜刻石》石質為青色石灰巖,高35厘米,長195厘米,厚23.5厘米,刻石文字27行,計138個字。其中,第一殘段高35厘米,寬41厘米,存完整字24個,殘字3個;第二殘段高35厘米,寬50厘米,存完整字32個,殘字10個。
刻石全文主要內容為祈禱神靈護佑墓穴、詛咒盜墓者、期寄亡靈平安免禍。
圖丨《禳盜刻石》拓片。
釋文 諸敢發我丘者,令絕毋戶後。疾設不詳者,使絕毋戶後。毋諫賣人,毋效貍人,使絕毋戶後。毋攻毋記,身已下冢,罪赦毋。毋為諭,毋背母考,必罪,天下利子孫。教人政道,天利之。身禮毛膚,父母所生,慎毋毀傷,天利之。分率必讓厚,何絕永強。卿晦,災;卿陽,得見車博道旁。蛇鼠蟲弟當道。秉興頭天,居高視下,莫不謹者。
圖丨《禳盜刻石》拓片,王友誼跋。
結體:
篆隸交融,方正欹側。
篆隸過渡特征。字形介於篆書與隸書之間,部分字仍保留篆書的圓轉結構(如「無」「後」),但整體趨於方扁,呈現「古隸」風貌。
因字賦形。字形大小不一,或縱長(如「疾」),或橫扁(如「毋」),結構靈活多變,尚未形成標準隸書的規整感。
偏旁未定型。相同偏旁寫法不一,如「言」旁或四橫或五橫,「口」部作三角形,體現早期隸書的不穩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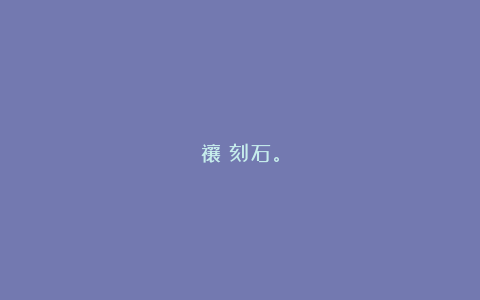
用筆:
方折直率,篆意猶存。
方折為主。筆畫多單刀直刻,起收筆方峻,如「絕」「戶」等字,線條硬挺,少修飾。
無波磔。捺筆無典型隸書「雁尾」,如「之」「後」等字,筆勢平直,保留篆書筆意。
粗細均勻。線條粗細變化小,近似秦篆的勻稱感,但轉折處已顯隸書的方折特征。
章法:
界格嚴整,疏密自然。
豎界格布局。刻石有豎線界欄(欄距7cm),行距清晰,但字距疏密不一,整體疏朗。
自由錯落。雖在界格內,但字形大小、長短不一,如「毋戶後」三字緊湊,「諸敢發」則疏朗,形成節奏感。
民間實用風格。不同於廟堂碑刻的嚴謹,章法隨性,體現西漢民間刻石的質樸。
書風:
古樸率真,山林氣象。
自然蕭散。因刻工技藝粗率,線條不加修飾,反而形成稚拙天真的趣味,與《萊子侯刻石》的端莊形成對比。
金石氣韻。單刀直刻的刀法使線條如「錐畫沙」,纖勁有力,兼具秦篆的凝重與漢隸的飛動。
地域特色。風格豪放率直,與當地民間的地域性格相契合,充滿原始生命力。
■■■■
西漢「禳盜刻石」探究
(節選 研究意義)
書法和文字演變方面:
禳盜刻石的發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隸變在該時期的具體呈現,為研究文字演變提供了實物資料。漢承秦製,到了漢代篆書仍然是西漢的官方用字體。而另一方面,隸書卻無時無刻對官方字體篆書發起沖擊,受到沖擊的同時也受到了其筆法的浸潤。「禳盜刻石」的字形尚未定型,篆意未完全蛻去;整體布局或渾然一體,或行列分明。「禳盜刻石」的章法布局字間開朗、行間緊密,開漢隸布局範式之先河,尤足珍視。「禳盜刻石」典型的隸書布局方式,不僅有邊框界欄,使布局更加完整、更富於裝飾性,而且字間疏朗,行間緊密。這成為後來東漢碑刻及隸書藝術創作中最經典的章法形式。「禳盜刻石」一類的書風對文字和書法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產生了潛移默化而又深遠的影響,這正是西漢刻石在隸變中的特殊價值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之所在。西漢現存刻石的數量較少,這些刻石大多是題名、題字一類的小型刻石,形製小且字數甚少,其中多是篆書,有如此規模隸書者,已發現的僅此一通。「禳盜刻石」吸引了金石、文字、書法等專家的高度重視。篆刻家劉一聞先生對該石的書法價值給予高度評價:「此金鄉魚山刻石,為西漢物也。西漢隸書本無傳世佳者,予之所見多字跡模糊,體貌難辨,此石雖未得之全,然已是稱稀罕之品類。」「禳盜刻石」作為西漢隸書中的極品,文字之多改變了西漢刻石字數少的現狀,其書法古拙變化可謂登峰造極,會對後世書壇產生重大影響。
歷史文化研究方面:
為研究漢代社會狀況提供了最為原始的素材。從刻石首段殘留文字看,前段內容確為護墓的詛咒文,稱為「禳盜刻石」亦無不可。刻石另一段內容是倡孝勸善之語,第一句「居欲孝,思貞廉」為西漢舉孝廉推行教化的標準,《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顏師古註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率眾為善」為推舉地方三老的標準,《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禳盜刻石後段第二句「身體毛膚,父母所生,慎毋毀傷」的內容與《孝經》第一章「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相累似的程度極高。二者皆是提倡孝道勸善的語句,句子尾部皆以「天利之」表示褒揚。從刻石的內容看,刻石其二與「禳盜」詛咒無關,而是有關為孝勸善的內容。我們認「居欲孝,思貞廉,率眾為善」為《孝經》句,為漢代孝經文化的研究豐富了內容。
作者:李英渠 孫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