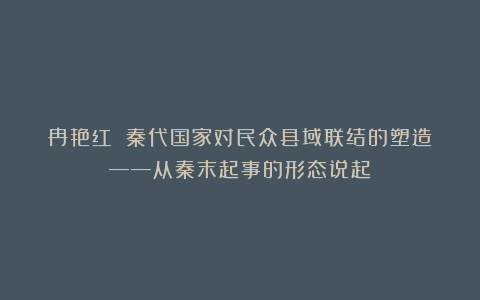冉艳红,历史学博士,重庆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摘要:在秦代,民众被地著并系于县乡里体系下,其在乡里的密切联系可自然产生,而更大范围的县域联结则需徭役和官僚组织提供的场域。县内的徭役和官僚组织运作,使得民众进入县域联结网络。出县的服役、从军者在外界对照下意识到县的群体特质,并以县为单位服役而长期相处,形成相互联结,回县后主导、联结自身乡里社会。反复的徭役征发和官僚组织运作中的国家弥散性权力,修剪出与行政区划体系重合的民众联结网络。秦末以县为单位的起事形态,正是这一联结关系的展演。秦汉中国的村社“小结合体”形态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塑造的,同时民众也存在更大范围的移动与联结,这既是其自身生计、生活的要求,也是国家提供的契机。
关键词:秦末起事;民众县域联结;国家统治;徭役;官僚组织
秦末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崩解后,民众间相互联结形成秩序。陈苏镇在讨论秦末起事时,将楚与其他地区区分,接续田余庆亡秦必楚的讨论【1】,认为楚地对秦的统治格外反感而多自发反秦【2】。这种“自发性”不论多强,其起事形态都折射出一种外部秩序瓦解后民众相互联结、组织的“自生秩序”。欲理解此秩序,就需关注楚地这些反秦起事的形态。陈涉起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3】,既然是杀郡县长吏以响应陈涉,那么显然是以郡县为单位起兵的,而且应该主要是县。其后“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4】,即杀郡县长吏后各地楚兵蜂起的状态。聚兵数千人,大概是一个县的规模,这可以从沛县和东阳县的例子来证明。刘邦初起于沛,“收沛子弟二三千人”【5】,东阳少年杀县令“相聚数千人”【6】。也就是说,这一民众相互联结的“自生秩序”是以县为单位的。作为秦朝国家的一级行政组织,县为何会转换为民众相互联结的单位,其过程和逻辑为何?要理解县这一层级的民众联结,需要先从其下层的乡里出发。
陈苏镇著《〈春秋〉与“汉道”》,中华书局2011年版
《史记·陈涉世家》
民众生活、交往的空间范围及其限制
秦代民众的主要生活范围是里,当时里的规模大约在二三十户左右【7】。在这一规模下,里内民众间基本能相互熟悉。在制度设计中,里应该是有垣墙的封闭聚落,当时也确实存在不少封闭的里,同时又产生宗、僤、社等组织【8】,如岳麓秦简《识劫案》中,的婚姻需由里内社会承认,并履行一定义务【9】,民众间关系密切可以想见。晁错所描述的徙民实边后的民众生活状况,可以看作当时理想的里内社会生活:
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10】。
其中特别强调民众之间“生死相恤,坟墓相从”,是想在迁徙地营造邻里间的紧密人际结合,甚至是世代联结。刘邦与卢绾“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里中两次“持羊酒贺两家”。两家亲爱,卢绾也成为刘邦最信任之人,“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11】,皆源出于这一里内关系。而两家亲爱,里内来贺,也展现了整个里亲密的交往关系。
不过同时也应注意到,之所以特别写下两家的亲近,显然因其并不常见。西汉中期王吉家“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后来王吉去妇,东家欲伐树,邻里共“止之”并请王吉“还妇”【12】。王吉本传对此的记载是为了彰显其“厉志”,也可看出邻里之间的和谐。但之所以“厉志”,自然是被视作特例的。借助今日生活的经验,可以想见,类似王吉妇摘邻家枣之类的邻里小矛盾并不罕见,更多情况下会引起争吵甚至冲突。邻里有矛盾及亲疏不同都很容易理解,亲密无间的“共同体”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但从整体而言,长期居于一地的民众朝夕甚至世代相处,相互之间自然会熟悉。
至于乡内,为了行政的方便,秦以就近里的原则设乡【13】,里聚间也不会路途太远,一般在一日脚程之内【14】。在这一状况下,乡内民众相互认识也还是可能的。而且当时存在不少户数相对较多的邑聚,并从中划分为几个里。商鞅变法时“集小乡邑聚为县”【15】,一般认为是在零散的小乡邑聚之上设置县【16】,这一县下有邑聚的格局应该一直得到延续。邑应有城墙,刘邦所在的沛县丰邑,在其起兵后,雍齿反叛为魏守丰,刘邦攻打“不能取”【17】,就与丰邑存在围墙之类的防御设施有关。而这种邑聚往往与乡相关,在对沛县丰邑的注释中,应劭即认为“丰,其乡也”,颜师古认为丰是“沛之聚邑”“邑系于县”【18】。里耶秦简8-1236+8-1791有“一邑二里”【19】,研究者认为这是指迁陵县下的都乡【20】;此外,9-450乡守尚“部启陵乡官及邑中”【21】,乡部“邑中”,启陵乡也称“邑”。如果认为这种“邑”是城邑的形态,就与有垣墙之里类似,只是规模更大。即便不是,乡所辖部分里也会相对集中地分布,那乡内这些里的民众相互之间应该也很熟悉。因此,乡内民众间产生联结也不难想象。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认为秦汉民众都天然地生活在乡里之内。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认为,传统中国农民的社会边界是由基层市场区域而非村庄的范围决定的【22】。其研究的主要资料来自帝制晚期,早先历史是否存在这样制度化的农村基层市场及其作用不得而知,不过民众自然多少也存在交易的需要,其生活也就不可能只以乡里范围为界,而民众为生计进行流动的范围还会更大。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的《猩、敞知盗分赃案》【23】显示,在秦统一前夕,数人参与渔猎、掘冢、为佣、卖铜、为养等各种生计,游走于今湖南常德、湖北荆州地区的数县,并形成相应的人际网络。受限于史料,目前还难以见到更多类似的例子,但整体来看恐怕也并非少数。秦汉即便是北方,民众以渔猎采集为生或补充生计者并不在少数【24】;南方的楚越之地,按照司马迁的描述,“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25】,同时直到东晋南朝也存在众多农耕以外的其他生计方式【26】。按照班固的认识,“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27】,这些非农耕的方式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生计可能,也要求民众有较大范围的流动,商人更是如此,人们不可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一直居于里中。当时还有为数不少的流民,特别是在灾荒、战争期间【28】。同时,按照秦汉时代的风气,一些人群的活动范围更大,如游侠,会在各地之间流动,张耳早年就从大梁“游外黄”,刘邦布衣时也曾“从张耳游”【29】。再如游学,特别是西汉中后期和东汉儒学发展以后,游学之风更盛【30】。这些人显然都会离开乡里,不论主动、被动。
侯旭东著《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年版
民众地著并固定系于县乡里下,是国家统治的要求。农耕和农民本就是国家为方便统治,在国家的推动下产生的【31】,秦汉编户民的户籍均书“县里爵名”,这是时人最关键的个人身份信息。与此同时,这一定位不仅是标示其户籍地,实际上也是民众所属的官署及其一般活动范围。岳麓秦简《亡律》载“亡不仁邑里、官,毋以智(知)何人殹(也)”【32】。这里将“邑里”和“官”对举,分别指一般编户民和徒隶的所属机构。在秦汉国家结构中,所有人,无论编户民还是徒隶,均隶属、系于某确定的国家官署,并通过这一官署向国家提供劳役、赋税并接受管理。倘若“不仁(认)”【33】所属官署,也就无法知晓其为何人,失去了在国家秩序中的位置。因此,使民众始终系于官署,将人与户籍、地域固定在一起也就是国家实现对民众统治的必要方式【34】。
为了实现民众地著,秦汉国家有诸多官署、制度、律令控制民众。秦汉国家在交通道路上设置有各种官署,具有稽查、控制民众流动的作用,这从汉代西北简传文书的套语中可大致了解到。如肩水金关简73EJT9:247“过所县邑侯国门亭河津毋苛留”【35】,即如果没有传,路途中会遭到县邑、侯国、关、门亭和河津的“苛留”。在西北边塞地区,这些机构更多,原因也在于防备流民特别是汉人出逃塞外【36】。张家山汉简中,汉初户籍属于关中的南意图逃回齐地,就在函谷关被抓获【37】。而外出需要使用的传,要由申请者自言提出,里担保,乡审查及县发行等步骤【38】,即便是小事。马圈湾汉简796:
元康元年七月壬寅朔甲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䜣为千秋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39】。
女子赵负从所在敦煌县寿陵里到玉门候官千秋燧给丈夫送衣物,也需“以令出关”,并在玉门关接受盘查并记录、上报玉门候官。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这些程序和要求无疑极为繁琐,同时也缺乏在官府看来的必要理由。
肩水金关简73EJT9:247
国家律令也打击未经上述程序就擅自离开所在地的人,虽然未必成功。这些人被称为“亡人”,如前引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的《猩、敞知盗分赃案》中的数人。而岳麓秦简(肆)第一组的105枚简都是《亡律》,规定了如何对不同的逃亡及舍匿情况进行处罚【40】。不过《亡律》的严密也正暗示逃亡的普遍,这些并不算密集的机构也不可能限制民众流动,即便控制更严密的西北边塞地区也依然有汉民不时逃亡匈奴【41】。在内陆,实际上包括秦汉在内的华夏国家大多只能控制平原及其交通线,国家疆域内部存在相当多不能控制的隙地【42】,这也是《猩、敞知盗分赃案》中民众可以四处游走的原因。
从国家的角度看,既然是由县审核发放传,那也就意味着在这些限制下,一般民众“合法”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县境【43】。县内文书对民众身份的标识,包括户籍,往往只有里、爵、名,而没有县,里耶城壕出土的南阳里户籍就是如此,如“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44】。这也是学者对这批户籍材料是否属于迁陵县而产生争论的主要原因。户籍往往保存在县及乡,民众一般也不能外出,因此无需标注县名。如果涉及跨县婚姻等人口流动,要将户籍迁移到夫家所在县,经县之间的文书流转程序才标注县【45】。因此,虽然存在民众恐惧迁徙的心理,但“安土重迁”【46】传统的形成恐怕更多的还是国家限制民众流动的结果【47】。
但县的空间范围其实也不小。《汉书·百官公卿表》笼统地概括县的面积为“大率方百里”【48】,邢义田对此有比较细致的讨论【49】。更具体的例子是里耶秦简中迁陵县下三乡,除都乡在县廷附近外,启陵、贰春两个离乡都相对较远,官府文书传递亦需累日【50】。民众在范围小、人户少的乡里可通过面对面的来往而相互熟悉,甚至能为某些事务组织集体活动,但扩大到县时,想要熟悉就很困难,这可以从民众的婚姻距离来理解。彭卫认为,汉代以近距离结婚为主,包括同村、同乡、同县或邻县,远者可在一郡之内,并举了几个传世史料的例子【51】。因为传世史料样本的不足,且记载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上层,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相对宽泛的认识,无法更精确地判断。相关情况可参考后世关于通婚圈的调查和研究。据1988年在湖北省麻城市王福店乡农村的调查,该地婚姻距离7.5公里以内的占绝大多数【52】。两者时间相差两千多年,自然会不一样,但在市场化大潮之前的农村可能与传统时代存在相似之处。当然,具体个人的婚姻圈不一定只局限于附近,就如史料中有跨乡甚至跨县的婚姻,但整体来说,更多人的婚姻距离恐怕还是在几公里内。通婚的范围如此,显示民众日常密切交往的距离也不会太远。因此,县范围内民众的联结,就不能简单用同一地域的自然交往来解释。如前所述,秦的全面县制是在商鞅变法以后开始推行的,方式是在原有小乡邑聚之上设县,目的是为了方便控制地方。那么相比乡里,其与社会自身形态、秩序的关联本就小,因此也要从国家的角度理解民众的县内联结。
二
徭役与县内民众的联结
在国家的设计中,民众遑论出县,甚至都不用出乡。制度设计中的编户民,应当是平时在田地耕作,于里内休憩。其耕作的田地,里耶秦简9-543+9-570+9-835存在都乡黔首田在两个离乡界中的情况:
刍稾志。AⅠ
□□□□□□□□AⅡ
· 凡千一百七钱。AⅢ
都乡黔首田启陵界中,一顷卌一亩,钱八十五。BⅠ
都乡黔首田贰【春界中者,二顷卌七亩,钱百卌九。】BⅡ
· 未入者十五BⅢ【53】
这是征收刍槀税在县一级的统计,其中将黔首田在他乡界中的情况单独列出,表明需特别处理,也即民与田分离,难以将这部分税独自计入某一乡。因简牍残断,我们难以确知AⅢ行的“千一百七钱”是否是三乡刍槀税的总计以及其中是否包括后面都乡黔首田在离乡界中的数额。不过,民、田不同乡的刍槀税相对较少,需单独列出也显示这是特殊情况。从官府的角度而言,每次单独统计这一特殊情况,进而在征收环节单独处理,都十分不便。那么可以认为,一般情况下,民众的田应都在本乡。同时,与官府相关的赋税缴纳、户籍登记等事也都由乡官完成,不用出乡。
而国家制度中民众必须出乡的,是徭役。按照渡边信一郎的划分,徭役分为内外两种:所谓内外是指郡之内外,内徭主要是指更徭与正徭,外徭主要是在中央与边疆的兵役以及财务运输的劳役【54】。首先是内徭,特别是其中的更徭,主要应该是在县内服役。自浜口重国以来不断被讨论的如淳说,其中有“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一句【55】。虽然学界对更数等问题争论不休,但对更卒是在县中服役则没有什么疑问,只是一般也根据颜师古注“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56】认为更卒有在郡内服役的情况,渡边就是以郡划分的【5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更卒就是在本县服役的【58】。不论如何,只有县及乡才掌握民众户籍,可以以此为凭具体组织徭役,而从秦汉徭役征发程序看【59】,县也是徭役组织的中心【60】。松柏汉墓所出第74号木牍,以县或侯国为单位统计用卒数量【61】。从更卒之役的内容看,按照藤田胜久的概括,包括郡县城郭营造、县城周边基础设施维护、郡县内运输和水利工程【62】,大多也应在县内完成。
其中有专门的所谓“邑中事”的役事,根据宫宅潔和小林文治的理解【63】,其具体内容见于下条岳麓秦简《徭律》:
补缮邑院、除田道桥、穿汲〈波(陂)〉池、渐(堑)奴苑,皆县黔首利殹(也),自不更以下及都官及诸除有为殹(也),及八更,其睆老而皆不直(值)更者,皆为之【64】。
这也就是藤田所概括的县城周边设施维护,不过两人都认为“邑中”是乡内部的某种地区【65】。但这里提到了这些劳动是“县黔首利也”,那应该不止于乡,而是县内【66】。邑院、道桥、陂池和奴苑皆是县内的一些基本设施,需要定期维护。岳麓秦简另一条《徭律》规定,“给邑中事、传送、委输,先悉县官车牛及徒给之”【67】,似乎“邑中事”应该由官府徒隶完成,但据研究,实际上基本仍由民众承担【68】。从律文规定的“为”此事者来看,应是官府组织民众完成的。小的设施可以由乡组织,但若较大及跨乡,则无疑需要县的介入和调度。整体而言,这些各类劳役当然会使民众劳苦,但另一方面也让民众不得不脱离乡里社会进入县域,从而有机会与其他乡里的民众相互认识,搭建起关系网络。
其次是外徭,民众还需要外出服徭役和从军。从西北汉简看到的汉代外出服徭役、从军的方式,是本地服役人员被集中到郡治所在县,然后由郡派出的官吏带领到服役地,一般是京师或边地,返回也同样【69】。不过,秦及汉初郡的权力集中程度不及后世,仍具有中央派出性质,不是地方行政的中心【70】,服役人员应该不用到郡集中而直接由县派出。岳麓秦简一条关于传槥的规定可以为证:
· 令曰:诸军人、漕卒及黔首、司寇、隶臣妾有县官事不幸死,死所令县将吏劾〈刻〉其郡名槥及署送书131,可以毋误失道回留。· 卒令丙卅四 132【71】
岳麓秦简131-132
即在外地的军人、漕卒和为“县官事”而不幸死的黔首、司寇、隶臣妾,需由“县将吏”“刻其郡名槥及署送书”。“将”在秦汉文书简中较常见,表示带领某人某物前往某处【72】,所谓“将吏”就是率领军人、漕卒等服役者的吏【73】,而“县”应是这些不幸死难者的派出县也即其户籍所在县。“县将吏”显示,在秦代,这些服役者正是由县派出的。当然,此处“县将吏”需要刻“郡名”,是否表明与郡有关?这其实是当时文书制度的规定,当跨县行文时需写郡名以区别上级属郡【74】,此处传槥及其文书写郡名也应如此理解【75】。
这也可以得到传世史料相关案例的佐证。刘邦“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76】,即刘邦作为县吏亭长带领沛县之徒去京师服役。“徒”在简牍中多指徒隶,不过也有不少文例显示是指服役的民众,两者均可称为“徒”【77】。在骊山劳作的,应该既有徒隶,也有服役之民众,而刘邦所送之徒,应是服役的民众,学者对此已有辨析【78】。刘邦所送之徒中的樊哙(详后),显然就是沛县的编户民而非徒隶。刘邦“常徭咸阳”【79】,其中不少应与送徒相关。总之,秦代是县安排吏员,即“县将吏”,率领本县服役者前往徭役地的。
而在服役地,来自同一县的戍卒也会被集中安排在一起。里耶秦简8-1517迁陵仓上行县廷的呈文中,“疏书吏、徒上事尉府者牍背”,而牍背的吏、徒包括“令佐温”“更戍士五城父阳翟执”和“更戍士五城父西中痤”【80】。除了“令佐温”外,其他两名戍卒均来自城父县。9-2209+9-2215中提及的两位戍卒,也同样都来自城父【81】。《里耶秦简》(壹、贰)中,迁陵县有不少来自城父的戍卒,兹列表如下:
表1 《里耶秦简》(壹、贰)中的城父戍卒情况表
上表中,17~19项的三人没有被明确记载为戍卒,姑且不论,另外16人都是从城父县到迁陵县的戍卒。其中部分有纪年的简,时间分布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到三十五年(前212年),自非同一批戍卒。但案例8、9、10、12、14的时间相距很短,最多不过十个月,他们应是同一批戍卒。不止里耶秦简,西北汉简的吏卒簿籍中,同县戍卒也被集中安排在一起服役【82】。
里耶秦简8-1517
那么,同县之民出县后相当长的时间都会共同生活、旅行以及服役。一直在原生地的人感觉不到自己同为一县的关系,如前所述,县内包括户籍都不会写县名,因为没有必要。但当走到他者的世界,面对异于自己的人群,包括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习惯等,就会陡然意识到自己的特质。而这一特质是群体的,其最明显的标识和概括就是县。县既是载于户籍的官署和他者的称谓,也是自己习惯的故土,更是具象为此刻在同一县名下共同在外服役的人群。
共同的他者经历会增进相互的联结,特别是面对与外人的冲突时。项羽败章邯军后,《史记》追述“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的,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83】。这些徭使屯戍的吏卒,是以县为单位过秦中的,那么被“遇之无状”,就是群体性的,会成为群体间的情感倾向与印象。这一事件中,具体的秦中吏卒对具体的山东吏卒的“无状”,想必项羽所降秦军和诸侯军之间没有多少具体的伤害与被伤害者,但后者将此扩大到对整个秦中民众的仇恨,从而导致二十余万秦军被坑杀。与其他群体冲突、仇恨相反的另一面就是内部的凝聚,来自秦人的“无状”加深了自己山东六国身份的感知。同时可以想见,在外徭役的民众,面对的还不单是与秦人的矛盾,而是更多向的。即在赴役和服役的过程中,也会与来自各个地方的以县为单位的不同人群发生冲突,而在外地唯一可以依恃的就是这些本就在一起的本县同乡。这些具体、多向、群体的冲突会增加县内服役者的内部感情,并强化对自己县的身份认知。
其实长期的在外共同生活经历,本身就会增进内部的联系和感情。陈胜、吴广带戍卒赴渔阳,其中,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故而特意挑起将尉对吴广的侮辱,从而“激怒其众”【84】。能够激怒戍卒,除了共同的被将尉侮辱的感同身受,更因为吴广与戍卒们在行戍过程中的感情积累。刘邦送徒的过程中“解纵所送徒”,但仍有十余人“愿从”【85】,也是在“送”的过程中特别是“纵”的行为带来的信任。英布则是作为刑徒在骊山服役期间,“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86】。虽然这些“曹偶”应该不是同县人,但可以提示我们,同一空间的共同生活、劳作提供了相互联结的场域。张家山汉简中,原是齐国田氏的女子南被迫徙陵到长安,同乡故齐都临淄的狱史阑送行。从临淄到长安,漫漫两千余里、一个多月的行程,两人相爱并成婚,最后意图“偕归临淄”而被捕【87】。不论是男女的相爱,还是对具体人的信服、“交通”,都是在外长期共同相处中产生的人际联结。
当这些同一县来自不同乡里的人经过这一历程后,再回到县内,也会形成超越乡里的关系网络。这里可以举刘邦和樊哙的例子。樊哙是元从之沛人,与丰邑的刘邦应非同乡。《史记》对其与刘邦在微末之时的关系记载,是“与高祖俱隐”【88】。所谓“隐”,是指刘邦纵徒之后为躲避官府惩罚,亡匿于芒、砀山泽之间。增渊龙夫对樊哙之“俱隐”是“徒中壮士”十余人之一还是后来加入,存有疑问【89】,李开元则直接将其当作刘邦所送“徒”之一【90】,但没有论证,在此可稍做补充。按樊哙本传记载,“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91】,也即在丰邑随刘邦起兵,那么“丰”指的哪里呢?刘邦正式反秦是在沛县,“起丰”在“下沛”之前,而流亡的芒、砀山泽又不在丰沛,樊哙追随刘邦的时间只会更早。恰好《高祖本纪》载刘邦“纵徒”而后十余人从,是在“丰西泽中”【92】,显然樊哙就是这十余人之一。两人之前恐怕没有太深的关系,不然就会如夏侯婴等人一样被详细记述。而与其产生紧密联系,甚至成为连襟“比诸将最亲”【93】的契机,应该就在这一段亡匿的过程中。沛县要起事反秦,是萧、曹等“令樊哙召刘季”【94】,那么樊哙实际上也常在县中,游走沟通两边,帮助刘邦维系了之前与沛县的关系网络,故而能够以沛县起兵。虽然这一例子比较特殊,但还是可以略窥回县之后的联结关系及影响。
顺便可以提及的是,按“起丰”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从《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找出“愿从者”十余人中的另外几位:
表2 《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起丰”侯者表
不过奇怪的是,在《史记》本传中明确记载“起丰”的樊哙,《史记》《汉书》两表均记为“起沛”,不知何故,但还是列入上表。此外,《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起丰”的还有安国侯王陵和煑枣侯赤,但《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各记为“以自聚党定南阳”和“起薛”,煑枣侯亦名“革朱”【95】,王陵在《汉书》中有传,事迹较为清楚,是在南阳属汉,煑枣侯未知,两人暂不列入。即便如此,这“十余人”中就有十人封侯,超过一半。再考虑在汉朝建立的过程中未必没有因战争、疾病而死者,那这一比例将会更高。
上表中,除了没有记载的冯无择,另外九人初起身份均是舍人、中涓、卒。这些身份在学术史上有特殊意义,西嶋定生正是因认为这些是刘邦的家内奴隶【96】才提出其旧说,其后,守屋美都雄、增渊龙夫均在重新理解这些身份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说【97】。后来学者得出土文献之助,对舍人等个别身份的研究有所推进,也多认为是侧近或某种主从身份【98】。李昭毅认为,舍人、中涓、谒者、执盾等是侍卫近臣【99】。不论如何,诸说都认为这些身份与刘邦存在更私人和亲近的关系。早年共同赴役、亡匿的经历所积累的感情以及最早追随刘邦而获得了更多立功机会,在国家建立后转换为切实的官爵。
而这些外出回来,特别是从军而归的民众,相对也更具有眼界、能力,甚至产生身份的变动,在乡里社会成为主导者。邢义田在讨论汉代的军中教育后,提出一个没有解决但可以想象的问题:汉代内郡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田家子戍边,有机会接受教育,包括骑射、识字、计算及其他特殊的技能,成为见过世面有“文化”的人,会对地方造成什么影响【100】。管见所及,没有直接的材料能解释这一点,不过很容易想象的是他们会在乡里更有影响力。从汉初《功令》的“功劳式”来看,对一般的为吏和从军为吏、一般功劳和军功劳都有区分,功劳的计算上,前者四岁劳为一功,后者只需两岁【101】。当然这是为军吏的情况,与一般军卒不同,但后者有机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岳麓秦简《识劫案》中,本为“隶”的识有从军的经历,其公士爵位应该就是从军获得的。而入宗时找的几位里人、宗人,作为里内社会的领袖,分别有大夫、走马、上造的爵位【102】。当时尚是秦统一之前,爵位几乎只能由战功获得,这几位也不能例外。这些军归者一方面联系着其日常生活所熟悉的乡里民众,另一方面在相互之间又存在联系,由此搭建起整个县的关系网络。
邢义田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年版
综上,徭役使民众不得不走出乡里,甚至走出县,出县又以县为单位赴役,这都编织了参与者的县内关系网络,产生相互的感情、联结。而徭役是反复不断进行的,同时徭役的参与者也并非单独的个体,而带有自身的关系。这些反复、日常的徭役由此成为民众县内联结形成的重要机制。这为国家秩序崩溃后,民众以县为单位联结起事提供了契机。
三
官僚制国家运作下的民众联结
当然,使民众走出乡里而在更大范围的县内获得联结机会的,不会只有徭役一种机制,只是这是涉及当时所有男性编户民的事务,能最大规模地将民众纳入其中。徭役由国家官僚机构组织并维系其运作,而事实上,官僚机构及其运作,本身就会为县内人群的相互联结提供机会。
官吏需在一定的场所处理公务,这会导致他们的集中。以迁陵县为例,今天发掘出的南北210.4米、东西残存103~107米的里耶古城被认为是秦官府聚集地【103】,县廷就在其中。古城东面被酉水冲毁,东西向应该更长,但对照南北向也最多不过两百米左右。而迁陵县的尉、司空、仓、少内、库和都乡等官应该就在县廷不远处【104】,那么这些官署就集中在县城及其附近这一并不算大的空间内。当然,迁陵县比较小,其他县的城邑应该会大一些,不过,县廷及其他官署所占用的空间恐怕差不太多。因此,县内的相关吏员,包括县廷的令、丞、令史,周围诸官啬夫、佐以及低级佐史就汇集于此,同时县内其他诸官也需日常派员到县廷处理各种事务。由此在一定空间内形成一个围绕县廷及其政务运作的人员网络。此外还有县内其他公务的展开,比如夏侯婴担任沛廐司御,这一工作需要“送使客”,而在送的路上会有亭等机构,刘邦正在泗水亭中。夏侯婴“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105】,两人因各自的工作而熟识。
里耶城址2002年发掘探方分布图,见湖南省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6年版
政务运作为官吏们提供了结识的机会,他们也由此发展出一些机制性的交往。秦末沛县令有“重客”,县内豪杰吏“皆往贺”【106】,这固然是攀附县令,但也展现了官吏们的相互交往。刘邦“以吏徭咸阳”,沛县“吏皆送奉钱三”【107】,显然存在一种县吏间的交往、互助圈子,并有默认的“奉钱”标准,是一种惯例化甚至制度化的交往机制。既是机制,也就会反复发生,维系县内官吏的私人关系及其群体网络。而且这也非一时之风气。在西汉末的尹湾汉简中,有两枚被整理者命名为《赠钱名籍》的木牍,一般认为是助丧钱的名籍。不过其中有一行为“之长安”【108】,研究者认为这是接受捐钱的用途【109】,其中包括明确写了官职的“萧主簿”,应是为去长安徭使所接受的钱【110】。
这些在县内展开政务的,也多是本县人。严耕望延续顾炎武说,提出秦汉“州郡国县道侯国政府之属吏皆由长官自辟用本域人”【111】。岳麓秦简《置吏律》业已证明这一点,县除任“有秩吏”及“小佐毋秩者”,皆需“各除其县中”【112】。那么这些属于本县的有秩吏与无秩小吏,也就借助官僚组织提供的场域有了结交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真切的感情。刘邦麾下出身沛县吏的重要成员,除了萧何早与刘邦熟识,夏侯婴、任敖均是其任亭长时结交的,并为保护刘邦及其妻子而受难或冒险。曹参与刘邦的早年交往未见记录,未必如前三人般关系深厚,但定然也是这一官吏网络的成员。
不过同样是岳麓秦简,其中有相当多“新地吏”的规定,即由外地调入为吏,而非本地人。游逸飞、鲁家亮对秦迁陵县的吏员构成有详细梳理,相当多来自外地【113】。但迁陵县十分特殊,因其偏远,除了官吏外,戍卒、徒隶甚至一般民众也有不少并非当地人,以至于被游逸飞称为“移民社会”【114】。至于新地吏本身,其来源多是犯罪、病免、考课为殿的旧地官吏【115】,有明显的惩罚性质,应属少数。并且外地为吏还面临高昂的成本问题。张家山三三六号墓出土汉初《功令》,“彘官大夫若思等五人、阳平公乘纵等二人”请求“家去官远,不能自给,愿罢,得复归居县须缺”,中尉以此请求“所前调河东郡为都官佐未迁欲罢者,比若思等”【116】。因都官的官署离家太远,官吏无法自给,所以请求归县,朝廷也同意,且其他“调河东郡为都官佐未迁欲罢者”可比照办理。这还是等级相对较高的人数尚不多的都官佐,如果要大范围地跨县调度低级小佐,成本更难想象。所以整体而言,“除其县中”才是更通行的原则。
上述分析似乎显示的是官吏这一县内精英群体的交往,但其实这一过程也不止于人数相对较少的官吏群体。官吏本身就是县内人,有其自身的关系网络,如同前述成为乡里领袖的军归者一样,他们也会成为关联县内关系网与乡里社会的节点。更重要的是,县的政务运作不能只靠官吏,还需要众多徒隶、编户民承担具体的差役,而这其实也算是民众徭役的一种。这些政务差役很多应由徒隶完成,不过也有不少有一般民众参与。里耶秦简的行书记录中,8-166“高里士伍□行”,9-1095“高里士伍赤以来”【117】。这里仅标注了里和士伍身份,没有具体的职役,应是高里民众被临时差遣行书。此外,县内的邮、亭、置等机构也需要供给、维持,这都要求当地民众的参与【118】。还有别的具体差遣、役使甚至任低级佐史的供役方式【119】,夏侯婴担任的“沛廐司御”,其实就不是官吏,因为他后来才“试补县吏”【120】。相比官吏们,差役的人数更多,前述围绕政务展开而形成的人员网络中,这些民众也在其中,行书的高里士伍就借此穿梭于县内诸官署(包括乡)之间。正如夏侯婴以此结识了亭长刘邦一样,这些参与政务运作的民众也在县内有了更大范围联结的契机。
前文一直强调这些联结在县内,这当然是因为国家对民众流动的限制,不过时人也并非没有县外的联系。长期生活在战国时代的人特别是相对精英的人群,凭借其自身的活动与家族的势力,自然有更广的关系网。“世世为楚将”的项梁“有栎阳逮”,可以“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而得免,后来杀人还能“避仇于吴中”【121】;五世相韩的张良甚至在刺杀始皇失败后还能“亡匿下邳”,并在县内圯上“闲从容步游”【122】;相对下层的刘邦任侠而结识张耳,其岳父吕公也可从单父避仇来到沛县为县令客【123】;西北边塞烽燧遗址出土的私人信件简牍,是汉代边塞官吏所经营的官场网络的见证,不少跨县甚至相隔遥远【124】。而一般民众,除了前文提到的亡人外,里耶秦简9-1095也有迁陵县与酉阳县的跨县婚姻【125】。迁陵、酉阳两县相邻,具体到两人的乡里还会更近。很难认为这些相互临近的乡里民众的联系会被县的边界切断,我们也很怀疑两县是否真的会在其间设置关卡专门阻拦双方来往。事实上,如前所述,广泛存在的隙地也无法都被控制。他们应该还是会按照自然的距离相处,延续其长期甚至世代积累的关系,秦简中的婚姻即证明。
但是,县无疑制造了边界,原先各自发散的交际网络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县也产生了中心,并以徭役等政务和官僚组织为媒介,围绕这一中心重构了民众的生活世界。县界虽然没有实际的隔挡,但至少理论上跨越它需承担风险。即便两县相邻,乡里民众可以自然相处与延续关系,但当需结成婚姻时,还需要两县的乡、县廷为此专门行文,移交民数,由此才产生了9-1095这枚简牍,这无疑增加了成本。而反复的徭役征发和官僚机构运作,则将民众纳入所在县的组织网络中,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交往圈。原先的网络当然并未消失,上节已有描述,只是在其中嵌入了一个新的机制,并挤压前者的空间,逐渐修剪出一个与国家行政体系重合的交际网络。
这一过程当然是漫长的,秦的统一仅短短十余年,不过县的历史却很长。姑且不论春秋时期含义不同的县,战国虽然文献缺失,但一般认为此时各国已普遍实行县制【126】,秦的统一对各国县域的调整应该不会很多。就秦地而言,从商鞅时期“集小乡邑聚为县”开始,以县为边界和中心的民众联结网络的修剪、整合就已展开。对刘邦等人所在的楚地而言,战国时期县的制度与运作虽与秦不一致,但基本的徭役和官僚组织也不会少,到秦统一后自然更加强化。
以行政区域为地域认同的单位,并在其中搭建人际网络,这并非只存在于秦汉,而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直到今天,只不过从郡县变为后来的省府州县,或今天的省市县。后世如何具体修剪时人的观念或生活空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既然与政区重合,那理应还是离不开国家的作用。
如果要简单概括的话,那就是这种民众的联结与官僚制国家的运作和塑造有很大的相关性。战国以来官僚国家的形成,不仅只是一种国家制度体系的变革,而且必然会介入民众的生活,并在日常的运作中塑造后者,以与官僚国家“适配”。这是一种弥散性权力,也可以说这一联结与认同只是官僚国家运作下的“副产品”。国家当然是无意的,因为对秦代国家发起的叛乱,之所以呈现以县为单位的“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的状态,正是来自于此。虽然自韦伯以来的官僚制论多关注其理性化【127】,但毕竟参与运作及影响的都是人,国家塑造了这一以县为单位的联结与认同,但决定其如何发挥作用及作用对象的,还是其中的人。
进一步而论,民众一些看似自然的交往,也未必与国家无关。民众间的交易及其基层市场,被施坚雅视为农民的社会边界,似乎是自发的。其中当然有不少基本需求是如此,但民众的交易也存在一个很强的动力,就是换钱。秦汉在内的古代民众生活本没有多少用钱的必要,是国家以钱币为纳税方式,使得民众必须进入市场,用农产品换取钱币【128】。同时如前所述,农耕及地著是国家统治的产物,乡里虽然具有民众聚落的意义,但也同样是国家的基层制度。乡在秦代的制度中,是负责管理民户及其附着地域的诸官之一,其国家性自不待言。而里作为聚落,是“自然村”还是“行政村”,日本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争论【129】,此不拟多论。不过,国家试图规划里的形态已有岳麓秦简的证据【130】,在其设计中,里都应该有里门、垣墙,形成封闭聚落【131】。可以设想,在秦的国家构想中,统治的理应是一个个独立的孤岛,而这一封闭状态又会增加内部的联系和凝聚。此外研究者也关注乡里内民众的组织,因材料较少的关系,多以河南偃师出土的“东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为主进行研究,相当多意见认为父老僤与征发赋役或均平赋役相关【132】。
但从前文的论述可以发现,民众生活在一个个独立的孤岛中的认识只不过是一个幻象。一方面是民众自身因其生计、生活的需要而流动,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为民众在乡里熟人网络之外的联结提供了契机。而且这一联结的空间可能还会很广,不论是一般民众远赴京师或边塞,还是官吏在官僚系统中被调动、迁转、徭使到外地,均远离了乡里故土。当然,服役民众外出时间相对较短,也难以积累并保持与外地人的联系。但官吏超过二百石则要在全国范围内调遣【133】,并可借助国家的邮传系统外出或书信往来,构建起全国范围内的交际网络。出土简牍中私人信件的问候,《质日》【134】或《日记》【135】简的官吏外出记录以及里耶秦简中的徭使吏员文书【136】,都是这一超出县域甚至全国范围的人员与信息网络的见证。倘若没有超大规模的国家及其官僚组织的运作,对当时的吏、民个人而言,这也是难以想象的。限制、塑造与机会,这些都是国家对于时人及其生活的意义。
结 语
秦汉时期民众的主要生活和交往范围是里,虽然邻里间难免存在矛盾,但因长期甚至世代相处,自然会形成密切的关系。而乡的范围也不大,特别是存在不少邑聚之乡,相当于扩大化的里,乡内民众有机会相互认识。不过民众也非天然居于里中,因存在农业之外的其他生计方式及生活需要而必然产生更大范围的流动,地著并系于县乡里下,是国家统治的要求。为此国家产生了诸多官署、律令、制度,导致民众“合法”的活动范围就是县内。但县的空间范围也相当大,民众在县内的联结显然无法用自然交往解释。
在国家的设计中,民众的耕作、休息及与官府相关的事务都可以在乡内完成,必须出乡的是徭役。更卒之役,特别是其中的“邑中事”,是由县级官府组织县内民众完成的,从而使民众不得不进入县内的联结网络。此外还要外出服徭役、从军。同一县的服役、从军者以县为单位赴役、工作和返回,长期的相处及其与其他人群的冲突,使民众意识到以县为单位的自身群体特质,强化了对自己县的身份认知,并增进相互的感情和联结。当回到县内,就会形成超越原先乡里的关系网络。而且外出归来,特别是从军而归的民众“见过世面”,并有机会获得书写等技能及爵位,容易成为乡里社会的主导者。此外,官僚组织本身也会为县内人群联结提供机会。秦汉县内属吏辟用本县人,围绕官僚组织及其政务运作,这些属吏及承担政务差役的民众形成人际网络,并发展出制度性的交往机制。军归者与官吏这一自身在乡里社会具有影响又相互存在关联的群体,搭建起整个县的关系网络。秦末特别是楚地的起事,呈现出以县为单位“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的状态,即是由这一以县为单位的民众联结提供的契机。
民众间的联结与国家的运作、塑造存在相当的关联。当时民众虽然仍存在更大范围的交往,但县界一方面限制了流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反复的徭役征发和官僚组织运作,在战国以来长期的县制历史下,修剪出与国家行政区划体系重合的联结网络。后世民众以政区为联结单位,也离不开国家的作用。官僚国家在其日常运作中,以其弥散性权力塑造了民众的生活。
最后也必须承认,本文所关注的县内联结是用倒溯的方法“发现”的。所谓倒溯,就是先注意到秦末楚地以县为单位起事的结果,而后倒溯历史寻找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倒溯的历史当然也是历史,只是夹带了历史的后见之明而放大了某一原因的重要性,并忽视别的面向【137】。具体到这里,站在时人角度,其生活世界和关系网络中,国家徭役、官僚机构运作等带来的人际联结,只是相当小的部分。这又与“联结”的程度问题相关。本文将民众间从认识到密切关系都称为“联结”,似有泛化之嫌,但这也正是时人生活的状态。县一级的联结关系,对于官吏而言或许比较强,对一般民众则相当微弱,微弱到其本身都未必能意识到。只是后来起事发生了,需要组织、形成一个团体,而这一原先存在的县内联结关系恰好提供了一种组织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起事中的父老、任侠等关系,也是组织资源之一,且未必互斥。父老、任侠以及被西嶋定生收回的家内奴隶旧说,都是以刘邦集团为例,本文也多利用相关记载,这都是其不同面向,共同为时人取用。同时,倒溯也强化了因果关系,即民众以县为单位起事似乎就是因为原先的联结关系,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止于此。事实上,应该倒过来说,是这种带有一定自发性的起事,为我们展演了县域联结关系的存在,并得以由此窥见国家在其中的作用。
(说明:本文所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在此致谢!)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9期
编辑:阎浩华
审核:安 瑞
监制:苗书梅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