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羊孩贾尔斯》的叙事形式要复杂得多,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有两组张力共同构成了巴思作品的悖论性张力。第一组张力存在于隐喻与反讽之间:隐喻试图在语言中寻求并肯定某种模式,而反讽则借助隐喻来否定其自身的有效性;第二组张力则存在于隐喻内部,即在元小说(对语言与小说自身进行自我反思)与形而上学(关注人及其宇宙)之间的张力。
关于第一组张力。首先,隐喻与其说是隐晦的,不如说已经偏离了它的原始义而表现为赤裸裸的。东西学院之间荒唐史和剑拔弩张的现状直指二战历史——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美国对日本的终结——和冷战的东西方对立。巴思只不过把世界浓缩在一所大学之内,仿佛尽职的纪录片导演一样展现一段事实,甚至没有夸张,因为现实往往比小说家虚构的东西更诡异、更暴力、更灭绝人性。
另一方面,隐喻仿佛就是描述,它不需要本体和喻体的区分,二者合为一体。当贾尔斯被关进监狱,在“高温、尖叫、狂笑、恶臭”之下,体会到“通过即挂科”,明白了那句话背后的真义,准备受难,直到命尽。这时,有两件事出乎他的意料:“古老的西校园里,灵魂死后的图景竟和现实一模一样,而非只是生动的隐喻——实在的铁、粪便、火焰、喊叫声和其他的一切,我觉得还有真实的竖琴和牧歌!——对我的惩罚,至少就目前而言,是严格按照对人的惩罚进行的。我自幼成长的畜栏比这狭窄得多,睡觉的地儿也比这儿尿味大;奠基人肯定清楚,相比于人类,我倒不怎么厌恶这里。难道是因为罚期永世,所有的惩罚都无休无尽,因此什么都一样?或者是奠基者智识无边,特意为自觉聪明的我选择了这个山羊圈,来讽刺我给人类指导?无论怎样,是眼前事还是其他事,都结束了。我脖子疼,此外我还挺舒服,浑身上下有一种惬意的疲惫感。我赤裸着,浑身满是污垢,安享着这黑色的高温、彻底挂科的温热。我挂掉了一切,什么都没通过!志向、怀疑、责任、害怕挂科之感统统被抛之脑后,解脱之感席卷全身,悲伤与恐惧不再,我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在这种隐喻所带来的肯定模式下,反讽则凸显出一种否定性,既否定隐喻的本体,也否定反讽自身。“斯托克挂科院长的资格和艾拉·赫克托的自私模棱两可、安娜斯塔西娅易被利⽤的慷慨、 马克西的代人受过、 格林的纯真、 艾尔科普夫的苦行主义和克罗克的纵欲无度”,这些行为或身份本身,都极其可疑。
艾拉·赫克托是新坦慕尼学院最富有又最吝啬的人,贾尔斯为他的身份赋予了合理性——“自私挂科,但将财富据为己有实际上是无私的……”——和行动建议——“把你的全部都捐给爱哲基金会和新坦慕尼产房之后你将⼀⽆所有,并以别人为代价来通过自己。这是最堕落的事情,你要明⽩,挂科就是通过。当那些松垮的⼀代再来,不要只告诉他们时间,他们想要什么给什么。把你背上的衬衫都给他们”。
故事中我们看到,东西学院都致力于要消灭对方,但它们却共用着一条供电线,其动力来源归撒旦所掌管;决定生死的既不是东学院,也不是西学院,而是人性当中的阴暗力量。或许表明,人类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一来存在本质上的不可能,二来一定会将人类自身全部带入地狱。
关于第二组张力,我们可以说巴思是野心勃勃的。他赋予了自己三重身份:叙事者、对叙事的评论者、思想者。尤其是最后的身份,很少有作家会把形而上学纳入到叙事当中,因为小说是一种感性的艺术,读者希望被感动更甚于被要求思考。然而在这里,巴思却给很多人物赋予了哲学身份,斯开普拉思代表柏拉图,隐德莱希斯代表亚里士多德,马约代表苏格拉底。
雷克斯福德在他的演讲中炫耀隐德莱希斯主义,而贾尔斯竟然指出了其中的悖论性:“如果中庸与折中的原则也折中中庸的话,这原则便失去了意义。”而且,对于某些行为,即使中庸也是不可取的。“隐德莱希斯自己曾警告世人提防’极端中的中庸’,意思是人不应撒谎、欺骗、偷窃、强奸或谋杀,即使小心谨慎地进行也不行,而应彻底避免上述恶行。而(我尽力用着客观的解说语气)通奸、家暴、酗酒以及各种暴力行为也同样如此。问题不在于何时、和谁、程度与频率如何,而在于到底有还是没有。答案就是不该有。”
院长雷克斯福德指出西学院从来奉行的就是隐德莱希斯主义。“与尼古拉人在尽可能多的方面进行往来,微妙而广泛地参与到两院事务中。两院虽在理论上存在矛盾,但缓和将成为两院关系的现实,而暴乱则无异于经济层面的自毁,肉体层面的自戕。长久存在的边界争端——如今几乎如同机构一般,有着自己的预算、办公点、管理人员、办事程序和出版物——为我们提供了与尼古拉学院,与其他较小的学生会主义学院接触的机会与机制。举个颇有讽刺意味的例子:边界上的接触同会议桌上的谈判一样,没了它们,两边的间谍与反间谍部门将失去用武之地;并且没了像边界争端这样妥帖的’战线’,秘密外交这一处理两院重大问题必不可少的举措,实施起来将变得困难重重。”
“如果没有这个争端,我们还得重新造一个,⋯⋯比方说,尼古拉学院的一位代表,这人自称X同学,说了只要新坦慕尼阻挠唐学院加入大学委员会,他的学院就拒绝缴纳会费。而他实际意思是,他们也不想让唐学院入会,但不好直说。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反对唐学院入会,让尼古拉学院拖欠会费拖得不失颜面,尼古拉人也不会干涉我们在其他学院的扩张作业。我们明白他的言下之意,X同学也清楚我们明白;所以我方代表心照不宣,只是谴责有些学院不缴纳会费,并威胁我们也不交了——实际上我们会交,因为如果大学委员会倒了,我们的损失可比尼古拉人的大得多。⋯⋯”
稍微熟悉一点历史的朋友都可以从上述雷克斯福德的叙述中感受到现实政治的功利性、妥协性和黑暗性,仿佛交易才是其中的核心,马基雅维利主义因此体现出了相比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这些思想家更多的深刻性。“对于一个长在羊圈里,⋯⋯这些一定感觉非常阴暗。”何止贾尔斯会,我们大多数人也会,而且我们甚至会有一种不愿承认的倾向——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一旦知道,我们就会开始怀疑正义和善只是政治用来利用和玩弄我们的东西,我们无法忍受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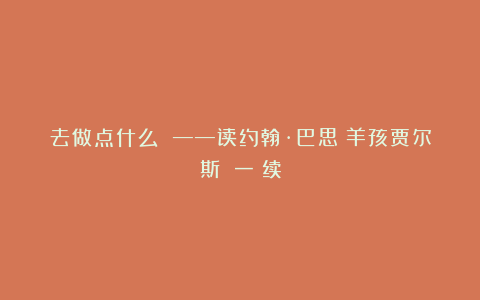
巴思并没有止步于让贾尔斯化身为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仿佛这样就给他披上了弥赛亚的哲学外衣,赋予了他更多的正当性。他或许仍旧在玩弄隐喻和反讽,即使一个时刻会陷世界于毁灭境地的政治困局,一头羊也能够轻而易举地给出方案。
贾尔斯提出了“应用隐德莱希斯主义解决边界争端的正确法子”——把输电线分开,让研讨会休会。也就是东西学院之间的彻底分离,“这就像斯托克,或是挂科院长,或是一场恶疾。⋯⋯你要是和他们打交道,你非输不可。你应该中庸之中持着激进的态度,一刻都不能向挂科妥协,或混淆两种相反的事物。拱门显然不能横跨真与假,真假就应该用跟无限分割器一样锋利的刀刃切割,并清楚分开。”
“向代表挂科的力量妥协——向X同学或斯托克妥协——就像向恶性的细菌妥协一样:在温和的运动与高强度运动之间,人可能会选择前者,但在温和的疾病与身体健康之间,没人愿意再选择前者。我清楚地看到,学院的良好运行,同有序、通过的管理部门的良好运行一样,并非源自与其对立面的合作,而是源自对对立面的否定。雷克斯福德律法的字面之意与精神便是秩序、才智与光明,去除新坦慕尼之中的无序、无理、或黑暗。”
贾尔斯的建议或许才是真正的隐德莱希斯主义,即一方面是极致的中庸,所有行为都要在理性指导下寻找符合中道的那个平衡点;一方面又要在中庸之上秉持一种激进的极端,那就是某种人性的或以理念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底线——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没有这种底线,所谓的中庸就是抱薪救火,也会南辕北辙。
这是否就是巴思想要表达的意思?或者这难道也是一个不怀好意的反讽?因为,世界仿佛从来容不下一种动人的、彻底的理想主义,后者只有在拜伦的诗歌或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显露端倪,现实却是联合国秘书长紧紧握着侵略国外交部长的手,谈笑风生;被侵略国在侵略者的无人机中发现很多国家的零部件,那么多的国家或者购买石油,或者你来我往。仿佛——正义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巴思或许想要打碎这种以合理性面目呈现的现实性,以后现代的名义,以干脆用“羊性”来取代“人性”的名义,因为人性这个词早已失却了它的本义,堕落为一种幻觉、魔性、鬼性、兽性,成了非人性的代表——无疑,这也是一种巴思赋予我们的反讽。
从这个角度看,古典和后现代或许走到了一起,或许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就精神秩序这个维度而言,前者是清晰的、显明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盼望的;后者是混乱的甚至阴暗的,仿佛看不到一点微光的。但相同之处不言而喻,二者都承认人类理应捍卫、坚持、发展基于理性的精神秩序,文学和哲学的本义或许都在于——它是一种行动而非一种理念;它需要理念,但更需要行动。这就像巴思在前言中所说的话:
“那时(此刻依旧如此)我试图去做羊孩贾尔斯和我们每个人必须做的事情:在最深层次上理解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并且在这理解的基础上努力——以悲剧式的、喜剧式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去做点什么。”
评价: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