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大正在找路
其实,早在三四年前,就听当地朋友说,离我们不远的原始森林里有一座瀑布非常壮观,可惜没有路,当地的人去得也少,只有常年打猎和或者采山货的人去过……
这样说着,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每次都央求边大带我去看看,边大一听要去原始森林里就坚决否定了,理由是路况不好,后来又说,等zf修通了再去……后来就不了了之……
这几天之前预定好的客人临时有事取消,正好可以休整一下身体,今日,吃了早点,听边大和邻居闲聊起原始森林的事情、突然又想起那个神秘的瀑布 ,便怂恿大家去看瀑布,后来边大决定骑摩托车带我去看看。
这个果子叫热情果
摩托车沿着老乡做农活的小路进去,路况越来越差,我让边大前边探路,我从后面徒步前行。
路两边是茂密的森林,植物种类繁多,突兀地看见一朵两朵奇形怪状的鲜花,还有掉在路上的各种坚果,一些藤蔓从对面的树上探到这边,鲜红鲜红的果子……
走这条路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那种消散很多年的好奇心让你忍不住往前行进,那种小惊喜小意外时不时冲击你的想象。一群蝴蝶在花丛里飞舞,他们估计没有见过人类、所以也不懂的害怕,有的蝴蝶都大胆地落在你的衣角上,头发上,那种被小昆虫温柔以待的感觉特别幸福。
又走了几百米,突然听到流水的声音,由远及近,开始震耳欲聋……有点像见一个老朋友一样,于是加快了脚步,转过山角,空气里弥漫着水汽,声音更大了,紧走几步,眼前的崖壁上飞龙一样冲下来一条巨大的水柱,逢石炸裂开来,水花溅成了薄雾和浓烟,转瞬间又汇成了一条长河,在密林中时隐时现……站在这里,我以为会欢呼,却是巨大的沉默,是在大自然面前的没抓没拿的无助……
再往前走,我想离瀑布再近一些,世界仿佛被重新创造。
原先零散的流水声此刻汇成了天地间唯一的语言——那不是声音,而是某种液态的雷霆,是大地深处苏醒的呼吸。空气突然变得湿润而甘甜,每一口呼吸都像在饮用酿了千年的甘露。崖壁在这里豁然开裂,仿佛天神用巨斧劈开了一道通往异界的门扉。
不知名的果子
那条主瀑并非垂落,而是在飞翔。从百余米高的悬崖一跃而下,像是银河决堤,又似万千白龙挣脱了束缚。水流在坠落中遇石而炸,炸成亿万颗钻石,炸成弥漫的水雾,炸成升腾的云烟。阳光透过林隙斜照进来,那些水珠便折射出虹彩——不是一道,而是无数道虹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如同诸神遗落在人间的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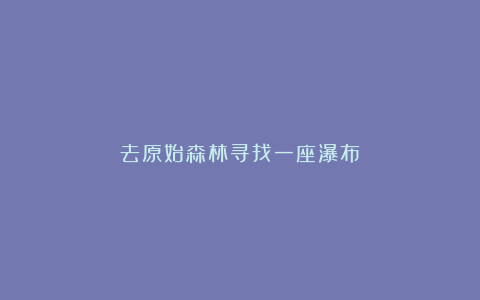
而更令人心悸的,是瀑布两侧岩壁上那些层层叠叠的小瀑群。它们从苔藓覆盖的岩缝中渗出,有的细如琴弦,有的宽如素绢,有的分成七八绺秀发般披散而下。这些支流与主瀑共同编织成了一张流动的网,一张由水和光、声音和时间织就的网。
看到瀑布
我忽然明白了刚才那阵沉默的来处——在这太过恢弘的造化面前,语言变得轻薄如蝉翼,欢呼则显得浅薄。就像你不会对星空鼓掌,不会对着初生的黎明喝彩。有些美,要求你以同样的深邃去回应。
崖壁上的苔藓厚得能埋进手掌,每一寸都蓄满了千年的水汽。蕨类植物在瀑水溅落的区域疯长,它们的叶片上挂着水珠,在幽光中像极了泪滴。而这些“泪”已经在流淌了千万年——从恐龙时代流到今天,从未干涸。想到这里,心头猛然一颤:我们何其短暂啊,短暂得像瀑水上瞬间破灭的一个泡沫。
瀑布边居然长着几树冬樱花,很粗的树干,枝条已经奴出嫩绿的叶片,再过一个两月,就是满树的鲜花,花树配着瀑布,那简直是美到窒息了。
边大在不远处的石头上坐下,掏出烟袋,却并不点燃。他只是望着瀑布出神,那张被山风雕刻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不是游客的惊叹,而是游子归家的安然。他或许早就懂得:瀑布的轰鸣不是噪音,而是大地的心跳。当你静静地听,听久了,自己的心跳便会与它同频。
我走近水潭边,伸手触碰那从崖上坠落了百米的流水。意料中的冰冷并未出现,反而有一种温存——是阳光穿过水层时留下的温度,还是这水流本身在漫长的坠落中与空气摩擦生出的暖意?就像某些苦难,在经历彻底的坠落之后,反而生出一种慈悲的温暖。
一亿年前的蕨类植物
当我们准备离开时,回望瀑布,忽然发现视角不同,景象已全然两样。原来真正的瀑布不是一个固定的画面,而是随着你的移动不断重组的光影戏剧。这多像真理——你永远只能看见它的一个侧面,当你以为把握了全貌,移动一步,又是全新的启示。
归途上,蝴蝶依旧在身旁飞舞,但我的心境已截然不同。那些进山时让我惊喜的野花、坚果、藤蔓,此刻都成了瀑布的延伸——它们本就是这巨大水汽滋养出的精灵。整片原始森林,不过是瀑布另一种形态的存在。
躺在地面上的花
忽然想起宋代画论中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这座瀑布却超越了所有这些范畴,它不可归类,只能体验;不可占有,只能融入。
摩托车发动的声音惊起了林中的鸟儿。我最后回望那片密林,瀑布已隐没不见,但它的轰鸣还在胸腔里震荡。或许这就是朝圣的意义——不是你到达了圣地,而是圣地随你回到了尘世。往后的日子,我只需闭上眼,便能回到这片瀑声如雷的森林,让那永远在坠落也永远在升腾的水流,洗净我那被圈养太久的灵魂,暗暗告诉自己:慢点,慢点,不必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