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涟文化,致力繁荣!
第二届老舍文学创新奖全国文学作品大赛
青铜与白鸽
城中心的广场,晨雾裹着香樟树的潮气,在石板缝里慢慢渗。老张把鸟笼挂在树杈上,笼门敞着,绣眼鸟蹦跶着叫,声儿碎得像筛子里漏下的小米,一粒一粒坠在雾里。孩子们踩着滑板车碾过喷泉的水洼,水花溅在纪念碑基座上,洇出的湿印子慢慢晕开,像谁在青铜浮雕的衣角上,悄悄洇了滴泪。那些扛枪的人影,让八十年的风磨得光润,衣角褶皱里藏着的,许是1945年深秋的凉意,摸上去,指尖还能沾着点棉布的糙。
夜里翻祖父的旧物,蓝布棉袄的口袋深处,滚出枚证章。绿漆掉了大半,”抗战胜利纪念”六个字却筋骨分明,边角让手磨得滑溜,像祖父揣了半辈子的铜钥匙——他总说这是民国三十四年换的,用半袋糙米,换给那独腿的兵。”你年轻,能活到好日子。”兵的声音像漏风的窗,祖父每次摸这证章,拇指总在”胜利”二字上蹭,蹭得绿漆褪成浅黄,露出底下的铜色,倒像块老铜锁,锁着些说不出的沉。
棉袄里还裹着半张油印传单。字是刻在蜡纸上的,笔画边缘让手指磨得发毛,”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几个字,让不同时期的汗渍晕出三层印子——浅黄的是1938年秋夜的,防空洞油灯熏的;淡紫的是1940年冬的,雪地里揣在怀里焐的;最浅的那层,泛着点灰,许是1943年蹲在战壕里,就着炮火把烟蒂按在上面烫的。
他总爱摩挲传单右下角,那里有个月牙形的折痕,是反复揣进掏出磨出来的。”刚见着这纸那会儿,”他抽着旱烟,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以为再熬个年把就能回家。后来在山里打游击,见着这折痕磨得发亮了,倒慢慢懂了——路得一步一步走,像田埂上的脚印,深一个浅一个,总能踩到地头。”传单边角卷着,像片经了三季的叶子,叶脉里藏着风的形状,却半句没提过”阶段”二字。
上海四行仓库的西墙,弹孔密得能漏下阳光。有回站在墙根,看光从孔里筛下来,在地上铺些碎斑,像谁把铜扣子撒了一地。讲解员说1937年深秋,陈树生捆着手榴弹往下跳时,军装后襟让风掀起个角,像断线的风筝——现在墙根种着虞美人,红得透亮,风过,花影在弹孔上晃,倒像那些枪眼在眨,眨掉了八十年的尘。
有回见个老兵,用拐杖头把游客折的纸船往弹孔深处捅,”那会儿谢团长给我们讲这墙的意思,”他喉咙里像卡着痰,”说这仓库就是块礁石,浪再大,也得钉在这儿。浪头一回比一回猛,可礁石上的缝,倒成了透风的窗。”虞美人开花时,花瓣落进弹孔,像给那些透风的窗,挂了层软帘子。
去年冬在长春见王景芳老人,九十二岁,右手缺俩指头,是山里打游击冻掉的。”那时候冷啊,”他往手心里哈气,白气刚冒就散了,”杨靖宇将军靠在树桩上,肚子里只有树皮草根。鬼子剖开他的肚子,都愣了——他们不懂,那不是饿的,是揣着整个东北的山呢。”老人从怀里摸出块帕子,包着半块旧怀表,表盖裂了道斜纹,”表针停在凌晨三点,天快亮的时候。”
怀表旁压着张泛黄的报纸,上面印着《论持久战》的节选,有几处用蓝墨水画了波浪线。老人说那年冬天,在雪地里把报纸裹在棉袄里,字都印在了皮肤上,”就像给骨头里注了铁,冻掉手指也不觉得疼。”怀表的滴答声,和当年雪地里的脚步声,倒像是合着一个拍子。
滇西抗战纪念馆的库房里,摆着双草鞋。草绳黄得发脆,鞋底却纳了三层麻布,针脚歪歪扭扭,像山路上的脚印。是民工李顺才的,1942年修滇缅公路时让落石砸了。他口袋里有个布老虎,耳朵用红线缝了又缝,线脚松松垮垮的。讲解员说,他离家时闺女才三岁,总拽着衣角问:”爹,路通了,能捎朵山茶花不?”那布老虎的耳朵,真像两瓣没开的花苞,还沾着点滇西的土。
草鞋旁曾躺着本翻烂的小册子,民工们轮着看,有人用炭笔在空白处画箭头,从山这边指到山那边,像在乱石滩上踩出条路。那只布老虎的肚子里,藏着片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众人拾柴”,字迹让汗浸湿了,却还能看出是个孩子的笔迹,大概是李顺才的闺女,照着大人的样子描的。
卢沟桥的石狮子,让游人摸得发亮。卖冰棍的周大爷掀开竹篮上的蓝布,绿豆冰棍冒的白气,缠在狮子爪子上。”那会儿躲防空洞,”他用袖子擦冰棍纸,纸角卷了边,”听着飞机在头顶嗡嗡,哪敢抬头?”竹篮底下压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举着本卷边的书,背景里的卢沟桥,石狮子的眼睛亮得像星。”后来有学生在桥上念,说熬着熬着,天就亮了。”风过,风筝尾巴扫过狮子的脸,像在挠痒。
晋察冀边区的小庙里,白求恩大夫的手术刀还在。铜柄上的漆掉了,露出黄澄澄的铜色,刀刃却亮,能照见人影子。1939年秋,他在这儿连做六十九个钟头手术,最后那台,手指让碎骨刺了下,发着烧还说:”再做一个。”后来这刀传给了土郎中,郎中的孙子现在是县医院外科医生,总说:”白大夫的刀,沾着救人心。”
手术刀旁摆着本译稿,纸页上有他用钢笔写的批注,英文夹着中文,”这仗,得在手术台上一寸寸赢。”刀柄上的指痕,深浅正好合着三代人的手。
1941年的北平,林迈可揣着药包往城外走。英国人,给山里送电台零件,遇着李效黎姑娘帮他翻译药瓶上的字。后来两人逃出北平时,李效黎怀里揣着只纸鸽子,学生们说:”等熬出头,让它往家飞。”林迈可的笔记本上,除了电路图,还画着两只鸽子,翅膀张得大大的,翅尖沾着太行山的灰,旁边写着”人多,路就长”。
驼峰航线的云,白得跟当年一个样。老人们说,那会儿中美飞行员驾着飞机在雪山缝里钻,云层厚得像棉花垛,底下是万丈深谷。天上过一百架飞机,总有一架落进山谷,第二年那地方就多丛杜鹃花。有个美国飞行员的日记里写:”战友的飞机掉下去,像片叶子飘进山谷,第二年,那儿就开了花。”
日记里夹着片青稞叶,上面写着”一朵一朵开,路就通了”。现在山里头,雨夜里还有人说听见引擎响,”是找不着路的飞机,往亮处飞呢。”
南洋机工陈永锡的日记,纸黄得像秋叶。上面画着椰子树,树干歪歪的,像他老家门口那棵。”等把卡车开到重庆,”他写,”就摘片椰子叶寄给阿妈。”日记到1943年春就停了,最后一页画着山茶花,旁边字儿歪歪扭扭:”像阿妹头上的花。”滇缅公路旁的坟,一千多座,都朝着南边,朝着椰子树的方向,坟头的草,每年春天都往南倒。
幼儿园放学,老师教折白鸽。小闺女举着纸鸽子跑过来,翅膀上的金粉在夕阳里闪,像撒了把星星。”老师说,”她仰着小脸,鼻尖沾着点金粉,”把想对爷爷说的话,写在翅膀上。”
广场上的白鸽起了群,翅膀扫过纪念碑的顶。碑上的青铜人影,像是松了松手里的枪,接住飘落的羽毛。卖烤红薯的老张,炭火烧得匀,红薯皮焦焦的,掰开来,瓤子是蜜色的,白气裹着甜香,漫到纪念碑根下,漫过那些青铜的手指。
祖父的证章,我用红布包了,放在抽屉最里头。夜里偶尔摸出来,铜片轻轻响,像谁在耳边叹:”你看这日子,多暖。”那半张传单压在证章底下,月牙形的折痕还在,像个浅浅的笑。
创作手记:写《青铜与白鸽》的时,心里总装着个念头:历史不该是博物馆里的玻璃柜,得让它走出来,在香樟树的影子里、烤红薯的热气里,跟现在的日子撞个满怀。
一、让理论“脱下西装”——关于《论持久战》的“生活化翻译”
最初想写进《论持久战》时,总怕写成“理论宣讲”。后来读董桥谈“老物件”,他说“铜器上的指痕比铭文更见心肠”,忽然明白:理论要落地,得先给它找件“家常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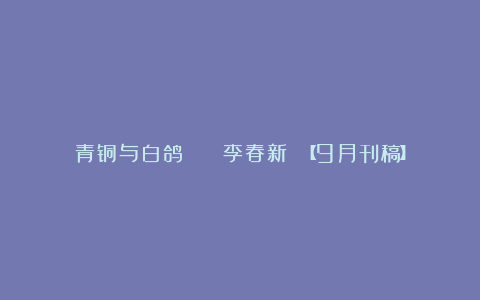
祖父的那半张传单,最初写了“三个阶段像爬三座山”,读着像教科书,赶紧删了。换成“三层汗渍”——浅黄是防空洞的油灯熏的,淡紫是雪地里焐的,泛灰是战壕里烟蒂烫的。这三层印子,其实就是“防御、相持、反攻”的另一种写法:1938年的“以为熬个年把就好”,是最初的懵懂;1940年的“揣在怀里焐”,是相持阶段的韧性;1943年的“烟蒂烫”,是快见亮时的焦灼。不用“阶段”二字,可田埂上的脚印“深一个浅一个”,谁都能懂那是“一步一步走”的意思。
四行仓库的老兵不说“战略防御”,只说“仓库是礁石,浪再大也得钉在这儿”。礁石的“硬”,浪的“猛”,弹孔成了“透风的窗”,这些比任何术语都更能让人摸到“持久战”的肌理。理论一旦穿上“礁石、脚印、汗渍”的衣裳,就从书架上走下来,成了能蹭到袖口的温度。
二、让时间“打个结”——关于过去与现在的“呼吸交缠”
蒋方丹写时间,总爱让“过去”和“现在”在同一个物件上“挤一挤”。卢沟桥的石狮子就是个好例子:1943年学生在桥上念“熬着熬着天就亮了”,现在风筝尾巴扫过它的脸“像在挠痒”。狮子还是那只,可它的耳朵里,既藏着防空洞的嗡鸣,也藏着孩子的笑。
修改时特意给每个历史场景加个“现在的注脚”:四行仓库的弹孔里,既有1937年陈树生的风筝般的后襟,也有现在虞美人的花瓣“挂了层软帘子”;白求恩的手术刀,铜柄上的指痕“合着三代人的手”——他的,土郎中的,现在外科医生的。时间不是铁轨,是老布上的补丁,新的旧的摞在一起,才暖和。
驼峰航线的杜鹃花是个意外之笔。最初只写“飞机掉下去”,后来想起老人说“第二年开了花”,忽然觉得这就是时间的打结处:1942年的坠落,2025年的绽放,痛与暖在土里长在了一起。不用写“牺牲的意义”,花会替你说。
三、让情感“藏在指缝里”——关于“不说”的力量
周晓风的文字里,最沉的情感总藏在最轻的动作里。写王景芳老人,最初想写“他坚信持久战必胜”,太硬了。换成“把报纸裹在棉袄里,字都印在了皮肤上”,再补一句“像给骨头里注了铁”。骨头里的铁,比嘴里的“坚信”重多了。
陈永锡的日记停在“像阿妹头上的花”,不写他怎么牺牲的。滇缅公路旁的坟“都朝着南边”,坟头草“每年春天都往南倒”,不说“思乡”,可草的朝向比眼泪更执拗。老兵用拐杖头把纸船捅进弹孔,不是“纪念”,是“给没打完的仗找个去处”——这些动作比口号安静,却像往水里扔石头,涟漪能荡很远。
连《论持久战》里的“兵民是胜利之本”,也换成了林迈可笔记本上的“人多,路就长”。人多了,路自然长,长到能把持久战的“久”,走成具体的脚印。
四、让青铜与白鸽“抱在一起”
最初写青铜纪念碑,总觉得它是冷的;写白鸽,又觉得太飘。后来发现,得让它们在同一个场景里“呼吸”。
广场上的白鸽掠过纪念碑,青铜人影“接住飘落的羽毛”——硬的历史接住了软的和平。烤红薯的甜香“漫过青铜的手指”,烟火气裹着历史的棱角,就不扎人了。祖父的证章和传单压在抽屉里,铜响和折痕的“浅浅的笑”呼应——八十年前的挣扎,和现在的暖,终于在同一个抽屉里和解了。
说到底,这篇文字想写的不是“历史”,是“历史如何变成现在”。就像那半张传单上的汗渍,晕开了八十年,最终成了现在日子里的甜。读者读到的,不该是教科书上的铅字,该是香樟树下的鸟叫、孩子指尖的金粉,还有自己爷爷抽屉里,那枚说不清来历的旧铜片——原来,我们都在历史的褶皱里,彼此相认。
【编后荐评】
李春新的《青铜与白鸽》以细腻笔触串联起抗战记忆与当下生活,让历史在烟火气中焕发生机。文章聚焦证章、传单、草鞋等老物件,通过祖父的摩挲、老兵的讲述,将《论持久战》的宏大理论化为“三层汗渍”“田埂脚印”等具象细节,让历史走出博物馆,成为可触摸的温度。作者巧妙勾连过去与现在:四行仓库的弹孔盛着虞美人花瓣,白求恩的手术刀映着三代医者的指痕,青铜纪念碑接住白鸽羽毛。全文情感藏于细节,坟头草朝南、布老虎沾滇西土,不言思乡却字字含情。最终,烤红薯甜香漫过青铜手指,让历史与和平在烟火中相拥,读来厚重而温暖。
作品与知音优雅相会 佳作与美刊相映生辉
当代文学家·顾问阵容
厚名家亦厚新人 重当代更重未来
总编:清涟一荷
全国文学作品创新大赛
征稿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