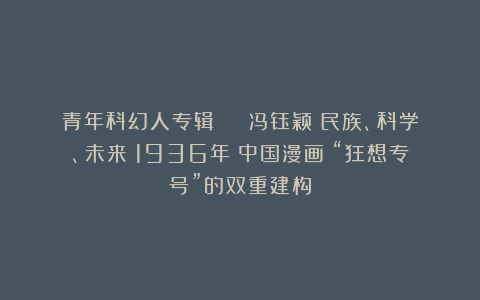四十二史
民族、科学、未来:1936年《中国漫画》“狂想专号”的双重建构
冯钰颖 / 文
冯钰颖(1997—),女,山西太原人,中国美术学院文创设计制造业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科幻人文》青年编委。当前研究领域为设计史、设计文化与技术美学。
1936年12月14日,《申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朱金楼主编,第十一期出版,狂想专号下编,科学特辑。包罗宇宙万象、展列星球伟观、掘发科学异迹、强调机械万能、未来派的珍奇、未来派的神秘。(附绥战漫画十余幅)健儿的抗战,前线的胜利。全书四十余页,单色漫画九十余幅,彩色漫画十余幅,富于刺激性的文字多篇,内容丰富,取材严格,编排新颖,印刷精良,墨色美观,并附绥战漫画十余幅。每册二角,预定全年二元。中国漫画出版社,上海武定路祥兴里三号。中国杂志公司总代发行。1
这则广告宣传的是《中国漫画》第11期。1937年新年前夕,由朱金楼创刊并担任主编的《中国漫画》出版上、中、下三编“狂想专号”,对应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第9期,同年11月5日出版的第10期,以及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11期。此后,《中国漫画》又出版了三期,便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被迫停刊。2
《中国漫画》第十一期封面
这三期“狂想专号”对于《中国漫画》而言意义非凡。《中国漫画》在《申报》上一共宣传过14次,其中尤以“狂想专号”宣传力度最大,它们肩负的使命是:以全国漫画家最奔放的个性,作整个漫画坛前最威武行列;无所顾忌的热烈的夸张、如火如荼的疯狂的表演、强化漫画艺术的特性、力迸出漫画艺术的光辉。3中编不仅在《申报》上宣传,4在《大公报》上也做广告,5这是《中国漫画》唯一一次在《大公报》上宣传。下编则在《申报》上连续宣传过两次。而且,《中国漫画》自1935年创刊至1937年停刊,共出版14期,其中以“专号”为名出版的只有“狂想专号”三期杂志。
朱金楼在中编的《编者之话》中写道:“’狂想专号’一来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再来作者与编者的狂兴未尽,所以本来出上下两编的,现在预备上中下三编了!”上下两编出版后,他希望第三编“狂想专号”聚焦科学。在文末,他向投稿作者提出要求:
下期的“狂想专号”下编,想请作者们多来些科学性的狂想稿,有些题材该是很有趣味的,如:“火星里的狂想”,“月球探险”,“宇宙海岳变迁”,“无线电时代”,“真空世界”,“未来的新兵器”,“百年后都市访问记”,“未来的机械与生活”,“人种改造”之类,不过很难讨好,应当多找几本英文或日本版的科学杂志或画报来做参考!6
本研究旨在探究《中国漫画》“狂想专号”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以及三编漫画所构造出的科学世界。李广益曾在《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一文中呼吁“左图右史”辅助中国科幻史研究,并将“狂想专号”科学特辑封面作为文章插图。7愿本研究能为之做出微薄的贡献。
一、战争焦虑与民族主义:
“狂想专号”的历史语境
1932年1月28日夜,上海事变爆发。次日凌晨,日军战机轰炸闸北区,中日双方展开长达三月余的交战。当警报在耳边轰鸣,炸弹向每日必经的道路投去,朝夕相处的邻人被扣押、虐待、杀害,8上海市民的恐慌与怨恨疯长。国民政府对日军侵略国土、羞辱国民的行径所采取的绥靖态度令人们失望,其残杀同胞、镇压舆论的行为更点燃人们的怒火。
同年3月,伪满政府宣告成立;1935年冬,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来自远方的消息同样悲哀,才始被文人比作母亲的“中国”似乎正不可避免地衰弱下去。国际政治的风云莫测如同一种预言:中日双方即将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于是,对沦为“友邻”庞大殖民地的担忧,成为1936年中国社会普遍性焦虑的最主要来源。
种种有关沉沦和死亡的想象啮噬着中国人,唯有一场澎湃的胜利才能挽救这消沉的意志。可惜,就连1936年的夏季奥运会也以惨败收场,再加上四川、重庆的严重旱灾和政府的“旱荒祈雨”活动……民众怨声载道,国民政府却充耳不闻,一面继续维护“中日亲善”方针,一面为蒋介石筹备五十大寿,向各界征集飞机,美名之“献机祝寿”。
时事无望。1936年,民众间积聚的焦虑、愤怒与哀恸已遮天蔽日,急需一场狂恣的宣泄。此时主流报纸受到严苛的舆论管控,于是《中国漫画》“狂想专号”以一场狂欢的面目现身,将上述事件编入其中。上编封底漫画配文:若干年后,为与友邦表示“亲善”起见,中秋节赏日不赏月,烈炎蒸腾,汗下如雨,民弗敢怨!9中编,俞创硕的《新镜花缘——救灾与航空救国》一文,戏仿李汝珍《镜花缘》,讲述林之洋、唐敖、多九公来到“东口”荒地,九公折下名为“祝余”的青草,称“吃此一枝,可以疗饥”,林之洋吃了,马上说要多带些回去,省得大旱荒吃树皮的时候,在这科学世界,再请什么班禅喇嘛祈雨做法事贻笑外邦了。一会儿,唐敖又折一枝“蹑空草”,吃了能立空中,林之洋拍手笑:现在中国不是正在提倡航空救国吗?一二八吃过矮脚鬼的亏,都说咱们的兵不是不会打仗,乃是断少了飞机,假使中国人都吃了“蹑空草”,不是个个都可成为空军战士了吗?唐敖闻之,又指出另一种用途:这几月来国内不是正在忙着献机祝寿吗?上海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捐到十架飞机,提议将蹑空草做寿礼。(图1)10
图 1 《新镜花缘——救灾与航空救国》
以上两例以过去或未来的时态叙事,表现的却是现实中的事件。在这另辟的时空里,民众间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得以释放。这是《中国漫画》“狂想专号”成立的条件。同1930年代整体以上海为中心的漫画创作潮流一致,《中国漫画》是一份以讽刺漫画(caricature)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杂志,叙事尖锐而幽默。11 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在其著作《以图证史》中解析讽刺漫画的社会功能。他认为,在报纸发明之后和电视发明之前,讽刺漫画在政治辩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撕掉了权力的神秘色彩,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国家事务。它们承担的任务是用简单、具体而引人注目的方法提出有争论的问题。12在舆论管控的年代,“狂想专号”因其冠以“狂”的名义而不必被追责,讽刺漫画家因善用转喻和讽喻的修辞而在审查制度之外拓出一个新的空间,最终达到对社会暗层作严肃的暴露、对敌人汉奸作勇猛的刺激、给政治动态以大胆的判词、给民族集团以激励的教育的效果。13
其中,对民族主义观念的渲染是“狂想专号”得以连出三编的潜在因素。作为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的回应,中国抵抗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迅速成长,并成为绝对正确的立场。在当时的情境中,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含义几乎一致。这样的意识形态和对现实的焦虑与战争的恐惧缠结,促使中国的各种文化实践超越西方印刷资本主义模式,成为独特的、创造性的实践。14漫画是这些文化实践中颇具想象力的一支。不同于西方讽刺漫画,中国的漫画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之所在,恰是它对民族主义和国家共同体的强调。在当时,漫画被认为应为国家服务,而界定漫画优劣的标准则是评判其是否能够调动起人们的爱国情感。如当时的漫画家黄文农认为,漫画的力量,在弥补人生的缺憾,引起大众的共鸣,为激发民族精神之唯一利器。15在“狂想专号”下编《今后的本刊》中,朱金楼表达了相似的立场:编者个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本刊的内容是以民族主义为其基底的。16“狂想专号”的民族主义立场为之确保读者群的广大和坚实,而其所表现出的近乎疯狂的民族主义情感,比理智的民族主义论述更具感染力。
在1936年压抑的社会气氛下,人们几近发“狂”。作者与读者积压已久的民族愤恨,借由夸张、幽默、戏谑的表达得以释放。在“狂想专号”的“狂欢”中,全国各地的作者想象着在战争中我军气盛而胆张,敌方魂飞而胆碎,最终东方睡狮,负创而起;17或赋予奥运健儿以超能力,让杨秀琼奋力攫住潜水鱼雷艇、褚民谊太极气功吹散毒瓦斯,终于洗雪一九三六年国耻,“十五年体育计划”成功,敌民倾倒脚下(图2)。18这些图文表现因自冠以“狂”的名义,而不必考虑想象被实现的可能。这是一种几乎没有边界的想象。它们是中日战争前夜知识阶层对积郁的愤懑的倾泻,也是民族主义观念空前高涨的社会情境的再现。不过,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实是此番狂想中有关科学话语的表达。
图 2 《雪耻救国记》
二、一种“科学”,两种想象:
当“狂想专号”遭遇、晚清“科幻奇谭”
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以恰当的概念来指代晚清民国有科幻旨趣的小说向来存在争议。若以“科学幻想”来指代这一文类,难免有“发明传统”的嫌疑。而若沿用晚清民国的分类标准,称其为“科学小说”,则难回避僵硬的分类体系束缚灵活的文本演绎的问题。19王德威没有采用上述两个概念,而是将这类小说归纳为“science fantasy”,认为这一文类更具混杂性,以此与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作区分;宋伟杰译之为“科幻奇谭”,并将原文中涌现的“fantasy”一词译作“狂想”。20将这类文本命名为“科幻奇谭”,究其根本,是因为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似乎与真实的科学知识关联甚少。冯鸽认为,这种关联的匮乏根源于当时中国科学事业的欠发达,其结果便是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主要特征显现为“狂想性”,因此这类小说更应该被称作“科学狂想”。21
1936年《中国漫画》“狂想专号”的作者与晚清科幻小说家想象科学的方式呈现出相似的“狂想性”。吴岩以“词汇暴接”概括晚清科幻小说中最典型的表现方法,即将科学术语和其他词汇拼接为新名词,典型的例子便是《新纪元》中的“海战知觉器”。22“狂想专号”中也有类似的发明,如“验心光”23“科学着衣器”24“光力车”。吴岩认为,这类词汇之所以出现在晚清“科幻奇谭”中,是因为这时的科幻小说最主要的想象模式是“书写愿望”,此时作家“科学素养不足”,对科幻作品的理解尚浅,无力写作有着充分逻辑推演和准确科学知识的科幻小说。25因此,这些作品便如陈平原所说的那样,除了若干从大众传媒获得的西学术语外,不得不借用若干武侠小说及神怪小说的伎俩。26“狂想专号”中的新器物也服务于以神怪小说为底色的叙事:在艾中信设想的宇宙里,“光力车”以光的速度在不同的星球间穿梭,游客可前往月宫饭店观看嫦娥舞蹈。27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狂想专号”下编中黄尧所作的《当中国科学最发达的一天》,配文:“战争不用枪炮,死光、毒瓦斯也无用了,我国可放’法宝’,尤以混元金斗最为利害”28。把明代《封神演义》中能收束万物的法器当作超越“死光”“毒瓦斯”的武器,无疑是一种戏谑的表现手法。然而,这种将现代科学术语和中国志怪小说中的语词并置的做法却让它和晚清“科幻奇谭”形成了一次时空错置的对话。
不同于晚清“科幻奇谭”,1936年于上海出版的《中国漫画》“狂想专号”在表现科学时所展现出的“狂想性”是有意为之。如果说晚清科学事业的“不发达”是导致“科幻奇谭”具有“狂想性”的可能原因,那么,若在讨论1936年的科学想象时仍沿用这一因果推论,则无疑忽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为科学事业付出的努力。况且,1936年的上海,绝非贫瘠滞后之地。李欧梵在《上海摩登》开篇引述的那段《子夜》,已足可证明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的物质现代性。29《中国漫画》的编者和作者多为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阶层,他们不但熟悉现代生活中的种种新技术、新器物,也对科学知识有着高于晚清科学小说家的认识。至于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读物,除了用中文写就的科学小说外,还要加上用中文翻译的西方科幻小说。威尔斯(H.G.Wells)于1933年出版的《未来世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次年就翻译为中文出版。30“狂想专号”上编中的《外国刘伯温:威尔斯在“未来世界”里所描写的——“中X大战”狂想》一文,31便是这部著作中有关中日战争部分的译文。32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的西语著述。如下编中朱金楼的《海底狂想》便选译自1910年的博物学著作《寰宇奇观录》(Marvels of the Universe)。33
这一创作环境恰恰也是民国科幻小说的土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重要的出版业中心,更是小说家想象未来的灵感源泉。1923年,顾均正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5年,包天笑发表《新上海》,徐卓呆发表《明日之上海》。这座被村松梢风称为“魔都”的城市,不但孕育着“鸳鸯蝴蝶派”的未来绮想,也滋养着以科学普及为志业者的文学创作。任冬梅曾比较晚清与民国科幻小说中的上海书写,由此引出科学想象自晚清至民国从“光明”向“灰暗”的转变,指出民国科幻小说在想象未来时往往从失望而忧愤的现实生活出发,并在文中透露出许多不满、无奈、矛盾与挣扎。34《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进一步总结了民国科幻小说不同于晚清“科幻奇谭”的特点:一,文本笼罩着国际大战的阴影;二,文中弥漫着悲观与绝望的态度,作者借由科学想象讽刺、批判现实;三、“科学”的消极后果和“邪恶”科学家的形象在文中有所表现;四、文中出现“通俗”“流行”元素;五、科幻与科普纠缠不清。35此外,科学知识的积累与科学观念的传播为这一时期的科学想象带来了新的素材。36
《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
相同的创作环境使得“狂想专号”与民国科幻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相同的特点,例如,下编中由穆忠良所作的《科学战争后之地球》,讲述“科学到了极发达之后,各地的战争亦更残酷。结果地球受不了过分的强烈的震动,而宣告破裂”的故事。地球破裂后,共产主义者跃入水星,法西斯主义者逃往金星,“倭鬼帝国”迁往火星,“素以中庸之道著称”者避入月宫,只有“黑人科学进步最迟”,留在破碎的地球上。37这则故事以科学的发达将导致地球的衰亡为前提,隐含着民国科幻小说中普遍存在的悲观和战争焦虑。但是,有关“月宫”的表述,以及“黑人”被迫留在地球上的情节所传达出的文明等级观,又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晚清“科幻奇谭”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又如,在下编由沈冠芬所作的漫画中,“科学”的未来与“科学家”的工作都变得可疑:不久科学将分两派:一派潜心研究杀人利器,一派绞尽脑汁,使死人复活,致将人类弄得不死不活,叫苦连天!38只不过,在“狂想专号”所构筑的漫画世界里,如何以科学的方式复活死人,又应以何种技术制造武器,这类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在此意义上,晚清“科幻奇谭”和“狂想专号”走向了同一种“科学”。它们都缺乏量化分析和标准化的概念、理论阐释,缺乏数理逻辑的推演,缺乏以实证立论的抽象理论。
因此,“狂想专号”的叙事同时具备民国科幻小说和晚清“科幻奇谭”的特点。尽管晚清“科幻奇谭”和“狂想专号”的作者以同一种不合理的“科学”展开想象,但不同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的科学想象判然有别,这种差别恰是民国科幻小说不同于晚清“科幻奇谭”的特征。可以说,“狂想专号”的作者是以民国科幻小说家的方式想象着晚清“科幻奇谭”所言说的那种不真实的“科学”。在此过程中,“科学万能”的话语被讽刺的修辞消解,科学及其技术化应用不再是胜战的法宝或文明的标尺,而被视为战祸的共谋和社会问题的来源。
三、“科学万能”的陨落与“未来派”的悲思:“狂想专号”科学特辑的双重建构
不同的科学语境造就不同的科学狂想。自19世纪末严复提出“西学格致救国”以来,经维新派的反复言说与大众媒体的传播,20世纪初,“格致强国”转换为“科学万能”。39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主义观念,世纪之交的“科学万能论”隐含着民族救亡的主题。西方科幻小说家因所见科学和技术的蓬勃朝气而起想象,究其根本,是因为西人那时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已上升为一种信仰。与之不同,晚清“科幻奇谭”为“遐想新的政治愿景和国族神话”而构造的那个“充斥着难以想象的机器人、魔术师、飞天气球、潜水艇、空中飞行器、导弹与太空船”的世界,40发自“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爱国主义,服务于“欲新政治”的兴国愿景。41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成立,次年始发《科学》月刊,与之同年出版的有由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此时,汪晖所言的“科学话语共同体”正在形成。42这一时期,大量科学技术期刊创刊,新兴的科学媒体和科学主义者团体共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构造出一个科学话语的新世界。在汪晖看来,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敬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中产生的。43与一战前后欧洲知识分子对科学和理性的质疑形成对照,中国思想家对战争的首要反应是建立科学团体、创办科学刊物,为科学的合法性辩护。44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使命的科学话语共同体在此背景下形成,由它促动的各种活动使得原先服务于政治愿景的“科学万能论”悄然变换为压倒一切的“科学世界观”。45
《科学》月刊
并非无人怀疑这名为“科学”的教条:梁启超在其1919年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中否定“科学万能”;46同年,杨杏佛在《科学》月刊发表《非“科学万能”》,称科学“未必万能”。47这份对“科学万能”的质疑因1923年科学话语共同体就“科学与人生观”展开的论战而达到高。论战肇始于张君劢以“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为要旨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他的观点使其迅速被科学主义的拥趸贬称为“玄学鬼”。然而,一方面,这些科学主义的反对者仅以“科学不能万能”立论,无意批判科学技术为社会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48另一方面,在这场论战中,由“科学派”塑造的“话语氛围”使其反对者也不得不折服,对立双方同时进入“科学的话语帝国”。49于是,科学主义的观念在论战后的几十年间继续增长。50
汪晖认为,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世界观在中国社会确立其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1923年“科玄论战”激起的水花非但没有动摇科学的话语霸权,恰恰相反,在此后道德、审美、情感等范畴被纳入科学化的知识分类体系的过程中,科学的霸权地位得以强化。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局势也未能让那些反思科学霸权及其技术运用的思想成为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51汪晖的论述重点在于两次世界大战间以救亡图存为志业的精英的科学世界观,而这种观念在民间并未受到热烈欢迎。作为一种大众媒体,漫画更多迎合的是普通人的趣味。“狂想专号”科学特辑反映出此时人们对科学至少产生了三个层面的质疑。
其一,一个高度科学化的世界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同时是一个战火不断的世界,这战火甚至蔓延到宇宙,梁永雄的漫画《第一次宇宙大战》配有如下文字:
一九四零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球由希特勒大王所统一。以一片焦土,无从建立地球王国,乃拍电给火星生物,要求实行亲善提携,共存共荣。电发后希陛下即令科学家将地球控制,驶近火星,讵火星生物冥顽不灵,亦控制火星逸出轨道逃走,希陛下极为震怒,命令控制太阳将火星焚毁,讵火星竟又控制另一太阳系之太阳回向周旋,鏖战甚烈,宇宙各天体无不受其影响,纷纷联成战线,相与抗衡,于是酿成第一次宇宙大战。52
应当注意,这则荒诞的政治想象描绘新世界秩序的方式已不同于晚清“科幻奇谭”。在《新纪元》《电世界》所表现的世界秩序中,中国是最强势的国家。53与之不同,在《第一次宇宙大战》的世界里,法西斯主义者大获全胜,代价则是地球变为“一片焦土”。为了建立新的帝国,希特勒首先命令科学家控制地球,接近火星,要求与火星生物“共存共荣”。不料火星生物竟拒绝接受法西斯主义者的殖民统治,于是希特勒又命令科学家控制太阳,焚毁火星。引发“宇宙大战”的两次行动均由科学家主导,在这里,科学被视为战争的同谋。
其二,人们反思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人的观念的改造。狂想家们不再热衷于借助科学来想象民族崛起,而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科学与技术投去更多的目光。在艾中信想象的“科学世界”里,只见一个人咒骂他的表太不准,因为与标准钟相差千分之一秒。他流出满头大汗,但是当他未看见寒暑表达到一百度时,不敢确定气候之热。54漫画家质问:当实证主义渗透日常生活,当客观性的法条取消了感觉的意义,人和机器的差别何在?
其三,“科学万能论”被质疑,人机关系得到思考。徐本大在《科学着衣器》中设想了机器坏掉的结果,科学愈发达,人类愈偷懒,于是有科学着衣器发明。有钱的绅士们裸体爬进机器,机器会替他着好衣裳出来。一旦机器损坏,则马褂着在脚上,裤子套在头上出来,大失尊严。55在另一组漫画《科学机器人》中,徐本大想象未来“万能机器人”夺走人的劳动机会的情形:商店全用机器人当职员,社会上失业人将更多。56与“科玄论战”中“科学不能万能”的论调不同,徐本大是在对“科学万能”的未来的设想之上,讽刺“科学万能”的世界的荒诞性。
从“格致强国”到“科学万能”,再到胡适所言的“科学的人生观”,57科学主义的观念逐渐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战争愈迫近,民间的怀疑、焦虑愈甚,科学与技术愈被视为现代战争的共谋。尽管科学在现代观念中的正统地位从未被真正撼动,但是,“狂想专号”科学特辑对科学话语的建构实践为重新审视科学主义提供了契机。
此外,我们不应忽略《中国漫画》的图像媒介属性。“狂想专号”科学特辑的另一建构方向集中表现为视觉性实践。“狂想专号”中的许多作者都来自艺术院校,这些作者所掌握的艺术知识应比科学知识更多。当朱金楼为登载《申报》的“狂想专号”科学特辑广告写下“未来派的珍奇、未来派的神秘”时,他所言的“未来派”是否和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的“未来主义”(Futurismo)含义一致?
20世纪30年代,有关未来主义的美术知识已被转译到中国。这种转译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不同于意大利未来主义的激进立场,58中国现代美术批评家倾向于从方法论的角度归纳未来主义绘画表现中的运动感,认为这一画派的表现手段有“瞬时性”“同时性”“同存性”三个特点。59“狂想专号”中的彩页漫画有意调用“未来派”的表现形式:汪子美在中编封面漫画《死光时代》(图3)中描绘作为武器的“死光”遍布世界,“使整个地球的生机归于死亡”的图景。图中经受死光炙烤的人物是“战神”,在这神秘粒子束的照耀下,他手中的匕首也被融化。围绕着战神的是坠落的飞机、热气球、导弹,以及枯死的植物。死光之下,一切金属制成的排烟管、无线电塔、坦克都被“消灭”。种种工业、战争、未来的象征物共存于一个二维平面,作者用弯曲的匕首和排烟管表现死光之下铁器的动势,这些视觉语言已具备“未来派”的表现特征。60
与《死光时代》相似,中编当中由朱金楼绘制的《未来之惊怖》(图4)也通过描绘弯曲的钢铁来传达末世感。这张漫画更加接近意大利未来主义绘画的形式语言:飞机、飞艇、巨炮、坦克、飞船等现代工业的“杰作”都涌向构图中心,几乎没有留白;右下角的坦克和上方的飞机有不同的水平线,表明它们处于两个时空。这一构图方式表现出“未来派”绘画所强调的“同时性”和“同存性”。背景中象征着“死声”“怪力线”的折线、曲线,以及前景中因炮弹发射聚积能量而弯曲的炮筒,则尝试表现“未来派”绘画应有的运动感和“瞬时性”。然而,不同于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技术狂热,朱金楼在左下角描绘的骷髅形象喻示死亡;前者的狂热和西方早期科幻小说家分享同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而后者对此持批判态度。在1936年的狂想漫画家眼中,那些冰冷的钢铁并不意味着光明的高技术未来,而意味着战祸。61
图 3 “狂想专号”中编封面
《死光时代》
图 4 《未来之惊怖》
这种悲观和“未来派”绘画表现形式的杂合在科学特辑的封面和封底中再度显现。封面漫画的背景中(图5),无线电塔、飞机和化工厂是现代工业的象征,两条长长的锁链则暗示工业远非一种“文明”,而是一种枷锁。前景中,一位西装革履的科学家跪倒在巨大化的机器人面前,围绕在科学家周围的是望远镜等自然科学范式的象征物,在自己制造的怪物面前,种种供科学研究之用的器物都失去了意义。62这里体现出另一种对科学主义的悲观:它不是出自科学与战争的联系,而是发自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科学特辑封底漫画的表现形式更具“未来派”特点(图6)。这张漫画描绘了未来某市突遭敌机侵袭,巨弹如雨,毒气纷纷而下的情形。为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全城市民皆避入公共避毒所,却仍觉不安,乃将全城市民用起重机移入直径二百四十六尺之远射炮中,由机器人领导,射入其他星球避难,同时用最新发明之“钢甲飞机”“钢甲汽球”,及可循探照灯之光而上的“空中坦克车”腾空驱擎敌机。图中自左下方斜插而上的便是这“远射炮”,下方的起重机还在不停地运输市民。处于视觉中心的蓝色飞机正腾空而上,探照灯发射出的光柱指引着“空中坦克车”擎天驱敌,他们的敌人便是那背景中密密麻麻的小型战机。上方飞艇一般的“钢甲汽球”,倒与晚清“科幻奇谭”中对飞艇的表述有几分相似。这张漫画同样没有留白。
图 5 “狂想专号”
科学特辑封面
图 6 “狂想专号”
科学特辑封底
与《中国漫画》其他封面、封底不同,科学特辑的封面和封底符号遍布,不留空隙。这种做法体现出漫画家对“未来派”绘画构图方式的理解。封底漫画中直入云霄的巨炮、探照灯发射的巨型光柱与右侧“钢甲汽球”释放出的浓烟构成了图像的动态,不同的空间与时间在一张图像中交响,所奏音乐却只令人感到恐怖,不令人心潮澎湃。63以这样的方式,“狂想专号”科学特辑在视觉上对“未来派”绘画的表现形式做出新的建构。
四、结论
作为在全国范围(包括香港)内,甚至南洋、日本等地也曾发售的通俗读物,《中国漫画》“狂想专号”因以“狂想”的名义,言官方媒体所不能言之事,备受读者欢迎。这三编“狂想专号”或许启发了于1943年2月以来出版的第17期、18期《生活导报》“狂想专号”,二者在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呈现出相似的特征。64
在1937年的恐怖降临前夜,《中国漫画》“狂想专号”通过图像和文字新辟时空,让读者和作者积久的愤懑得以释放。这些以“狂”为名的讽刺漫画、杂文,再现了1936年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观念。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发一回“科学”狂,是这一时期身处上海及其他都市的漫画艺术家回应压抑社会气氛的方式,也是他们回应读者与作者在上编“狂想专号”出版后“狂兴未尽”的方式。这些作者狂想中的“科学”与晚清“科幻奇谭”所言说的“科学”呈现出相似的特征。但是,从晚清民族危亡之际的“格致强国”到新文化运动高呼的“赛先生”,科学文化的语境已经转变,科学主义的观念日渐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中日战争前夜,民间散布的悲观与怀疑不断冲击着科学话语的霸权地位,这在民国科幻小说的书写中亦有迹可循。“狂想专号”科学特辑以晚清“科幻奇谭”的表达方式讲述民国的科学想象,以戏谑、幽默的口吻讽刺科学技术及其后果,是对晚清“科幻奇谭”的科学话语的建构实践。作为漫画,“狂想专号”有意调用“未来派”绘画的形式语言来配合其科学想象。然而,有关“未来派”的美术知识是中国美术批评家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绘画理念的创造性翻译。“狂想专号”中的图像是对这一经过转译的“未来派”绘画理念的视觉建构。狂想漫画家们妙用“未来派”绘画的诸种原则,却并未描摹出乐观的、高技术的未来图景;相反,他们试图表现战争的惊怖与技术的失控,这让我们看到了“科学世界观”辖域而外的科学观点。
本文原刊于《科幻人文》(第一辑)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责任编辑:阿泽
您可能还想看
四十二史
宇宙的未来/现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