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武宗
学
天下武功
武派侠 又见风波恶·江湖行路难
以武学打开世界·智者不匹夫 武者无懦夫
甘联珠当时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被桂武拉着,一路从家门冲了出去,一口气不停歇地跑了二里地。甘联珠这才缓过神来,问桂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啥祖母的棍子打过来,我闭眼等死的时候,你却能把我救出来?”
桂武笑着说:“我哪有那本事把你救出来啊!这事儿也挺邪乎的。你当时被祖母的棍子打得架不住,身子往后一仰就倒下了。我眼睁睁看着,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也知道自己本事不行,铁棍还坏了,哪敢动手帮你啊?心里正又急又痛呢,突然就看见一只大鹰,比闪电还快,从门外飞扑进来,一爪子就把那要打下来的棍子给抓住了,从祖母手里夺了过来,然后翅膀一扇,好像是扇在了祖母脸上,就听见祖母’哎呀’一声,连旱烟管都丢了,双手捂着脸。我一看这情形,心里那叫一个痛快!不敢停留,也来不及说什么,拉着你就跑了。”
甘联珠一脸吃惊地问:“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一只鹰?”
桂武说:“大白天儿的,我能看错吗?确实是一只特别大的黑鹰!”
甘联珠叹了口气说:“坏了!我家的仇敌金罗汉来了。除了他,谁还有两只神鹰啊!”
桂武问:“金罗汉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就成了你家的仇敌呢?”
甘联珠说:“我经常听我父亲说,江湖上有个吕宣良,外号金罗汉,专门跟崆峒派的人作对。他养了两只神鹰,好多有本事的人都败在了那两只鹰的爪下。我师伯董禄堂,差点连命都没了!所以金罗汉是我家的仇敌,不知道他今天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还救了咱俩的命?”
桂武又问:“他是不是个白胡子老头儿?”甘联珠点点头说:“我虽然没见过他,但听说他年纪很大了。你问这个干啥?”桂武就把前日在山顶闲逛,遇到金罗汉的事儿说了。
甘联珠笑着说:“幸亏你前晚没跟我说这事儿。要是你跟我说了,我肯定怀疑是金罗汉故意来离间我家人的,特意来挑拨你的!我要是有这疑心,不但不肯跟你一起走,说不定还会怀疑你是来我家卧底的,那事儿可就糟透了!”
桂武说:“我之所以没跟你说遇见他的事儿,一是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要是把当时那种神出鬼没的情形说出来,怕你疑虑;二是,我本来就想离开你家,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不是遇见他才有的,所以就没说。”
甘联珠点头表示认同,又说:“这儿离家太近了,咱们不能久留!你打算去哪儿,咱们这就走。还好我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咱们只要出了这个门,在这儿停留一会儿,倒也没什么。要是他俩在家的时候,咱们不能马上逃出三十里地以外,恐怕咱俩的头,这会儿早就被飞剑给取走了呢!”
桂武说:“我来湖南,本来是想找我姑母,投靠她,让她给我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无奈找了好些日子,都没找到。现在只好再去临湘,慢慢找。我想我姑母现在年纪应该还不到四十岁,肯定不会去世。她出嫁得早,那时候我才四岁。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和姑父陈友兰在我家住了好些日子。后来我父亲一死,路远了,两家就不怎么来往了。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我收到姑母让人送来的讣告,才知道姑父也死了。姑母带着一个两岁的表弟,听说搬到临湘乡下住了。之后就再也没消息了。这也怪我那时候太不懂事,整天跟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家里的事儿一点儿都不过问!我姑父去世都这么久了,姑母又不在县城,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所以没找到。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还是去临湘吧!”
于是两人就去了临湘。甘联珠拿出些珠宝,变卖了换成钱,买了田产和房子,也没跟人说自己的来历。
临湘的人见他们两口子都长得那么漂亮,举止又很阔绰,也没人怀疑他们是强盗窝里出来的人。桂武逢人就打听他姑母的消息,可是一年多过去了,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桂武琢磨着,他姑母要么是已经去世了,要么是搬到别的州府县去了,不在临湘。慢慢就把找姑母的心思给放下了!
有一天,桂武正和甘联珠在家闲聊呢。突然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孩,长得骨秀神清,英气勃勃,站在门外,大声问里面:“这儿有一位姓桂的公子吗?”桂武听了,心里一动,一边迎出来,一边留意看那小孩的眉眼,居然跟自己的眉眼一模一样,要是俩人一起走,谁见了都得说是同胞兄弟。他一边想一边走到近前,也不先说自己是桂公子,先问那小孩:“你从哪儿来的?姓什么?找桂公子干什么?”
那小孩见桂武出来了,眼睛也不停地在桂武脸上打量,不等桂武说出姓氏,小孩就跪倒在地,说:“我母亲今天才知道表哥在这儿,特意让我来请表哥到我家去。”
桂武听了“表哥”这个称呼,这才想到是自己姑母打发表弟来请的,连忙也跪下去,把表弟扶起来,心里那叫一个高兴,自不必说。他一手拉着表弟的手,一起进了屋,跟甘联珠也见了礼,桂武问表弟叫什么名字。
表弟说:“我叫继志。我母亲吩咐,路上别耽误,见到表哥就请他一起去,别让我母亲盼着。”
桂武高兴地问:“姑母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可笑我专门为了找姑母,才来临湘的,在这儿前后住了三年,都没找到姑母住的地方。今天倒是她老人家知道了,还劳烦你跑这一趟来找我。”
陈继志说:“我母亲怎么知道表哥在这儿,她没跟我说,表哥去见了我母亲,自然就知道了。我母亲还吩咐了,表嫂也一起请去。”
桂武回头看着甘联珠笑着说:“怪呀!她老人家连你在这儿都知道了。”
甘联珠也笑着说:“既然知道你在这儿,自然也就知道我了。我本应该一起去请安的,只是她老人家住在哪儿?这去有多远?得问问小弟弟。”
桂武说:“他这么小的年纪都能来,肯定没多远,这是显而易见的。”陈继志也点头说:“没多远!”
甘联珠走进自己卧室,换衣服去了。桂武让陈继志坐下,也跟着甘联珠进了屋。只见甘联珠正坐在床上裹脚,把铁尖鞋套在里面。桂武惊讶地问:“又不去跟人家动手,你穿这东西干什么?”
甘联珠笑着说:“非得跟人家动手才能穿这东西吗?”
桂武说:“我觉得去见姑母,用不着穿这东西。”
甘联珠把桂武拉到跟前,低声说:“你又不认识你这位表弟,今天突然跑来,让我们俩一起去。你想想,你前后在这儿找了三年,就住在这屋子里,也有一年多了,姑母住的地方离这儿又不远,你怎么有心找却找不到,她没想到你在这儿,却打听出来了。这事儿不是挺说不通吗?而且我们住在这儿,从来没跟人来往过,也没跟人说过自己的姓名来历,她从哪儿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呢?你刚才问你这表弟,看他怎么说,他不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让你去问姑母,自然就明白了吗?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不去也不好,又怕是真的,要去就不能不防备着点儿,小心点儿总没错。”
桂武听了甘联珠的话,心里也有点疑虑。只是看陈继志的相貌,跟自己特别像,又相信是自己姑母的儿子。因为他知道自己从小就跟姑母长得像,母子面庞相似,这是很平常的事儿!不过他也觉得甘联珠顾虑得有道理,自己衣服底下就暗藏了防身兵器。
甘联珠打扮好了,一起出来跟陈继志动身。陈继志在前面走,桂武两口子跟在后面。走了半里多路,陈继志的脚步越来越快。桂武跟甘联珠说:“看不出来他这么小的年纪,这么能跑。咱们也把脚步放快点儿吧,别追不上他,让他笑话!”甘联珠微微点了点头,没说话。
两人真就把脚步放快了。又走了半里,桂武忍不住问:“老弟不是说没多远吗?还有多远呢?”陈继志回头笑着说:“那有多远,一会儿就到了!”陈继志嘴里说着,脚底下更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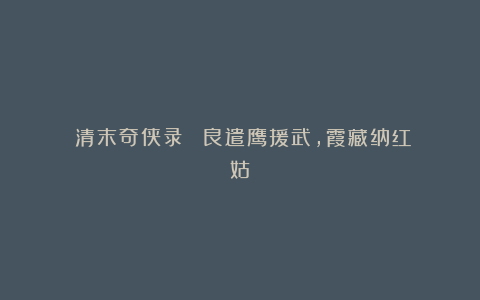
桂武都跟着跑出汗来了,甘联珠还不怎么觉得累。不一会儿,一座很高的石山挡住了去路。陈继志停下脚步,正要和桂武说话,桂武已经落后有四五丈远了,甘联珠却只离了几尺。桂武脸上有点不好意思,走近陈继志说:“好久没走这么多路了,走不动,让你笑话了!还有多远呢?”
陈继志笑着说:“本来表哥是公子哥出身,自然不会走路。就是表嫂,也是千金小姐,怎么能跟我这个乡下放牛羊的小孩比,我整天翻山越岭都走惯了。现在得翻过这座山,这可怎么办呢?哥哥、嫂嫂能爬上去吗?”
桂武看那山,全是房子那么大一块的顽石堆成的,石头上都是青苔,别说树了,连草都没长一根,更没有上去的路,陡峭得跟墙一样。心想凭自己这一身本事,上去是能上去,但是石头上不长青苔才好啊!脚踩在青苔上面,是滑的,万一蹿到半山腰,一脚没踩牢,滑下来,那不得摔个骨断筋折啊?又想表弟这么小的年纪,他未必就能爬得上去,他要是真有这能耐,不怕滑跌下来,那我们就照着他脚踩的地方踩,也就不怕滑了!当下对陈继志说:“去老弟家里,非得从这座山爬过去吗?要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我们也只好跟老弟走了!”
陈继志说:“第二条路是有,不过得回头,绕一个大弯子。我怕母亲盼着,所以把表哥表嫂引到这儿来了,我在前面慢慢上去,二位照着我这样上来就行。这座山我三四岁的时候就爬惯了,不算一回事儿!”说着,举步就跟走平地一样,一点儿都不费劲,转眼就上到半山腰了。
甘联珠也跟着飞身而上。桂武得抖擞精神,连蹿带跃地往上赶,好不容易使出浑身力气,赶到半山腰一看,陈继志已经神闲气静地站在山顶了,甘联珠虽然也上去了,但是脸上变了颜色,站在那儿喘息不已。
桂武这时候两条腿都疲软得动不了了,上半截的山势更陡峭了,实在没力气爬上去了!
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低头就找了一块平整点儿的石头,坐下来歇息。心想:“我小时候在家乡,虽说家里有钱,有下人伺候,不用我自己干活,但是我生性就喜欢武术,整天在外头翻山越岭的,但是像这么陡峭的山,别说我没上过,又几时见有人能上呢?甘联珠是练就了上高的好本领,尚且累得喘气不匀,可见我这表弟的本领,肯定还在她之上!不过我小时候,并不曾听我父母说过我姑母也会武艺,算算我表弟的年龄,现在不过十一岁,又没有父亲,难道是天生的这么敏捷的身体?甘联珠怀疑这事儿有点蹊跷,她怀疑的,恐怕没错!”
桂武正低头琢磨呢,忽然觉得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在动,忙抬头一看,原来是一根极粗的葛藤,从山顶垂下来,陈继志捏着一端,在上面说:“表哥身体疲倦了,就双手紧紧握住这藤,我拉表哥上来!”
桂武又想,他这么点儿大的身体,怎么能拉得起我呢?这不是开玩笑吗?别连他自己都拉下山来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仰面朝上说:“用不着拉!我再歇息一会儿,就能上来了!”
陈继志在上面说:“我母亲在家等得着急呢!还有几里路,别耽误了!”
桂武也实在是疲乏不堪了,姑且握住葛藤试试,要是上面拉不动,也不要紧,而且有甘联珠在上面,也可以帮着拉一拉。于是两手牢牢地把葛藤握住,顿时就身不由己,两脚腾空,仿佛登云驾雾一样,直往上升。桂武的身躯挺重,拉得那葛藤喳喳地响!桂武心里慌,就怕葛藤从中断了,那必然摔得骨断筋折!还好陈继志手快,就跟在吊井里提水似的,只须几把,就把桂武吊上了山顶!
桂武站稳了脚,满脸通红地问:“老弟会上山,可以说是从小翻山越岭惯了。两膀这么大的力气,难道也是吊人吊惯了吗?老弟得跟我说个明白,我才敢跟老弟到姑母那里去,要是不说明白,我总免不了有些疑虑,我与其搁在心里怀疑,不如请你说个明白,姑母究竟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
陈继志笑嘻嘻地答道:“表哥要问我两膀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吗?我母亲还时常骂我生得太脆弱,练不出力气呢!表哥怀疑些什么?下山不远,就是我家,见到我母亲,我母亲都会说给表哥听的!这根葛藤,是我三四岁的时候,我母亲给我做帮手的,起初没有这葛藤,这座山不能上下,如今上下惯了,这葛藤就没用处了,搁在这山顶上,都好几年了。”
陈继志刚说到这儿,忽然停住嘴,侧着耳朵往山下听,接着跟甘、桂二人说:“我母亲在下面呼唤了,请快走下去吧!”甘、桂二人也听见有女子的声音在山下呼唤。陈继志匆忙把葛藤塞进石岩里面,引着二人下山。
下山的路,不像上山那么陡峭,三人走到山下,陈继志指着前面一个穿道装的女子,跟桂武说:“表哥请看,我母亲不是在前面等着吗?”桂武没回答,心想,我姑母怎么成了一个女道士?渐渐走近了,仔细一看,还约略认得出容貌来,不是自己的姑母是谁呢?
桂武小时候乳名叫清官,他姑母已经迎上来叫他的乳名,笑道:“十年没见了,见面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我知道你找我很辛苦,我到今天才知道呢!”桂武这时候,疑云都散了,忙紧走几步,跪下地磕头,口称姑母,甘联珠自然也跟着跪拜。
他姑母笑着问甘联珠:“你就是北荆桥甘家的小姐吗?也真难得,有你这般明白大义!我听说的时候,就喜欢得不得了!”甘、桂二人都猜不透他姑母是怎么知道的,当下在外面,也不便开口去问。
一起到了他姑母家里,谈论起来,原来他姑母就是前几回书里写的红姑。只因为她丈夫陈友兰死后,红姑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守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取名叫继志。陈友兰留下不少财产,当时陈家的族人,都难免有些眼红,想把红姑排挤得改嫁,族人欺负继志年纪小,好把遗产平分了,以为红姑年轻貌美,肯定容易诱惑。
哪知道红姑的节操特别坚定,族人用了好多办法,都没能把红姑诱惑动。红姑的性情特别豪爽,不肯拘泥小节。平常没了丈夫的妇人,在家守节,都是浑身缟素,到死不肯穿红戴绿,凡是年轻妇女所享受的一切繁华,都得摒弃干净。而红姑生性爱红,又本来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丈夫在世时穿的衣服,不肯完全废掉,安葬了陈友兰之后,还是照常穿起来。
族人便抓住这一层做证据,在临湘县告红姑不贞节。亏得那县官廉明,把族人申斥了一顿。
红姑就搬到临湘乡下住了。族人告红姑没成功,反被县官申斥了一顿,红姑占了上风,心里不服气。见红姑独自搬到乡下去住,便集合许多无赖,去红姑家里行劫。
这时候红姑只雇了一个乳母、一个粗使老妈子,住在自家的田庄上。这天黄昏过后,忽然来了一个化缘的道姑,年纪约有六十多岁,要在红姑家借宿。陈友兰在世的时候,对这些三姑六婆,本来就极为厌恶,从来不许上门。如今陈友兰死了,红姑见这道姑年纪已经老了,天色又已经黑下来了,要是不许这道姑歇宿,心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让她和老妈子同睡。
谁知道到了半夜,族人行劫的来了,一共有二十多个壮健汉子,一个个都用锅烟涂黑了面孔,把唱戏的假胡须挂上了,劈门而入,把红姑和乳母、老妈子都捆起来,堆在一张床上,反锁了房门,各自抢东西去了。
红姑见乳母也被捆了,却不见自己的儿子,便问乳母:“继志在哪儿?”乳母回答说不知道,说自己被捆醒来,已经不见了公子。老妈子就说,那借宿的老道姑,也不知去向了,她肯定是强盗一伙的,特意来这里做内应。
红姑守节所希望的,就在这个小孩,一旦被强盗劫得不知去向,怎么能不心痛,只恨自己手脚被捆了,不能动弹,不然,也一头撞死了。正在那里伤心痛哭,忽然房门开了,有人拿了个火把过来。红姑以为是强盗,把两眼闭了不看。
只听得乳母喊道:“奶奶!看呐,公子果然是在这道姑手中抱着呢!”红姑这才睁开眼,只见那道姑笑容满面的,左手抱着继志,右手握着一条竹缆子火把,照着红姑说:“奶奶不用害怕,强徒都被贫道拿住了,公子一点儿也没有损伤。”说着,把继志放在床上,只用手在三人身上一摸,捆缚手脚的麻绳,顿时就像被刀割断了一样。
红姑坐了起来,一把抱了继志,才向道姑道谢,问:“怎么把强徒拿住的?”道姑笑道:“请奶奶同去外面一看,便知端底。”红姑心里还虚着,仍有些胆怯,不敢去看。
道姑拉着红姑的手说:“有贫道在这儿,怕什么呢?一个也没跑掉,只看奶奶要怎么发落?”红姑仿佛在梦里似的,跟着道姑出来,见堂屋角上,挤满了一角高高矮矮的人,脸上都涂抹得那么可怕,没有绳索捆绑,也没有墙壁遮拦,却都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各人的眼睛又都是睁着的,只是不能活动着看人。
红姑向那道姑问道:“师傅用什么法子,能使他们这样挤在一块儿不动呢?”
道姑笑道:“这法子容易得很,奶奶要是想学,贫道可以传授给你,在山野之间居住,这类法子,也不可不知道一些儿,贫道数十年出行野宿,就全仗这些方法,保护性命。这些强徒,奶奶要怎么处置,只须说一句,都交给贫道办理就是,据贫道看,这些强徒,必非是寻常强贼,奶奶两岁的公子,与强徒有何仇恨,他们竟想置之死地,若不是贫道在旁边,把公子救了,怕公子此刻的身体,已是四分五裂了,贫道因见他们如此狠毒,才存心一个也不教他跑掉!”
红姑一听道姑的话,已经知道这些强徒,全是同族的无赖子,只要自己没受什么损害,便不想再结深怨。当下请道姑教众强徒醒来,红姑亲自训斥了一番,一个一个地放了,并不追究。
红姑的天分本来就高,从此就拜那道姑为师。那道姑姓沈,道号栖霞,也是有清一代的女剑侠,和金罗汉吕宣良,最是投契,终年借化缘,游行各地,专门救济贫苦,诛锄强暴。她也和金罗汉一样,没有固定的庵寺。因见红姑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很愿意收她做徒弟。五年之后,红姑已经练了一身了不起的本领。
江湖上人因为她喜欢穿红,都叫她为红姑。红姑一面跟沈栖霞学道,一面督促陈继志练武艺。
陈继志才两岁,刚学会走路,就教他拣不好走的山岭去爬,五岁,就教他练气,还有道家一切的基础功夫。红姑的本领练成了,陈继志的本领,便也不在人下了。
这天,红姑在清虚观中遇见金罗汉,金罗汉问红姑,已经见到桂武没有,红姑见问,还摸不着头脑。金罗汉就把桂武来临湘投靠红姑没找到,在华容卖艺,入赘到甘瘤子家中,想逃没计,以及自己如何指引桂武,如何派鹰去救了甘联珠的话,说了一遍。又说:“我前日在一家新造的房子门前经过,还见甘瘤子的女儿,在那房子里面,我料想就是桂武夫妇住在那里,只道你早已见了,还不知道吗?”
红姑这才问明了那房子的所在,回家就教陈继志去请。所以说起来,知道得这么详细。红姑把前后的事儿,说给甘、桂二人听了,甘联珠因为想跟红姑学习剑术,就认红姑做了义母。从此两家往来,十分亲密。
却说甘瘤子父子回家,听说自己女儿和桂武走了,倒不怎么在意。听到末尾,来了一只黑鹰,把自己母亲的杖抓去,并用翅膀拂伤了母亲的左眼,知道是金罗汉派鹰来救的,便气得暴跳如雷,恨不得抓金罗汉拼命,只因知道自己的本领,不是金罗汉的对手,现放师兄董禄堂就是榜样,只好勉强按捺住火气。
甘瘤子的母亲是个年老的人,受了这次大惊吓,心里再加上一气,不到半月,就呜呼哀哉死了。甘瘤子既然和寻常人一样住家,不能不发丧守制,就把这仇恨,延搁下来。有一天,他师叔四海龙王杨赞廷来了。甘瘤子把金罗汉吕宣良,屡次如何欺负崆峒派人,添枝带叶地说了,有意激怒杨赞廷。果然把杨赞廷激得要去找吕宣良,替崆峒派出气。
不知找了没有,出了气没有,咱们还是等下回再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