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秋天,当解放军的红旗插上西宁城头时,所有人都以为,青海这片土地上的动荡将从此画上句号。
然而,旧势力的残余却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虽然马步芳的部队大部或溃散、或投降,但那些散落在青海各地的旧军官、保甲长,以及被裹挟的土匪,却在暗中伺机而动。
他们认为解放军初来乍到,根基未稳,对地方的控制力尚弱,因此在暗地里勾结串联,企图卷土重来。这股潜藏在平静下的暗流,很快便掀起了波澜,青海大地再次陷入了动荡。
然而,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这股匪患为何仍能在元宵佳节血洗工作组,酿成惨案?
大通县的冬天,山岭披着厚雪,羊皮袄是抵御严寒的唯一依靠。马老五,曾是马步芳手下的营长,败退后不肯投降,一直藏身于山中。
1950年元旦刚过,他带着几百人,趁夜色摸到县城附近的村落。冰冷的月光下,匪徒推开一户户农家的门,抢走刚分到手的口粮,还砸毁了区政府的牌子。
有个年过花甲的李姓老农,因为在院口说了一句“解放军是好人”,被马老五的人当场用马刀劈倒,鲜血在地面结成了暗红的冰碴。这一幕,令村里人至今心有余悸。
消息很快传到西宁。刚进驻青海的解放军,顾不上休整,当夜拔营北上。部队穿着单衣,在齐膝深的积雪里一步步蹚向大通。
途中,他们遇到一个放羊的少年,十五六岁,执意要带路——原来他的父亲就在前不久死于马老五的刀下。战士们默默接过他递来的干粮,谁都没多问一句。
1950年春天,匪患在青海多地如毒草般滋长。门源县的娘娘山成了匪徒的老巢,白天他们藏在山洞里,晚上顺着羊肠小道下山骚扰县城。
一次,县大队十几名战士押送文件途经山脚时,被两百多匪徒围困在一间土坯房里。子弹打光后,他们用石块还击,直到仅剩的两名重伤员被乡亲们用柴车掩护送出。房门被撞开的瞬间,战士们的呐喊声还在风雪中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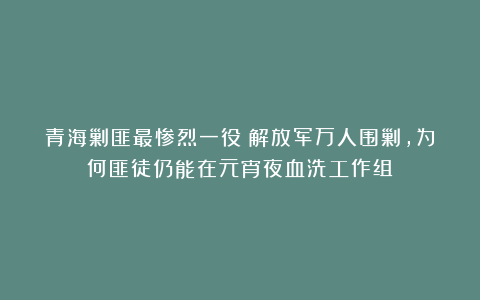
湟中县的匪徒更狡猾,他们换上百姓衣裳,混入村庄,伺机下手。一次工作组下乡宣讲土地政策,刚发完传单,麦垛后就窜出十几名持刀匪徒。
驻村排长王德胜一把推开身边的女干部,迎向闪着寒光的刀锋。钢刀划开了他的军装,血染透棉衣,他却死死抱住一个匪徒,直到力竭倒下。乡亲们说,那天黄土被血浸得发黑,连风都带着腥味。
1951年春天,新疆境内的乌斯满匪帮败退至青海,与本地股匪会合,四百余人逃进了柴达木盆地。那是片人迹罕至的荒原,戈壁连天,风卷沙如浪。
解放军追击部队行军三天三夜,干粮早已吃尽,士兵只能煮皮带充饥,渴到极处时甚至喝自己的尿液。俘虏后来回忆,他们中许多人因缺水倒毙在沙中,看见解放军炊烟时,宁可放下枪投降,也不愿再受荒原之苦。
循化的夏天,本应是河水丰盈、草木繁盛的季节,却因匪徒的围村而蒙上阴影。那年夏天,两个受伤的解放军被藏在村中菜窖。匪徒围困三天三夜,扬言不交人就烧村。
村支书马占福站在村口,面对刀枪毫不退缩:“要杀冲我来,娃娃们无辜。”他最终被乱石砸死,两名战士却得以保全。乡亲们至今记得老汉尸身前那片被血染红的土地。
1952年正月十五,元宵的灯火尚未点亮,互助县的夜色中却潜入了一股匪徒。他们闯入工作组驻地,杀害了正在伏案写报告的三名干部。噩耗传至西宁,军区领导当场拍案:必须调集兵力,一举剿灭。
作战命令下达后,来自青海、甘肃、宁夏的骑兵与步兵共一万余人,在雪原和山谷间铺开,像巨网般合围。战斗在日月山最为激烈,山顶碉堡中机枪喷吐火舌,解放军在雪坡上接连冲击。白雪被鲜血染成斑驳红色,一个17岁的四川新兵腹部中弹,仍拖着伤躯向山顶投出手榴弹,直到生命定格在冰冷的冻土上。
历时二十天,战斗共消灭土匪千余名。剩余的零散匪徒被武工队逐点清剿。那时,武工队白天帮乡亲耕种,夜晚背枪巡山。战士张柱子在农家养伤时,匪徒突然闯入,主人的闺女急中生智将他推入地窖,自己却被枪托砸得血流满面,一声不吭。
循化、湟中等地在这几年中,因匪祸丧生的百姓数以百计,许多村落化为废墟。但人心始终向着保卫他们的解放军。回族老人马大爷曾将七名伤员藏在炕洞里,面对持枪的匪徒,他稳坐炕头抽烟,任凭殴打也不吐半句。
妇女们夜里给山上的武工队送饭,揣着馍在山间跋涉十几里,脚磨出血泡也不回头。有的被匪徒抓住审问,咬牙说“不知道”,纵使刺刀逼到腹前,依旧不改口。
1952年夏,青稞抽穗,格桑花遍地,匪患终于平息。军民在烈士与遇难乡亲的坟前种下成排小树,随风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