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的冬天,冷得像刀子。雪没膝深,风能把人脸刮开花。
那年正月初七,猎人老宋在山里打猎。他在秦岭一带干了二十多年,啥猛兽没见过?黑熊、野猪、豹子,他都打过。
可那天,他犯了个错,一个他这辈子都抹不去的错。
事情起因是山上猎物越来越少,村里人年关前几乎断了肉食,老宋咬牙带上猎枪进山,说啥也得搞点东西回来过年。
雪地里有一串梅花爪印,他认得,那是熊。脚印深、跨度窄,说明这熊饿得不轻。
他一路追了两个山头,终于在一片老松林下,看见了那头母熊。
母熊正用爪子刨着一堆枯木,估计想找点虫子充饥,肚子瘪得吓人,肋骨都凸出来了。
老宋没多想,抬枪就打,一枪命中,母熊倒下前,朝他咆哮了一声,那声音不大,却让他心头一紧。
等他走近,才发现,母熊乳头又肿又红,明显是哺乳期。他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四周寂静,他顺着母熊死前盯着的方向走去,在不远处一处石洞前,看见了两只熊崽。
毛茸茸的小家伙,才巴掌大,黑乎乎一团,缩成一堆瑟瑟发抖。一个略胖,眼神呆萌,另一个瘦小,眼睛里全是警惕与愤怒。
老宋蹲下来,掏出身上那点干粮分给它们。小胖子哼哧哼哧吃了,瘦的那只却死盯着他,甚至在他靠近时朝他龇牙。
他叹口气:“是我错了,可你们娘也回不来了。”
说着,他脱下大衣,把两个小家伙裹起来,抱回了家。
养熊崽不是件容易事。
起初是羊奶兑米汤,小家伙吃得一脸都是。老宋把胖的叫“墩墩”,那只警惕的取名“尖尖”,因为它眼神尖,爪子尖,连动作都跟刀子似的。
墩墩乖得很,没几天就认人了,老往老宋怀里钻。尖尖则一直冷冷地看着他,从不亲近,也不撒娇。
老宋知道,尖尖记着那一枪,记得谁夺了它妈。
两年时间过去,两个熊崽长成了百十来斤的大小,院子都快关不住了。老宋在山后给它们搭了窝,每天喂红薯、玉米糊,还教它们挖树根、掏蜂蜜。
墩墩最听话,老跟在他屁股后头;尖尖还是冷,甚至有天深夜,老宋在柴房睡着,猛一睁眼,发现尖尖正站在门口,盯着他看,眼神一如两年前——带着恨。
“你要动手,就别犹豫。”他自言自语。
尖尖没动,只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到了第三年春,老宋知道,不能再养了。这俩家伙已近成年,是得还山林了。
他带着它们走进秦岭深处,找了个水草丰茂的地方,搭了个简易木棚,放下食物,拍了拍它们的脑袋:“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别回来了。”
墩墩似乎明白,一脸不舍地蹭他裤脚。尖尖没看他,转头进了林子。
老宋站了很久,直到身影彻底看不见,才转身下山。
以为故事结束了,其实刚刚开始。
一年后,老宋家的狗一夜之间被咬死,尸体被整齐地摆在院子中央;第二年,鸡窝被翻,十几只鸡全部没了头;第三年,他的菜园一夜之间被踩得稀巴烂,水缸碎在地上,瓦片像是被熊掌重击。
每一次,现场都会留下一撮黑毛——细长、浓密,明显不是野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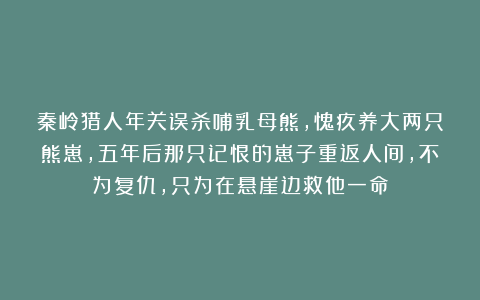
他知道,是尖尖。
不是饿了,是故意。
它回来了,带着仇,带着恨,带着三年沉淀的记忆。
村里人劝他设陷阱、下毒饵,可老宋只说:“是我欠它的。”
第五年,腊月。
山雪封路,村子几乎与世隔绝。
老宋为了过年打点野味,上山查看陷阱。雪厚得吓人,每一步都要费大力气。
中午时分,他来到一处断崖边,打算回头,忽然一股劲风从后袭来。
他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猛地推下崖。
千钧一发之际,他手勾住了崖边的一根枯藤。身下是几十米深的山谷,落下去,尸骨无存。
风雪里,一头成年黑熊站在崖边。
是尖尖。
它站在风中,四肢粗壮,身形庞大,早已不是那只瘦小的熊崽。一双眼,还是那样,透着深不见底的恨。
老宋苦笑:“五年了,还是来了。来吧,我不躲。”
藤条在咔咔作响,随时可能断裂。
尖尖一步步靠近,爪子伸出,在他头顶划了一道血口。它低下头,看着他,鼻子喷着白气。
然后,它咬住了他的胳膊。
老宋以为是最后一口,可那牙齿并没有深入骨头,而是稳稳地咬住,死死拖着他往上拉。
雪地上,一道红痕拉出好几米长。
终于,他被拽了上来,躺在地上,大口喘气,胳膊血肉模糊。
尖尖站在他面前,咧开嘴发出低吼,像是在咒骂,也像是在叹息。
然后,它转身,朝山林深处走去。
走了几步,又停下,回头看他一眼。
那一眼,复杂得让人心碎。
春天来了,老宋的胳膊落下残疾,握不住猎枪,干脆种起了玉米。
偶尔会有野兽下山啃几根,他也不恼,只是笑笑。
他知道,是它们。
后来,有村民说,在秦岭深处看到三只熊,一大一中一小。
大的黑得发亮,中的圆滚滚,小的额头上一撮白毛,特别显眼。
老宋坐在炕头,看着窗外春光,忽然笑了。
有些仇,不是非得血偿。
有些债,还过心,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