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基本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当下,人们或许会更多地聚焦于“文明标准”的探讨。我个人的观点,真正的“标准”理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度与准则——倘若某一准则仅适用于特定群体,那便不能被称为“标准”。基于这一逻辑,我并不认同非要为 “文明”主观地划定一套统一的标准。
1984年,美籍华裔学者、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到北京大学讲授“考古学专题六讲”,其中第一讲便聚焦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他在这一讲中提出的两个观点尤为关键。
第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未断的鲜明特质,这一特点使中国历史有望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杆。在他看来,中国历史如同一个 “正常发育的个体”,而欧洲及中亚、西亚地区的诸多历史则呈现“突变”特征,这种突变往往伴随着文明的不断“覆盖”。以古典时期的希腊、罗马为例,许多人误以为其历史是连续不间断的;类似地,也有人认为埃及文明始终保持原貌,但事实并非如此。埃及曾被波斯人统治长达百年,后又被希腊人统治百年之久——尽管这些统治者未对埃及的宗教信仰进行灭绝式打压,其行政体系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使得埃及在表面上维持着连贯性。然而,即便是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虽仍以“埃及”为名,实则已进入希腊化阶段,是希腊人治理下的埃及,其文明内核一直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波斯的情况亦是如此,在其鼎盛时期,统治范围曾扩展到欧、亚、非大陆,对区域内的文明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张光直指出,历史上包括古巴比伦所在的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等,即便被视为同一文明体系的延续,实际上也经历了多次“覆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持续发生,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强调,交流对文明而言无疑是有益的——如同物种若缺乏交流便会走向衰败,文明在交流中也会不断做出选择与调适,最终实现自我强化与发展。当然,交流过程中可能出现类似 “转基因”的争议性问题,但总体而言,文明正是在这样的动态互动中不断成长为更具生命力的形态。
而我国中原地区的文明,正是在持续不断的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逐鹿中原”,说的是周边地域的势力强大起来后,往往视入主中原为掌控天下的关键——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便道出了这一地理“熔炉”在古代中国政治与文明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历史上,中国周边的诸多文明在特定时期曾展现出耀眼的光芒,却因种种历史因缘际会渐趋式微。以良渚文明为例,它虽拥有5000余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以玉礼器、水利系统为代表的灿烂成就,但关于其主体人群的去向,始终是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地理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依托单一地理单元发展的文明,首先面临的是抵御风险能力的局限(如气候变迁、资源枯竭等);其次,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向外辐射的“溢出效应”——就像一个盛满水的容器,一旦达到临界点,水流便会自然向外漫溢,文明的扩张与交流也遵循着类似的逻辑。类似的情况也见于红山文化。这支以精美玉器、祭坛与女神庙为标志的北方文明,曾在辽西地区达到高度繁荣,但其后续的发展脉络同样指向与其他文化的融合。
龙山文化红陶鬶
事实上,纵观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许多地域文化都呈现出向中原汇聚的趋势。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化因子在中原地区碰撞、交融,最终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这一动态过程,恰如中国那句广为流传的俗语所概括的那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既揭示了地域文明此消彼长的客观规律,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在分合交替中不断凝聚的深层逻辑。
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恰似一个“揉面”的过程 ——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养分的过程中,这团“文明之面”被反复揉捏、延展,变得愈发“筋道”,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深厚底蕴。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北方地区的影响尤为显著。许多对中华文明发展至关重要的文化元素,如早期的战车技术、牛羊驯养技艺,乃至青铜冶炼的原料与技术,都可能经西北草原通道传入中原,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星堆文化的璀璨成就,同样是文明交流的生动例证。有人说其是“外星人文明”,这种说法忽视了人类文明互动的广泛性——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玉器造型中,既可见到中原商文化的印记,也蕴含着与西亚、南亚地区的间接交流痕迹,恰恰印证了古代中国也绝非封闭的孤岛。2020年,四川甘孜州皮洛遗址的发掘为早期人类的迁徙与交流提供了关键证据。该遗址出土的手斧、手镐和薄刃斧等石器组合,与欧亚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高度相似,被研究者认为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其年代可追溯至约13万年以前,通过最新系统年代测定,可以确认其遗址最底部的年代已经超过了20万年。这一发现表明,早在10余万年前,东亚与欧亚大陆西部的人类群体就已通过某种路径产生技术或文化联系,人类文明的交流互动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国虽因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 4000—7000米)的阻隔,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并未因此隔绝于世界。北方广袤的欧亚草原地带始终是贯通东西方的天然通道,而西南地区通过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印度河流域相连通,在张骞于大夏看见“邛竹杖、蜀布”前,可能已经存在持续很久的文化往来。这种“相对独立”与“适度开放”的地理特质,使得中华文明既能保持自身的连续性,又能不断吸纳外来养分,在动态平衡中实现螺旋式发展。
张光直的第二个观点,着重强调了中国研究对世界文明探索的独特价值。他指出,国际学界曾普遍以“文字、金属器具、城市”作为判定文明的核心标准,但这一标准在不同地域的适用性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的文明演进模式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特例。因此,对中国文明的深入研究,或许能为世界提供一套新的参考体系;若要完整理解世界历史的全貌,忽视中国历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张光直也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同样不能脱离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他认为,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探索,必须建立在不同文明个案的比较之上:通过对比才能清晰辨识各文明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而在共性中提炼普遍规律,在个性中理解文明的多样性。这种“以中国观世界,以世界观中国”的研究路径,既是他对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启示,也为全球文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维范式。
张光直的观点,本质上是对传统的国际学界“文明三要素”(文字、城市、金属器)标准的反思。他通过对中国早期文明(如夏商周)的研究发现,中国文明在形成阶段虽逐步具备这些要素,但其更核心的特征在于以“礼器体系”为标志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这与两河流域、古埃及等依赖文字与城市作为核心标志的文明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主张文明标准应具有多元性,中国案例的价值正在于打破了单一标准的局限,这一思路对后来“多元文明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
探源工程到底应该“探”什么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五千余年绵延不绝,形成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独特轨迹,就因为背后蕴含着自身特有的发展模式与精神特质。深入探究并阐释这些模式与特质,正是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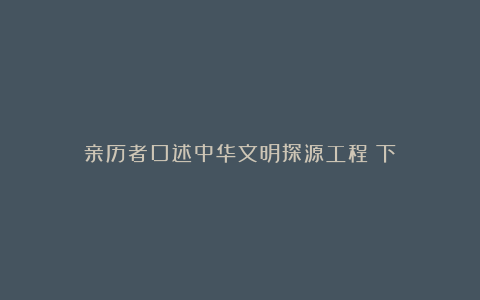
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在多个维度:文字体系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礼制传统从三代的宗法制度到后世的伦理规范,始终是社会秩序的核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虽历经冲突,最终多以融合收尾,而非文明的替代。这种 “和而不同”的包容力、“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智慧等,共同构成了文明延续的内在密码。文明探源的价值,不仅在于追溯历史的起点,更在于解码这些支撑文明存续的深层逻辑,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提供中国案例。
在诸多场合中,我其实不太倾向于使用“文明起源”这一概念,更多时候会选择“社会的复杂化”来描述相关进程。社会的发展本就是一个持续走向复杂的过程——好比最初某个地方只有一户人家,而后逐渐发展为村落,再进一步演变为乡镇、县城,最终形成城市、省份乃至国家。在这一演进中,人群如何组织、生计方式又以何种纽带将人们联结在一起,这些问题的厘清至关重要。社会复杂化的背后,固然有行政层面的推动,但更根本的动力源于需求。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本质上是需求的驱动——人并非孤立的个体,必然要与他人建立联系,而交换便是构建这种联系的重要方式。以水稻种植为例:水稻生产离不开协作,单靠一家人难以完成插秧等繁重劳作,于是全村人会互助协作,先帮一户插秧,之后这户人家再反过来协助其他村民。这种协作模式会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又会引发生产关系的调整。良渚文明中发达的灌溉技术与水资源管理体系,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协作需求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生产协作与资源管理的需求,正是社会从分散的氏族部落向早期国家形态过渡的核心动力,这也正是良渚文明能成为中国早期文明重要代表的原因之一。
2013年上海世界考古学大会期间,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参观良渚博物院
若要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模式加以概括,或许可以这样梳理: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乃至更早(相当于夏代存续的时空范围),受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北方地区出现持续干旱,原本适宜农耕产粮的区域逐渐转向游牧经济;而南方地区则频发洪涝灾害,像良渚这样以稻作农业为单一支柱的文明,难以抵御大范围洪水的冲击。彼时,北方与西部地区的干旱、南方的水涝,其影响范围逐渐蔓延至整个长江、黄河流域。反观中原地区,这里兼具高山、平原、台地与河谷等多样地形,加之植物种类的多样性,使得不同经济形态得以在此共存:河谷湿地可种植水稻,河谷台地适宜旱作粟黍类作物,山坡区域则易于发展畜牧。这种多元的生业体系,让中原地区在环境气候剧烈变化的时期具备了更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周边诸多区域的文明发展均遭受重创,而中原地区凭借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地形结构与生业体系的多样性,始终保持着发展活力,夏王朝或许便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崛起,早期文明也随之孕育成熟。可以推断,在夏王朝诞生之前,南北之间、东西之间必然经历了长期的整体交流与融合,正是这种持续的互动,为中原地区经济的整体性发展注入了动力,奠定了文明跃升的基础。
若我们将历史的目光再向前追溯,会发现另有几个时期的文明已发展到相当高度。例如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当时的文化已在广袤地域内形成显著的一致性——北至河套地区,南抵江汉平原,东达山东半岛西部,西达甘青地区,在这一辽阔范围内,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样与器物形制广泛分布,成为跨地域文化认同的鲜明标志。
庙底沟时期之后,进入仰韶文化晚期(亦称半坡晚期类型),各地文化又呈现出各自发展的态势,这正印证了前文所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规律。事实上,那种大范围的文化统一性往往如昙花一现,难以长期维系。究其原因,在缺乏成熟官僚体系与管理网络的时代,要对如此广袤的地域实行有效治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各区域很快便走向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这一现象可与后世的历史案例相互参照:亚历山大大帝用13年时间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但他去世后,帝国迅速分裂,各地相继出现不同的继承者政权。这些政权虽仍存在相互影响,却已形成各自独立的政治体系与文化特征。由此可见,文明的演进始终是一个充满变量的复杂过程,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交替、聚合与分散的循环,共同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
宋新潮(中)等人考察陕西石峁遗址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对待“文明标准”问题需持审慎态度,是因为西方曾将自身文明的标尺作为普世尺度,以此判定其他文化处于蒙昧、野蛮抑或文明阶段——这种认知本质上就是单线进化论的产物,忽视了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我们常说科学是一套完整体系,历史研究同样要兼具时代性与社会性。以“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概念为例,其形成便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遭逢列强侵略,知识分子为唤醒民族意识,开始追溯“民族始祖”。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符号被凸显,以黄帝为起点的纪年方式逐渐流行。当时,刘师培、章太炎等革命派为对抗清朝纪年与西方公元纪年,主张采用“黄帝纪元”,并将黄帝诞生年份推算为公元前2700年左右(刘师培主张以黄帝降生为纪元元年,约为公元前2760年;章太炎以黄帝即位为起点,约为公元前2698 年),至民国时期恰好约五千年,“中华五千年”的说法由此广为流传。事实上,“五千年”更像是特定历史阶段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我们不必执念于用考古实证去“证明”这个符号的绝对真实性。比如,有人因埃及文明的早发而产生莫名的自卑感,这种心态恰恰落入了单线进化论的陷阱。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迥异,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千差万别,文明发展模式自然各具特色—— 正如不能简单评判埃及金字塔与中国长城孰优孰劣一样,文明的价值本就不在于单一维度的比较。
因此,我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不在于发现的遗址有多宏大、出土的器物有多精美、可追溯的历史有多久远,而在于通过严谨、科学、系统的解读,探索并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独特发展路径。这项工程的意义,更不在于得出某种固化结论,而在于在探索过程中深化对自身历史与文明的认知,同时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提供中国视角与经验,并让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不断走向世界、惠及人类。
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历经万千变迁,却始终有一些内核未曾改变——比如我们民族特有的坚韧性、对和平的执着与兼容并蓄的胸怀。中国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背后是对“希望”的执念、是绝境中求生存的智慧: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总能找到适应之道;既善于因时而变,又坚守“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这种深植于民族性格中的韧性,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的重要密码。我们崇尚“以和为贵”,却也懂得“和而不同”——在坚守自身立场的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些贯穿千年的特质,如同中华文明的“DNA”,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正在于发掘并阐释这些支撑文明存续的核心密码。
在现代语境下,我们需要以世界眼光审视自身历史:摒弃固有的优劣比较思维,不再执着于与其他文明论高低、比先进,而是从历史研究中汲取对当下有益的智慧——无论是对待自然的敬畏、治理社会的经验,还是处理人际的准则,这些不仅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更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中国启示。
同时我们也需清醒地认识到:探源工程的成果只是特定阶段的认知,不可能得出一劳永逸的终极结论。古代社会的丰富性若以“亿”为计量,我们目前窥见的或许仅为“一”;若仅以片段见闻便轻率定论,难免失之偏颇。唯有将具体历史阶段或事件置于数千年文明长河中审视,方能真正理解“何为中国”,读懂这片土地上文明延续的深层逻辑。(完)
本文选自《纵横》2025年第9期,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宋新潮口述,杨玉珍采访整理。图片由口述者提供。
编辑:杨玉珍
校对:于 洋
审核:张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