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周易研究》2019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
秦洁:山东日照人,历史学学士,哲学硕士、博士,文学博士后。现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易学、象数学和易学文献研究。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特别委托项目等多项。
主要内容
摘要
于省吾的《双剑誃易经新证》是民国易学的代表成果。书中运用新材料、新方法,对《周易》文辞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解释,以求证古义。由新近出土易学文献资料,比对研究,可确证于省吾的部分新释,但其更多新解却得不到新资料的支持。除新注释外,于省吾承继传统经学的情怀,认可“观象系辞”的作《易》观点,而致力于寻找易象、阐明易辞;但在取象方法上,其对传统易学有所分判,对虞氏易等有所批评,而主张仅由本卦中取象。《双剑誃易经新证》与民国易学整体风貌一样,内蕴变革时代的学术品格,内容有新有旧,成果有得有失。
关键词
《双剑誃易经新证》;于省吾;本象;出土文献;民国易学
《双剑誃易经新证》(以下简称“《易经新证》”)是于省吾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是其继《尚书新证》《诗经新证》之后的又一部以出土甲骨文、金文资料,考证先秦典籍古义的著作。《易经新证》在民国期间多次出版、影响颇大,是近代《周易》新注释、乃至民国易学的代表成果。
一、由出土易学文献再议于氏新释
于省吾是由古文字学,而进入易学、进行《周易》新注释的。文字训诂自古是注《易》的基础、解经的手段,于省吾认为,除却工具价值外,古文字形与《周易》还有更深刻的联系:
作《易》者之取象,不本于当时之器物,则本于当时之文字。
汉字的创造,许慎总结有“六书”之说,其中的基础是象形字。于省吾认为汉字的创造与作《易》的时代相近,圣人作《易》,既直接仰观俯察物象,又间接取法于文字之象形。由此,于省吾常以古文字形比附易卦,而阐发新释。如其释:“古丘字象外高中空之形,甲骨文丘作,卦象惟震象与此同,其余皆不类,乃逸象也。”按甲骨文“丘”字,似高地底部相连而中上部断开,其形确实与震卦相似,据此于省吾称“卦画与古文字密合无间”(《新证》卷二,第108页)。再如,损卦䷨六五、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的“朋”字,于省吾考甲骨文作、金文作,与损卦六三至上九、益卦六二至九五的䷳(大艮)卦画相似,故而于氏再次确认:“卦画每与古文字或器物之象,密合无间,今验之而益信。”(《新证》卷三,第146-147页)字形与卦画的比附,有悠久的传统,《易纬·乾凿度》便认为八卦卦画为古文天、地、风、山、水、火、雷、泽诸字,后世更由此发展为汉字起源的假说之一。质言之,于省吾由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字形,衔接易辞与卦画,而阐释了一些卦爻辞。
于省吾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其收藏、掌握有大量新材料,且熟稔古文字学的新方法,以此为基础对《周易》所进行的注解,正如其书名“新证”之义,多为古来未见的创新。于氏的这些“新证”,尚秉和认为“皆信而有征,私谓其义不可易也”(《新证·序》,第2-3页),当代学者也多有好评。当前对于《周易》的注解,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利的资源就是马王堆帛书、上博简竹书、阜阳汉简等出土《周易》文本,以及王家台秦简《归藏》、清华简《筮法》等相关资料。对于上世纪于省吾先生的“新证”,我们应该站在新材料的基础上,重新予以探讨、评价。
于省吾的“新证”,部分在出土易学文献中得到了佐证。如讼卦卦辞“有孚窒惕”,于省吾以“窒惕”为“至易”,至训为甚,易为难易之易(《新证》卷二,第56-57页)。按“窒惕”帛书作“洫宁”,“窒惕”依照文字本义是趋向于凶吝的状态,而帛书作“洫宁”是趋向于吉的状态;而“至易”与“洫宁”,则吉凶意义相近。另外,小畜六四“惕出”,阜阳汉简作“易出”,也是以“易”代“惕”;而今本《周易》中的几处“惕”字,帛书、竹书中均不作原字。由出土文献的情况,可佐证于省吾的新释是有道理的。再如,兑卦九五“孚于剥,有厉”,于省吾释“剥”为“仆”。按帛书、竹书此爻缺失,而传世《归藏》卦名中“剥”作“仆”,阜阳汉简剥卦残存三处爻辞中的“剥”均作“仆”,清华简《别卦》中“剥”亦作“仆”,可见于省吾“剥仆古字通”(《新证》卷三,第171页)的论断是信实有征的。
对传世《归藏》真伪的辨明,是于省吾先生的经典论断。其引《西溪易说》中《归藏》卦名与《周易》卦名对应考证,进而论及传世《归藏》的真伪:“今观其遗辞,颇为古质。《汉志》失载,然《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均曾引之,后人多斥为伪妄之书,误矣。《西溪易说》所引六十卦名,多存古义古字,证之于古籀文,亦多吻合。虽非殷代之书,然亦非秦汉之后人所伪托。断可识也!”(《新证》卷二,第45-46页)按传世《归藏》历代多斥为伪书,直到1993年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学者始重视《归藏》;另外,出土帛书、竹书《周易》中卦名的写法,许多也与《归藏》有关。而近年清华简《筮法》《别卦》出土,其中坤、坎等卦名与《归藏》接近,且只在《归藏》中出现,因而学者再次确认《归藏》一书不伪。于省吾先生于民国时期,无以上出土易类文献的证据,而据自己的古文研究,推断传世《归藏》“非秦汉之后人所伪托,断可识也”,可谓真知卓见!然而,也应指出的是,于省吾在具体卦名的对应考证上,有一些是错误的。如其考证,《归藏》中犖为姤、钦为坎。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归藏·犖》:“朱震曰坎。李过曰:谓坎为犖,犖者劳也,以万物劳乎坎也。黄宗炎曰:坎为劳卦,故从勞谐声,而省物莫劳于牛,故从牛。”均以“犖”为“坎”。按出土文献,王家台秦简《归藏》中坎卦写作勞;清华简《筮法》中坎卦作犖,而“勞”“犖”相假。可见于省吾此处的卦名考证是错误的。
于氏大部分“新证”得不到当前出土文献的支持。例言之,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于省吾以“直”为“值”、“习”为“袭”,改爻辞为“值方大,不袭无不利”;释“方”为方国,爻辞释为“当方国盛大之时,不侵袭之,固无所不利也”(《新证》卷二,第47-48页)。按帛书爻辞作“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与今本无异;帛书《易传》中《二厽子》《缪和》引释此爻,文辞也与今本无异。更《缪和》云:“子曰:’直方者,知之胃也。不习者,□[□]不安者之[胃]也。无不利者,无过之胃也。夫羸德以与人遇,则失人和矣;非人之所习也,则近害矣。’”“直”与“习”,显然是就本字之义解说,而与“值”“袭”无关。阜阳汉简《周易》残存“不习无”三字,也是用“习”本字。可见出土易学文献中并无于氏此爻新证之义。再如,随卦初九“官有渝”,于省吾释为“观有渝”,改“官”为“观”。按帛书、竹书、阜阳汉简《周易》中“官”均作本字;更帛书为“官或谕”,《说文》“谕,告也”,“谕”有晓谕人之义,正与“官”的职责相关。可见,于氏改“官”为“观”,与出土易学文献不符。如此之类,所在尤多。
近现代《周易》新释与出土易学文献不符的情况,在于省吾同时代的郭沫若、高亨等诸先生的研究中也多有体现。因此,这些新注释往往不被当下学者所认可。以于省吾为例,反思新释的失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改字释义太过随意,失训诂严谨之原则。于省吾言:“古书滞义,如得其解,固文从字顺也。”(《新证》卷二,第89页)可见“文从字顺”是其新解的确立标准。但问题是,于省吾最喜用通假,由字形、声音的相近,一个字往往能通假到数个、数十字不止,其中自然可能有“文从字顺”的情况,而被于氏定为新释,但如此是否合于文辞本义则未可知。古人解经,最忌改字,于省吾的新释,正是失之随意,而不顾注释谨严的传统。其二,对历代易学家既有的训释不够重视。易学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且有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古人注经,多有所传承,而大体不离易学的话语。近代易学往往弃固有研究不用,不重古人训释,则必然有脱离易学话语的危险。其三,古文字学在近现代仍很不完备。受西学与近代考古学等影响,20世纪的古文字学从小学中独立出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于省吾时代,古文字学尚不完备,如其时上古音的音系研究较粗糙,因而于氏注《易》使用的很多声音通假,在今天看来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二、于省吾象数易学发凡
于省吾虽然与高亨同为《周易》新注的代表,但两者区别甚大,于省吾是精研象数的,甚至按传统划分,于氏易学属于典型象数易学。于省吾承继汉代易学观,其言:“《易》,象学也。”(《新证·序》第5页)“《易》无象外之辞。”(《新证》卷三,第166页)《周易》是关于象的学问,《周易》中没有脱离象而独立存在的文辞。显然,与汉儒一样,于省吾认同“观象系辞”,认为圣人由象而作《易》。既然“《易》无象外之辞”,那么在注释易辞的时候,就必须要为每个字找到对应的象,以明圣人作《易》之旨。于省吾云:“卦爻之词,皆本于象,不知其象之所出,则不知其词之所本。是故读《易》者必求其象,象明而词义始了无隔阂矣。”(《新证》卷一,第23页)于省吾在《易经新证》中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其取象解《易》的原则。如其释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以下卦坤取象为“康”、为“用”、为“马”,以二、三、四爻互艮卦取象为“锡”,以上卦离取象为“日”,以三、四、五爻互坎卦取象为“三”,又以艮取象为“接”。由此,于省吾将晋卦䷢卦辞落实到了卦象中,而确认了其主张:“然则’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实无一字不由象生。《易》无象外之辞,其信然乎。”(《新证》卷三,第134页)站在象数易学的立场,于省吾批评汉代之后的义理易学:“汉以后之说《易》者,多扫实象,而演空理。盖《易》义之不彰,由来尚矣。”(《新证·序》第5页)于省吾认为没有取象基础的义理,是没有实质内涵的“空理”,自王弼扫象,《易》之真义就不复彰显了。所谓义理易学,《四库全书总目》称王弼“说以老庄”、程颐“阐明儒理”,是义理易学的主要代表。而于省吾对于王弼、程颐严辞抨击:“王辅嗣局促于乘承比应之中,程伊川缘饰于虚疏寡要之际,而易学亡矣。”(《新证·序》,第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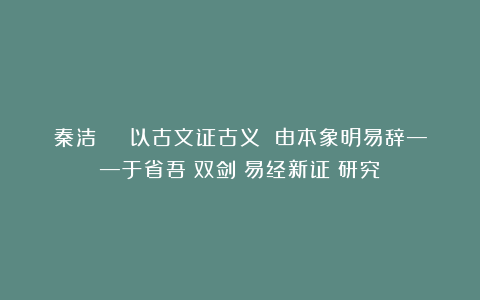
在易学观与注《易》原则上,于省吾完全沿袭了传统象数易学。但在具体求象的方法上,于省吾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其对传统家法有所分判、选择,对象数易学前辈多有批评,统观《新证》,于氏批评了虞翻、来知德、惠栋、张惠言、焦循、端木国瑚、姚配中、俞樾、杭辛斋等一众学者。于省吾对于虞翻的批评最多。其言:“虞氏往往以之变为言,殊不可据。”(《新证》卷二,第124页)按“之”即“之正”,是虞氏的主要易例之一,易卦六爻的位置有阴阳之分,奇数初、三、五为阳位,偶数的二、四、上为阴位;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是得位,否则就是失位;对于失位的各爻,虞翻认为他们应变化阴阳属性,成得位的状态,而所有的卦最终都成既济:这就是虞翻“成既济定”的“之正”说。例言之,鼎卦九四爻,于省吾云“虞翻……以四变为震,非也。”(《新证》卷三,第162页)“以四变为震”,即鼎卦䷱九四为阳爻居阴位,不正,变为阴爻“之正”,卦画成蛊䷑,则三四五爻可互震卦。于省吾反对虞翻的这种卦爻变化。除“之正”外,其他诸如“卦变”“旁通”等虞氏易例,也受到了于省吾的批评。按“卦变”是讲卦的生成,离卦虞翻释“坤二五之乾”,通过乾九二、九五与坤六五、六二之间的卦爻交易,而生成离卦。对此,于省吾批评:“虞氏以乾坤之变为说,非是。离卦意象具足,无须以之变为言也。虞氏诂《易》,好以之变迁就己说,不可为训。”(《新证》卷二,第126页)所谓“旁通”,即六爻阴阳完全相反的两卦,为旁通卦,如虞翻释离卦“与坎旁通”,因而虞氏常取坎卦之象来释离。对此,于省吾批评:“虞氏谓出离为坎……非经旨。”(《新证》卷二,第125页)于省吾对其他象数易学家的批评,与虞翻相似,不再赘述。
于省吾对象数易学家的这些批评,正能体现出其象数主张的独特之处。要而言之,就是摒弃一切由他卦释本卦的易例,而务求从本卦中取象,要“求诸本象”。其言:“自来解’舆说輹’者,皆以之变或对象为言,皆求诸本象而不得其解者也。”(《新证》卷二,第63页)于省吾认为,之所以历代学者会使用“之变”等易例,不过是因为在本卦中找不到需要的卦象而已。正如王弼所谓:“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
由象数易学注《易》的基本逻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求诸本象”。按象数易学家注《易》,往往据本卦或变动相关的他卦卦象,而得到八卦之象,再由八卦所取物象,直接或间接得出《周易》的文辞。也就是说,通过八卦的中介,实现卦画与卦爻辞之间的对应。如虞翻释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的“日”字,云“二变成离,离为日”,所谓“二变成离”,是二爻“之正”,下卦成离卦;引《说卦》“离为日”,是由八卦取象以对应文辞。此注《易》逻辑为:六十四卦—八卦—物象(卦爻辞)。所谓“取象”,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六十四卦卦象中取八卦之象,二是用八卦取具体物象。传统易学在这两个方面都颇为用力。为取八卦之象,在本卦中使用互卦、半象等易例;又通过卦变、之正、旁通等,过渡到他卦中取八卦之象。为取具体物象,在《说卦传》的基础上,不断使用新的八卦取象,这些超出《说卦》的取象名为“逸象”,包括孟氏逸象、九家逸象等等。
由象数易学的取象逻辑来看,于省吾所批评的是在“六十四卦—八卦”这一环节中,不从本卦取八卦之象的做法,上文所引对虞氏“之正”“卦变”“旁通”等批评即是此类。于氏主张“求诸本象”而得八卦之象,其所沿用的易例有互卦、半象、大象、覆象等。互卦即在六画卦中,取中间相邻的三爻得出八卦之象;取相邻的四爻或五爻,重叠中间部分,得出六画卦。如于省吾释大过䷛,云“中互乾为大”(《新证》卷二,第80页),就是使用互卦。半象即六画卦中的相邻两爻,在其上下加阴阳爻,可得不同八卦之象。如相邻两爻为,则可以取为☲、☳、☵、☱四种八卦之象。于省吾释归妹卦䷵,以四、五两爻为兑卦(《新证》卷二,第70页),正是用“半象”。而六十四卦中,若有四画、五画、六画的形象,与八卦之象相似,则称为“大象”。其用六画大象:“夬之为大兑象也,犹剥之为大艮,颐之为大离,大过之为大坎,其象一也。”(《新证》卷二,第70页)五画大象,如其释大壮:“初至五为大兑象。”(《新证》卷二,第131页)四画大象,如其释大畜䷙:“三至上为大离。”(《新证》卷二,第80页)所谓覆象,即卦画颠倒之后的卦象,八卦中震与艮、兑与巽互为覆卦。如旅卦䷷中,三四五爻互巽,于氏称“覆兑”(《新证》卷二,第70页);坎卦䷜中,三四五爻互艮,其称“覆震”(《新证》卷二,第122页)。
于省吾不用“卦变”“之正”“旁通”等易例,而只从本卦取八卦之象,显然弱化了“六十四卦—八卦”这一环节。那么为取得足够的物象,其必然要加强“八卦—物象”的对应。因此,于省吾广泛使用《左》《国》逸象、孟氏逸象、九家逸象、《易林》逸象等。如取孟氏逸象,震为主、巽为妻(《新证》卷三,第166页)等;取九家逸象,震为玉(《新证》卷二,第51页)等;取《易林》逸象,震为神、兑为鲁(《新证》卷三,第158页)等。他还使用古文字形与古代器物形象,发明逸象,这是其独特之处。由古文字的象形,所使用“古文字逸象”,上文已述。由古代器物形象,使用“象形逸象”,如于省吾赞同毛奇龄等所论,认为鼎卦与鼎的器形正相似(《新证》卷三,第160-161页);再如,其认为“近世出土古玉玦,形如环,其中断处有口甚微”,与兑卦相似,故以兑取玦象(《新证》卷二,第70页)。
如前所述,于省吾认同“观象系辞”的作《易》观点,认同取象释辞的研《易》理念;其象数研究中,使用《说卦》取象,使用先秦至两汉各家“逸象”,亦使用所发明之古文字与古器物逸象。于氏自信其取象所释,完全符合《周易》的本来面貌。按于氏所论,由重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现代学术标准来看,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卦爻辞之作,绝不可能如于氏所释般取象。如于氏所用古文字、古器物逸象,其本质是卦画与字形或器形之相似,由象形而比附取象。但卦爻符号之形状,古今有巨大变化。从《易》类出土文献看,爻画是以数字书写、由多个数字逐渐归约为代指阴阳的一(七)、六,卦形与今本卦画差异较大。卦画本身古今不同,则所谓象形之取象,自然难以成立。由此例,于氏取象,乃至汉易象数,显然不是准确客观的作《易》之历史事实,与《周易》本来面貌有相当距离。
当然,不合于“本义”,也不意味着于氏取象没有“诠释”的合理性。从经文到传文,再到汉易,象数之学不停地以卦爻符号来分类取象万事万物,以万事万物归类表征于卦爻符号,在两者的融通中丰富易学、解释世界。易卦与事物的融通,是在不断扩展、调整与完善之过程中的。如坎离水火之取象,今本《易传》以坎取水、以离取火;但清华简《筮法》中以坎取火、以离取水。以八卦阴阳属性来看,坎为阳卦,离为阴卦;水火相对而言,火为阳,水为阴;则《筮法》中坎火离水有一定的合理性。今本《易传》与清华简《筮法》的差异,足证象数之学,从先秦到两汉是在不断调整中的。期间,淘汰掉一些象数观点,也最终形成了许多流行至今的经典象数解释。从诠释的角度看,于省吾先生的象数主张,融合其所见之新材料,甄选传统象数资源,又发明新的象数内容,对易学的当代诠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范式意义值得肯定。然而,真正的问题与困难是:当代的思想、学术、生活与传统割裂严重,现代象数之诠释,能不能再次得到人们的认可?能不能对当代生活有所贡献?就此角度而言,于氏象数研究、乃至近现代象数易学,距离形成当代象数易学的经典诠释,仍有很长的距离。
三、《易经新证》与民国易学
于省吾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易学研究,深受民国时期学风的影响,而其《易经新证》也是民国易学的代表著作之一。因而,有必要在整体民国易学的视域下,认识、评价于省吾先生的成果。
民国是易学的转型时期,此时代的易学研究,至约而言,有两大进路:一者是“以旧纳新”,延续经学传统为主体、而吸纳时代新知识。此一路直接承继清代的汉学传统,因此清末民初有徐昂、曹元弼、沈祖绵等专治汉代象数易学。而受时代风气影响,开明学者往往能由经学承接新义,乃至开出新的研究范式,如杭辛斋、章太炎、刘师培俱为此列。此一路到马一浮、熊十力等,虽仍本于旧学而开新,但已然是理路精致的另一番风貌。另一进路是“以新释旧”,主要受西方分科体系的影响,以不同学科范式,重新研究作为旧经籍的《周易》。取消经学学科后,易学被划入哲学门类,故有以哲学研究易学者,诸如冯友兰、朱谦之、金景芳等;随着史学革命,“六经皆史料”更新经史关系,故有以史学研究易学者,诸如古史辨诸君、郭沫若、胡朴安等;近代以来,科学声誉日隆,易学因此用来比附科学,而有致力于科学易诸学者;随着考古学的建立,古文字学的发展,而有新释《周易》的诸研究,于省吾《易经新证》即在此列。
除由古文字学的方法,对新材料、新方法的使用外,《易经新证》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近代学术新色彩。如受近代史学风气与经传分离说影响,于省吾对《易传》颇有质疑。例言之,其释蛊卦:“有子考即有子孝……《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是读考如字。余于《象传》,尤不尽信,此一征也。”(《新证》卷二,第102页)于省吾认为“考”为“孝”,而《象传》解释为“考”,因此对《象传》“尤不尽信”。再如晋初六“罔孚裕无咎”,于省吾释:“《象传》:’裕无咎,未受命也。’是读作’罔孚’句,’裕无咎’句。非是。应读作’罔孚裕’句,’无咎’句。”(《新证》卷三,第134页)对《象传》的句读提出了质疑。除《象传》外,于省吾对《说卦传》等也提出了质疑。如其云:“按《说卦》’乾为首’’震为足’’坎为下首’……实不尽然。《易》言首、言角、言顶,谓卦之上也;言趾、言足、言尾,谓卦之初也。非取义于八大象而为言也。”(《新证》卷一,第42页)认为“首”“足”“下首”等,是由爻位的上下而取的象,并非《说卦传》所云由八卦取象。除疑传外,于省吾还在易辞的考释中,使用出土材料,发现古史故事,这显然受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影响。如于省吾考证“利用为依迁国”,其以“依”通假为“殷”,而认为这是周成王时的故事,是迁殷商的余裔为宋国,而封康叔在殷墟之地。(《新证》卷三,第147-148页)
于省吾易学研究中的这些新色彩、新材料、新方法、新结论,其目标是要恢复易辞的古义,剥离后世的错误、附会之义。在这个层面上,虽然其具体方法与结论有失误,但参考新材料、回到经文本身的研究理路,无疑是当代开出《周易》新注的必由之路。
于省吾“由本象明易辞”的象数理路,同样受近代崇尚逻辑理性学风之影响。按梁启超评价清人焦循的易学:“我对于里堂有些不满的,是嫌他太骛于旁象而忽略本象。’旁通’’相错’等是各卦各爻相互变化孳衍出来的义理,是第二步义理;本卦本爻各自有其义理,是第一步义理。里堂专讲第二步,把第一步几乎完全抛弃,未免喧宾夺主了。”“旁通”与“相错”,是焦循在汉易基础上自创的象数体例,与汉易“之正”“卦变”等相似,都是寻求本卦与其他卦之间的联系,是“旁象”而非“本象”。观一卦,重心不在此卦的“本象”,而孜孜索求“旁象”,与近代理性逻辑之立场,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故而梁氏批评焦循讲“第二步”之“旁象”,不讲“第一步”之“本象”,是“喧宾夺主”。于省吾对虞翻等象数易学的批评,与梁启超之于焦循的批评,显然是高度一致的。
民国易学“以新释旧”的理路,虽然整体是新易学的面貌,但以于省吾为例,亦可看到学术转型中的新旧激荡。在易学观上,于省吾先生深受经学传统的影响。如前文所述,虽然对传统象数易例有所批评,但对于“观象系辞”的作《易》认识、对于由象释辞的解《易》方法,于省吾彻彻底底地继承了汉代易学的观点。申言之,于省吾先生是有经学情怀的,他对新材料、新方法的使用,其目的不仅是要得出新结论、考释通顺卦爻辞,其更根本的是要贯通易象与易辞、揭示作《易》的本来面貌。而这正是象数易学千年未变的学术目标。有趣的是,于省吾由古文字字形、布局等比附论证了半象、大象与覆象的合法性,正可体现出其新旧交融的学术品格。于省吾发现,甲骨文、金文中,组成字形的各部首往往没有数量的限制,不管多少都是同一个字;这正与象数中半象、大象类似。同时,文字的书写也没有反正倒立的限制;这正与覆象的原理相同。(《新证》卷一,第18-27页)对甲骨文、金文材料的研究使用,是新学的视野;而所论证的半象、大象、覆象,则是旧学的范畴。
就于省吾先生“新证”的得失来说,上文已有论及,其结论能够得到出土易学资料支持的是少部分。由此原因,于省吾的易学研究在当今学界影响有限。然而,于省吾先生易学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具体字辞的训释,而在于其研究的范式价值。新学的手段、时代的风气,对“新”的关切是易学前进的动力;经学的情怀、传统的借鉴,对“旧”的关怀则是易学传承的根本。若缺少“新”的关切,则是与现实脱节、无时代影响的死学问;若缺少“旧”的关怀,则一定会成为无根无据、恣意妄言的假学问。实际上,自民国以来,这样的死学问与假学问都是存在的。质言之,有新有旧,有得有失。这是于省吾的易学,也正是其时代的易学。
文章来源
《周易研究》
2019年第1期
编 辑 | 陈涵杰
以生命点燃生命 以智慧点燃智慧
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