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吉(1280—1345),字梦符,号笙鹤翁,太原人,出身太原书香门第,却一生漂泊江湖,最终流寓杭州,元曲“清丽派”巨擘,与张可久并称“曲中双璧”。
他科举不第,混迹市井四十余载,自谓“江湖状元”,在瓦舍勾栏间以曲笔为刃,剖开时代病灶。
其作品多借山水、世情抒发对功名的淡漠与对世俗的洞察,风格清丽洒脱,又暗藏辛辣讽刺。
这三曲《山坡羊》,作于元末社会崩坏之际:
《寄兴》直刺世情浇薄,用阮籍“青白眼”之典化作匕首,戳破势利者嘴脸;
《冬日写怀》见富贵者“攒家私,宠花枝”的荒淫,预言其必自噬的终局;
《自警》以“安乐窝”为盾,抵御浊世唾沫,宣告“东西都在我”的清风白云间的精神宣言。
《山坡羊·寄兴》
鹏抟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
事间关,景阑珊,黄金不富英雄汉。
一片世情天地间。
白,也是眼;青,也是眼。
赏析:
鹏抟九万:典出《庄子・逍遥游》,象征超越凡俗的志向与力量。
腰缠十万,扬州鹤背:典出南朝《殷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故事里的人贪心不足,既想坐拥财富,又想身居高位,还想成仙得逍遥。
青白眼:典出《晋书·阮籍传》,“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嵇康携酒挟琴来访,“乃见青眼”。说阮籍以正眼待贤者,以侧视对俗人。
该曲起笔如鲲鹏击浪,借《庄子》凌云之志、《五灯会元》富贵迷梦,铺展理想宏图。
开篇便将世人追逐的“功名”、“富贵”、“逍遥”一网打尽。
可“事间关,景阑珊”陡然一转,豪情骤落。
纵有凌云壮志、千金财富,终究难逃世事波折、风光易逝的宿命。
“黄金不富英雄汉”一语刺破迷障:真正的英雄风骨,从不在金银堆砌的牢笼里,而在精神的丰盈与操守的坚定。
世人以“白眼”轻贱失意者,以“青眼”追捧得意人,天地间的世情本就如此凉薄。
天地如剧场,看客眼色翻覆,唯英雄以冷笑对峙。
《山坡羊·冬日写怀》
朝三暮四,昨非今是,痴儿不解荣枯事。
攒家私,宠花枝,黄金壮起荒淫志。
千百锭买张招状纸。
身,已至此;心,犹未死。
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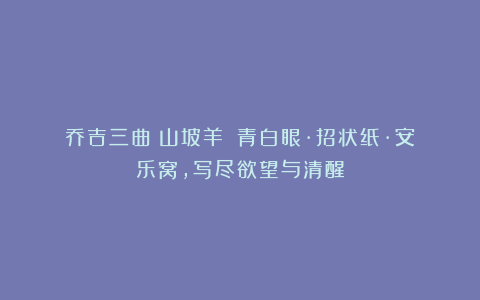
朝三暮四:典出《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故事中,养猴人用“早上三颗栗子、晚上四颗”还是“早上四颗、晚上三颗”来欺骗猴子,猴子只看表面数字却不知总量未变。
招状纸:指元代司法文书“招伏状”,犯人需签字画押认罪。
世人总在是非真假间摇摆,却连“荣枯自有定数”的简单道理都参不透。
“攒家私,宠花枝”,寥寥六字,绘尽追名逐利者的丑态,他们敛财不止,耽于声色,以黄金壮胆,实则养肥了“荒淫志”,直指金钱对人性的异化。
然而,费尽心力积攒的财富,最终不过成了给自己定罪的“招状”,讽刺名利场终究是“自作自受”的困局。
尾句“身已至此,心犹未死”如杜鹃啼血,在绝望中迸发抗争强音。
《山坡羊·自警》
清风闲坐,白云高卧,面皮不受时人唾。
乐跎跎,笑呵呵,看别人搭套项推沉磨。
盖下一枚安乐窝。
东,也在我;西,也在我。
赏析:
乐跎(tuó)跎:逍遥自在的样子,同“乐陶陶”。
搭套项推沉磨:佛经《法华经》以“驴驮重物,不知疲倦”来比喻无明众生;元杂剧《看钱奴》中有“推磨似驴走”。世人项套金锁链,自以为驭风雷,实则为欲望之驴。
安乐窝:源自北宋邵雍,他隐居洛阳,居所名为“安乐窝”,作《无名公传》说“寝止之所,名曰安乐窝”。
与前两首的刀光剑影迥异,此曲如云卷青空。
清风为席,白云作衾,“唾”字轻抛,便卸尽世俗枷锁。
不逐风不追云,只与清风为伴、白云为邻,何等自在。
坚守本心,不媚世俗,便不会落得被人唾弃的下场。
与《寄兴》的激愤不同,此曲以“乐跎跎”三字为枢机,完成从愤世到自适的哲学转身。
全篇如水墨长卷,留白处皆是超然物外的禅意,在元曲中独树一帜。
全曲无一句怨怼,却以通透的豁达与坚定的自守,为乱世中的文人立起一座精神灯塔,温暖而有力量。
乔吉这三首《山坡羊》,写透三重人生境界:
《寄兴》是壮年时的凌云壮志,以鲲鹏之姿叩问苍穹;
《冬日写怀》是中年后的冷峻批判,以手术刀解剖社会病灶;
《自警》则是暮年的圆融通透,在清风明月中寻得心灵栖居。
三首小令如三枚玉璧,映照出十四世纪中国文人在专制与困顿中,既有“黄金不富英雄汉”的铿锵,又有“乐跎跎,笑呵呵”的洒脱,在雅俗交融中完成对传统文人形象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