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关中平原的风还裹着残冬的凉意,陕西西咸新区摆旗寨村北塬的考古工地上,队员手中的小刷子轻轻拂过陶俑肩头的浮土,指尖突然触到后室棺椁旁两枚冰凉的圆片。
蹲下身细察,在场众人都屏住了呼吸——那是两枚边缘磨得发毛的金币,一枚正面是东罗马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半身像,右手紧攥长矛,背面胜利女神羽翼舒展;另一枚却透着古怪:皇帝像掌心托着十字架,背面带翼天使的体态比寻常金币上的更显健硕,既沾着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版型特征,又隐现查士丁尼一世的风格痕迹。这种“混版”金币,在此前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中,从未见过。
墓室全景
墓主人究竟是谁?为何能将罗马金币、波斯银币与西域玻璃器一并带入地下?待前室那方青石墓志被小心清理出来,答案才渐渐浮出水面。
那方墓志被千年潮气浸得泛着乌色,51厘米见方的石面上,769个楷书字带着隶书笔意,虽有斑驳却筋骨分明,清晰刻下墓主身份:“魏故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乐陵县开国子陆丑”。
更关键的信息藏在“其先鲜卑步陆孤氏”一句中——这绝非寻常姓氏,而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汉化改革的核心印记:当时孝文帝将穆、陆、贺、刘等八个鲜卑勋贵大姓改为汉姓,步陆孤氏便改姓为陆,还特意下旨“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让其与汉族崔、卢、李、郑等高门士族享有同等地位。墓主的鲜卑贵族血统,瞬间将人拽入北魏末年那片动荡的权力漩涡。
墓中出土的金币
墓志中关于家族的记载,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被尘封的鲜卑勋贵史:“河南烈公乞真之孙,怀朔镇都督伐莲之子”。
翻检《魏书・陆真传》,这段历史骤然清晰:“河南烈公乞真”,正是太武帝拓跋焘麾下赫赫有名的鲜卑将领陆真。
这位武将一生追随太武帝征战四方,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随征蠕蠕,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率军攻悬瓠、战滑台,后来又平定氐人仇傉檀叛乱,在长蛇镇筑城御敌,最终因功封河南公,死后谥“烈”,归葬京师洛阳。
而“伐莲”二字,经考证极可能是陆真之子陆延的鲜卑名音译——《魏书》载,陆延承袭父亲爵位后,长期驻守北境,曾任怀朔镇大将,都督沃野、武川、怀朔三镇军事。那片土地,正是后来六镇起义的核心之地;正光五年(524年),陆延死于秀容牧子叛乱,他的尸骨尚未寒透,六镇戍卒的烽火已烧遍北境大地。
棺外中部偏东出土的漆器
陆丑生于太和七年(483年),祖父陆真去世时他才9岁,虽曾沾过家族余荫,却未赶上鲜卑贵族最风光的年代。墓志记载,他直到孝昌二年(526年)才“解褐直后员外散骑侍郎”——这是个第七品的闲散官职,多用来安置无实权的贵族子弟,《魏书》中甚至有“(司马祖珍)年十五,举司州秀才,解褐员外散骑侍郎”的记载,足见此职对年少贵族的“宽容”。
44岁才得“解褐”入仕,对出身鲜卑八姓的陆丑来说,这哪是仕途起步的荣耀?倒更像家族光环褪色后,一份带着敷衍意味的安置,字里行间藏着难掩的无奈。
彼时的北魏,早已不是太武帝横扫北方的鼎盛模样。正光四年(523年),沃野镇戍卒破六韩拔陵摔碎酒碗,“昔高祖以六镇镇北,今我辈以六镇反北”的怒吼响彻北境,那些本应戍卫边疆的鲜卑健儿,因粮饷断绝、朝廷轻视,成了揭竿而起的“乱民”;而洛阳城里,胡太后却正斥巨资修建永宁寺,铜钟敲响时声震街巷,可北境传来的战马嘶鸣,早已像惊雷般越来越近。
棺外南端出土的圆形漆盘
陆丑在洛阳当值的那几年,恰是北魏皇权最脆弱的时刻。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带着契胡铁骑逼近洛阳城外,这位以“兵不厌诈”著称的酋长,以“祭天”为名,将两千余名朝臣诱至陶渚,一夜之间尽数屠戮,黄河水被染成暗红——这便是震惊天下的“河阴之变”。
那时的陆丑,正“出入墀陛,夙勤禁阁”,是孝庄帝元子攸身边的近侍,他亲眼看着皇帝被尔朱荣捏成傀儡,看着元子攸对着铜镜叹息“这冠冕之下,原是他人棋子”,也亲眼见证了无数鲜卑旧勋在刀光剑影中殒命。
可蹊跷的是,河阴之变中,多少鲜卑老臣前一日还在朝堂论政,次日便成了黄河浮尸,陆丑这位皇帝近侍却安然无恙。是他提前察觉杀机,躲入深宫避祸?还是祖父陆真留下的赫赫声望,让尔朱荣的人在乱刀之中留了三分情面?墓志对此只字未提,这段刻意留白的往事,反倒成了最勾人的悬念。
墓中出土的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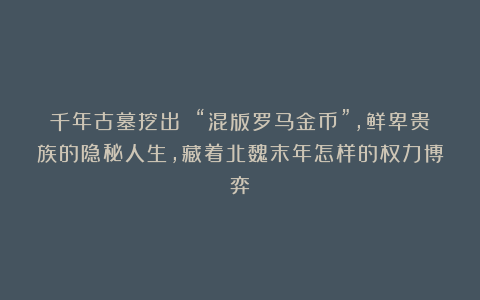
永熙二年(533年),陆丑的人生突然转向——他被外派为宁夷郡事。那处今属陕西礼泉的地方,在北魏时还只是个小县,直到西魏初年才勉强改县为郡。
按北魏官制,上县令不过第六品,中县令为第七品,而陆丑此前担任的员外散骑侍郎已是第七品,这次外派看似平调,实则是明升暗降的“左迁”。
好好的洛阳中枢待不住,是他早已察觉高欢与宇文泰之间的裂痕,刻意躲去关中避祸?还是不愿卷入尔朱氏内部的权力争斗,被排挤离京?
这疑问尚未解开,永熙三年(534年)的巨变便席卷而来——高欢从晋阳起兵,洛阳城“朝廷榛梗,有北顾之忧”,孝武帝元修带着少数亲信西奔关中,投奔宇文泰。
而陆丑,恰好正在关中的宁夷郡任上。这场看似偶然的“巧合”,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孝武帝抵达关中后,见到这位昔日的洛阳近侍,当即拜其为冠军将军、中散大夫——虽仍是无实权的散官,却让陆丑稳稳踩上了西魏政权的门槛。
谁也未曾料到,仅过了当年十二月,孝武帝便被宇文泰鸩杀,文帝元宝炬即位,陆丑的官职反倒一路攀升:大统元年(535年)加散骑常侍,得以出入中枢参与议事;大统二年(536年)封乐陵县开国子,获食邑三百户;大统三年(537年)任武卫将军,掌管皇宫禁卫,不久又迁征东将军,跻身西魏高级官员行列。
墓中出土的水晶坠饰
若对比同时代的西魏臣子,陆丑的升迁显得格外突兀——他既无宇文导、贺兰祥那样的关陇集团核心背景,也没有李弼、独孤信那样平定四方的军功,为何能在短时间内步步高升?
答案藏在宇文泰的政治考量中。西魏初立,宇文泰一面要对抗东魏高欢的军事压力,一面要弥合关陇本地豪强与鲜卑旧勋之间的裂痕。
陆丑的“鲜卑八姓”身份、步陆孤部落统帅的背景,正是他急需的“正统招牌”——抬出这位“洛阳旧臣”,既能向天下昭示西魏承袭北魏正统,又能拉拢散落在关中的鲜卑贵族群体。陆丑显然看清了这层利害,他选择彻底倒向关陇集团,用家族仅剩的声望,换来了晚年的荣宠。
墓中那些域外器物,或许正是他西魏时期地位的注脚。那枚绿色透明的玻璃器盖,表面布满相错分布的六边形磨面纹,是典型的西域工艺;萨珊波斯卑路斯一世银币,正面刻着两位祭司守护圣火坛的图像,虽有残碎,却仍能复原出钵罗婆字母书写的波斯文字——这些绝非普通贵族能轻易拥有的异域珍品。
那时的长安虽不复洛阳旧年繁华,却是宇文泰经营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西域商旅带着香料、玻璃、钱币穿梭其间。
陆丑或是参与了与西域部族的外交往来,或是获颁朝廷赏赐的异域宝物,才将这些见证丝路交流的物件纳入私藏,死后随葬地下,成了跨越千年的文明印记。
墓中出土的陶俑
大统四年(538年)四月,56岁的陆丑在长安永贵里的宅邸中去世。那片里坊聚居着张惇、宇文猛等多位北魏旧勋,是他晚年为数不多能寻得“同乡”慰藉的地方。
他最终被葬于雍州城西北廿里的平陵原——也就是如今的摆旗寨村北塬,距离西汉义陵仅2.5公里,与那些西汉帝王陵为邻,也算给了这位鲜卑贵族最后的体面。
当考古队员将那枚“混版”金币小心翼翼收入文物箱时,阳光正斜洒在墓坑之上,金币边缘的磨损痕迹在光下格外清晰,仿佛还留着陆丑生前反复摩挲的温度。
陶碓
陆丑的一生,没有祖父陆真横扫北境的赫赫战功,没有父亲陆延镇守边疆的壮烈,却像一叶在乱世洪流中漂泊的扁舟,凭着对时势的审度与家族仅剩的声望,在夹缝中寻得生存之地。
而这座古墓中的金币、玻璃器与墓志,更让我们看清:北魏末年的大历史,从来不只是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位高权贵的权谋博弈,更是无数像陆丑这样的“小人物”,用他们的挣扎与选择,共同织就了那段暗潮汹涌的岁月。
推荐个出游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