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怎么到中国?没人会觉得是件偶然小事。带着经卷和语言,穿过了沙漠,翻过天山,这宗教和它背后的文明悄悄在西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迹。1300年前,这与长安的市井喧嚣毫不相关,却深远得令人琢磨。浑身上下透着陌生的伊斯兰教一步步渗透、改变,不小心就撞上了盛极一时的佛教?这碰撞带来的结果,不是表面的宗教转换,有人只看见胜负,没人想着中间的缠斗。
汉、唐之间,有谁能想到后来伊斯兰教居然可以替代佛教?说这场变动只是因为商路交通,岂不是把复杂事当成了买卖?唐代,丝绸之路两头交易热火朝天,带着香气的乳香从阿拉伯逆风而来,茶叶杯里荡着波斯人的故事。公元七世纪中叶,第三任哈里发的使者,不动声色地走进长安,抬头瞧着天宝年间气象,讲起他的国度,讲到信仰。开口闭口都是“安拉”二字,那时中国人把这些人统称作“蕃客”或“胡人”,不曾细究他们夜里礼拜的方向,更关心他们带来的香料和故事。
混居在长安“蕃坊”,这些最早的穆斯林像洋人住在租界一样,隔着一条街,有点距离,又难免彼此打交道。唐朝末年,安史之乱没完没了,李唐王朝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大食”士兵,许诺他们战后可以安家。战争结束没多久,他们娶妻,落户,孩子的头发混了点“蕃”的色彩。可关于伊斯兰教,这会儿说到底还是个外来的新鲜玩意儿,中国百姓心里对它神秘疏远。长安的夜晚是不是就偶尔传出清真寺第一轮阿訇的颂经之音?没人记得太清楚。
很快进入宋元,局面又变。宋朝鼓励海外贸易,广州泉州广州等地成了异邦商人的新据点,南来的穆斯林在这里建寺安家,“五世蕃客”,听起来像极了小区里已经熟悉本地话的外国亲戚。宋王朝允许他们有公开的清真寺,有专门的墓地,那些异乡的习惯在沿海慢慢落地生根。到了元朝,情形又一变,蒙古的察合台汗国热衷皈依伊斯兰,甚至逼着整个汗国跟着改变宗教。于是推行新信仰成了国策,“不信伊斯兰要杀头,能背古兰经的免税!”这种高压,一下子把大量佛教世家直接推向了新教义。
有人觉得可惜,佛教不是在西域驻足过很久么?于阗那会儿,寺塔成排,僧人端坐,有的国王还自己打扫僧院。彼时,修佛寺像修路一样,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拜佛塔,小孩儿一睁眼就是大佛的脸。龟兹、于阗这些旧国名,和佛教太贴脸了。佛教兴盛时的繁华,偏偏也成了累赘:僧侣队伍庞大,劳力资源被消耗得一干二净,生产都干不动。百姓日子紧巴巴,心里时常冒出疑问:信仰还能解决温饱吗?伊斯兰教倒好,正赶上这个关口,摆出了“政教合一”的架势,教义仪式简单直接,跟吃饭睡觉一样渗进普通人生活。再看“政教分离”的西方,多少还要磨合,这里直接一体了。
但这些推行到底有多少自愿,又是被推着走的?这种夹杂着命令的宗教流变,在官方史书里不大愿多说,其中有多少人的故事被埋没了?对有些人来说,皈依只是一纸命令。可是,压迫之下的改变,我们应该怎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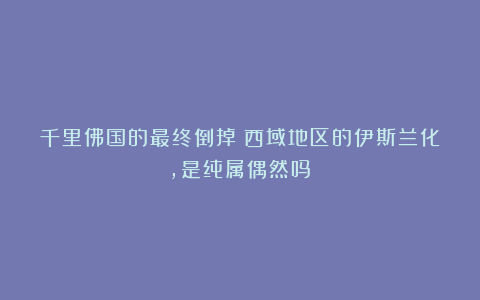
那些改教的人,背后挣扎得也不轻松。佛教土崩瓦解,不全怪新宗教势力,倒是寺庙里层层叠叠的教义,没法再打动已经习惯看实惠的百姓,神佛再高大,能解决吃穿不?随着权力转换,信仰也不得不换。明明口称心敬,却不知道往哪个方向磕头才有效。
伊斯兰教在西域变得主流,归根结底靠的不只是铁腕和法令,也有它自身裹挟来的文化包容。有人说它教义死板,真论起适应能力,偏偏比许多宗教都灵活。传进中国以后,伊斯兰教没拿自己那套道理生搬硬套,反倒像在老北京学了三年儒家,化起来有模有样。孝顺父母、夫妻和睦,弄了“五典”——这些词听着怎么这么像隔壁孔子讲德行?一转手,把“认主独一”同“太极无极”连起来,摆在书案上哪边都不尴尬。地藏菩萨保佑,真主也管万物起源,这一来,信仰变成了调和。
中国大一统的行政系统并不允许宗教翅膀太硬。伊斯兰教首领想搞个全国统一的教权组织,难得行得通。中央王朝宁愿看看地方上的阿訇在群众中讲几句道德经,说几句古兰经,安分就好。在这个夹层里,穆斯林成了体制内外的桥梁。明朝那阵,常遇春、胡大海这些大人物还都是虔诚信士。朱元璋气势汹汹把穆罕默德的故事让翰林院翻译,大清的皇帝甚至劝自家臣子“各安本俗”,没强求人家改旗易帜,倒也算宽厚。
不过,话说回来,大清的政策说宽容,其实也不过是“各自消停,不惹事”那个味道吧?控制手段上,还和其他宗教差不了太多。对宗教的态度在不同时间也摇摆,清前期还重用穆斯林上层,后期则随时防着有叛乱。皇家的大算盘,不外乎巩固统治,让基层社会别生乱。西域新修清真寺,汉文伊斯兰典籍不断问世,表面繁荣,背后政策随时可能有变化。
在新疆,伊斯兰化的速度和广度让人侧目,好像一夜之间,旧的佛国变成了新月皎洁的土地。但要说光是因为政权推行,故事未免太简单。地域本身自带游牧与农耕的混血气息,这种流动、本土与外来的边界早就朦胧了,伊斯兰教恰巧找到合适的落脚点,两种文明的特性擦出火花。忽然之间,改教、改俗、改习惯,大家就都接受了新秩序,有些地方连祭祀、悼念死者的方式都变了。穆斯林子孙穿白戴孝,不理发,三年中祭忌不断。孔子的规矩、伊斯兰的仪式,杂糅得自己都分不出哪条是先哪一条是后。
到底是信仰变了人,还是人自愿换了信仰?讲不清。信仰的成长,比想象的更复杂。明明官方支持下顺利发展,可实际在不同年代也会出现低谷。不知到底是谁改造了谁,各有各的本领。
现在看,西域变迁的路上,伊斯兰教能成“主菜”,既靠了自身的灵活适应,也少不了政策推波助澜。谁都说文化包容是一种力量,可逼着百姓改信这事儿,恐怕也没那么纯粹。是啊,历史就这样,理不干净。
最后说点实际的。无论宗教如何发展,融合的可能性总存在;伊斯兰教成了西域的“主流”,过程并不平顺,也没有标准答案。夹杂着权力、贸易、文化、风俗的更迭,每一步都有苦有甜,和预想的都不太一样,谁说结局非要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