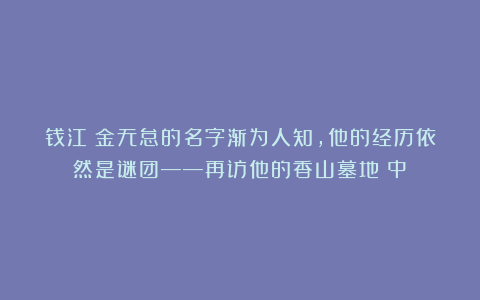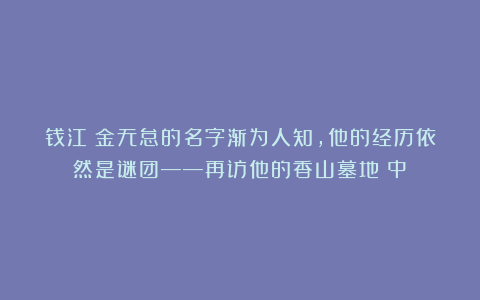|
本文原本编作“下篇”来结束。没想到情节反转,就在撰写的时候与金无怠后辈亲属有了联系。如果请他们来写出下篇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和金无怠的关系更直接,相关记述和数据更准确,更能满足人们知情的需要。
6年前,作者初访北京香山山麓金无怠墓,写出《金无怠:燕京人中超级谜团》一文,记述这位“超级间谍”的燕京大学同学对金无怠的回忆,以及坐落在北京香山玉皇顶的金无怠墓。
今秋香山红叶正浓,作者再度拜访,此文记述墓地变化及6年来对金无怠增加的些许了解。
金无怠的墓碑,包括他父母的墓碑依然如昨。6年前笔者在写文章时推测这两个墓碑看似同时竖立,现在知道这不准确。金无怠父母墓的年代要早一些,而且可能是金无怠墓碑所以安置在此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父亲相册里的照片,后排右1是金无怠。前排左起:沈明霞、徐元约、程佳因、金无怠夫人周谨予(脸部只拍了一半)。后排左起苏传绪、王恭立、金无怠。除了金无怠夫人,照片上的人物都是燕京大学20世纪1940-1945年期间的同学。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1982年左右,《世纪》杂志2019年首发,广泛传播,是笔者迄今所见金无怠在自由生活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们在下坡去买“贡品”时经过的村落,就叫“公主坟村”,与北京城内西三环路上的“公主坟”同名。可知“百果园”一带的大片果园,是由原先墓区逐渐发展起来的,百年来地形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金无怠墓前的樱桃树已经有些树龄了,果园门卫说,这里的樱桃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金无怠的墓碑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根据新的探寻所知,是在他辞世后一年,1987年清明前由亲属安放的。当时碑上的墓主姓名阴刻用深红色漆填勒,立碑时有以妻子周谨予名义献上的鲜花,花束垂下的飘带上写“吾夫无怠,永垂不朽!谨予泣血”字样。
20多年风雨将漆色剥蚀殆尽,碑上字迹已与碑身浑然一体。金无怠墓碑立于香山山麓30年后才比较地广为人知,似也表明在可述程度上,公众知晓能力的薄弱。
有一点现在比较清楚了,如今的金无怠墓所在,是当年这个入关家族的百年墓园。如今烈士墓碑立于此处,亦表示这位与谜团相伴一生的万里游子叶落归根。
金无怠墓北侧有一棵很有些树龄的松树,枝干有如虬龙伸张。
如果说我有几分幸运,就是6年前寻访到金无怠玉皇顶墓地以后,随即访问了他的燕京大学同学祝寿嵩、蔡公期、张澍智,记录了他们对金无怠的印象和所知,金无怠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的经历因此留下了文字记载。
到如今又是几度风雨,几位前辈:蔡公期已于2022年1月辞世,享年101岁。张澍智是2024年(也就是今年)3月2日去世的,享年也是101岁。就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上海传来消息,祝寿嵩前辈于2024年11月13日去世,享年102岁。
有一个细节,是访问张澍智前辈所知,当时她嘱咐暂不发表。如今6年过去,她已经辞世,那还是留下这一笔,增加一分对历史人物金无怠的了解。
这就是针对周谨予回忆录中所引金无怠写给她信中的几句话,说他在燕大读书期间专心学习,“不交女友”云云。张澍智认为,这是一笔带过的承接之语,姑漫读之。其实,金无怠在成都上学时追求过她的闺中密友胡睿思。
张澍智说,青春年代的男女大学生互相倾慕是正常的,他们虽然没有谈成,彼此的友谊是确定无疑的。虽然此后几十年没有联系,待“文革”结束实行对外开放,这时金无怠将到未到退休年龄,他们很快取得了联系。金无怠为胡睿思的子女到美国留学提供了很大帮助,胡睿思十分感激。
《金无怠:燕京人中超级谜团》一文发表6年来,经受了时光的检验。应该说总体上经受住的。遗憾的是其中仍有差错,主要在写到金无怠如何与党共中组织或情报机关建立联系这一点上,采用蔡公期作口述时他的推测。蔡老前辈认为有一种可能是,金无怠来到抗战中南迁成都的燕京大学继续学业期间,和同学陈麒章关系密切,而陈是中共资深党员……
文章发表后,陈麟章的夫人刘敦茀教授给蔡公期打来电话,说这个名字您记错了,金无怠的要好同学陈麟章不是党共中员。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联系的,就是陈麟章的哥哥陈麒章,他倒是很早就加入中共的。“麒章和麟章”在分别书写时容易搞混。
金无怠是否因为与陈氏兄弟这层关系与党共中组织或情报系统建立最初联系?刘敦茀教授并不知道。
我的差错在于,得知“陈麟章”这个名字后没有严谨考证。如果他曾任饶漱石的秘书,应该是可以考证出来的。
还要指出,即便说明了陈麒章、陈麟章名字的混淆,仍然不能确定金无怠投身“隐秘战线”是否通过这个途径。这一点,也是蔡公期前辈一再强调的。
这就是我对6年前的文章要做的修正。这样做,是为了朝着历史和人物真相更加接近一步。这一步要花费很多努力,却是值得和应该去做的。
很遗憾由于我文中的错记,给年高的刘教授增添了烦恼,我要感谢她的宽容!还要感谢蔡公期前辈,他在接到刘教授电话之后随即告诉我,还把错因揽到自己身上。
在笔者来说,撰写历史述实的时候出现差错会深感遗憾,因为落笔初衷是希望准确记述。出现差错会有一种没有尽责的失落。
出现了差错又怎么办呢?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加以更正加以说明,然后继续出发。
从金无怠墓向北走出数十米,果园开阔处有一块架起了三角布篷的露台,站在那里可以远眺北京城区。
言及当代史当代人物,对感到疑惑的地方,多一个问号、多一声询问,常常是迈前一步的阶梯。为寻求真相,去多看一份文献,多问一声,多打一个电话或是再发一个微信,难吗?看起来不难,真要步步走到,却也并非容易。
前面说到这里“百亩园”的门卫称,“带贡品”才能拜访金墓,其实是子虚乌有。一位学长告诉说,他和夫人几年前也去拜谒金墓,在门口被挡住。当时正值樱桃成熟季节,门卫要他们承诺购买采摘的樱桃才可以入内。学长夫妇一口答应,就进门了。出门时就有了一袋樱桃。
看来凡举“奇特规定”往往是门卫自定的。笔者经过询问加以印证了。
在百亩园附近向近处居民——当地农民打听金无怠的情况,包括墓地管理,都不容易有结果。笔者向山坡高处行走一路,询问路边闲坐的当地老人,几乎每一位都回答“不知道”。
我很想知道,《世纪》杂志刊登“谜团”一文后,对金无怠墓地的整修是什么时候做的?
虽然这里的人们都说“不知道”,但线索却是有可能在这里找到的。绕了好大的圈子,我得到了帮助终于知道,金无怠墓地在2020年秋天得到修葺,成为今天的样子。
6年过去了,对于金无怠的经历,笔者增加的了解只是一星半点。不知道人们还要等待多久才能知道他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
做历史研究,和当代事件与人物的距离要近一些。不过,距离近了,要写好写准倒也并非容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近前事物和人物有着更加强烈的去了解的需求,记述者需要面对更多的选择和寻求、推敲。
关于金无怠,作者惊诧的是,这个世界不大,这个谜团人物居然就是父亲在燕京大学同堂上课的同系同学。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父亲面前触及他的故事,结果失之交臂。倒是6年前抓住仅有的机会,写下了一些记录。
行文至此更可以感知,金无怠的意志力何等坚强。他几十年置身隐蔽战线,与战友和上级远隔万里,无时无刻不在万分警惕中生活。紧张和孤寂久久缠绕他,成功与喜悦不能和亲人分享,甚至共同生活24年的妻子丝毫没有察觉丈夫还承担另一种国家使命。
隐蔽战线是看不见的,却与高风险相伴。进入晚年的时候他暴露了,身陷囹圄。为了保全机密,或有种种考虑,他选择告别人生,抓住仅有的机会,用一个塑料袋、一根鞋带结束了自己的秘密使命,于是留下永远不会解开的谜团。
金无怠辞世至今,将及40年了;笔者对他燕京大学生活的记述,至今也有6年了。他的名字渐为人知,他的经历无人知晓。
人们依然关心他的使命和经历。如果要知道得更多,看来还需要时间,待到花开花落,待到往事变得很遥远很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