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佩特连科与柏林爱乐 马勒九
动手开始打字的这一刻就预感到今天要写很多东西,也预感到我的想法会比较杂乱,但由于想要写好的心情过于强烈,我争取不这么语无伦次。
究极忙碌的五月本不打算安排任何音乐会,但时隔八年上演的柏林爱乐马勒九,我不去一定会后悔,再加上来柏林之后还没有听过一次佩特连科,让我对这场产生了巨大的向往,和朋友提前两个小时站在音乐厅门口排队买站票,我买到了全场最后一张站票,陪朋友在场外蹲出票,临开演前十分钟蹲到了,苦尽甘来。
这场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主观情感相当强烈,看完到现在还在回想,想的不仅仅是演出。
第一乐章近结尾处,一段极美的小提首席领奏的旋律,我想起来最近偶然又读到的每个人在小时候都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前段时间读到时,写下了一些话:
最近也跟朋友分享了我对这首诗感动之处的看法,每次说到正是江南好风景这一句都会略显激动难以平复,很巧的是,佩特连科指挥棒下的柏林爱乐——我在马勒九里也听到了这样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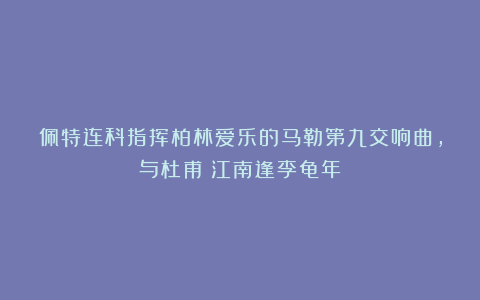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一边是西方古典交响乐的巅峰作之一,一边是中国唐代诗圣写下的七言绝句;一个用复杂的管弦乐写死亡,一个用短短二十八字描绘重逢。但就在今晚的音乐厅里,我站在柏林爱乐厅最高层的站票处,甚至看不见完整的舞台,身体的疲累在开演前即将把我掏空,可那一刻我感觉到,尽管有着如此之大的文化差异和东西方世界的间隔,但这两部作品分明在说着同一种语言——关于如何面对失去与即将失去,关于有一种苦痛与悲伤,是仍然允许万物如其所是。
马勒第九交响曲作为他人生中最后一部交响曲,被公认为是一部马勒对死亡的告别与沉思,这自然会引导我们期待听到其中偏向悲情与痛苦的部分。可佩特连科的演绎很克制,没有大开大合,听上去没有很多经典版本里的马勒九那么的强烈与厚重,那些充满挣扎的渐强,比如第三乐章Rondo-Burleske,佩特连科刻意压制爆发力,让音乐始终处于将破未破的临界状态,再比如将一些抒情段落处理得更加生动,让人时而忘记悲伤的底色。这种处理与杜甫的平静叙述也形成一种耦合,为什么苦痛不能藏在最朴素、平静甚至反之有些美好的表达里?当然可以,佩特连科似乎特别懂这一点,他的指挥让音乐始终保持距离,就像杜甫写诗时那种既在经历又像在旁观的状态,这也是诠释苦痛的一种方式,我不觉得这样的演绎就让这部艺术作品失去了其应有的对痛苦的深思,我反而热衷于听到不同指挥家手下不一样的诠释方式。
之前听欧丽娟老师讲《红楼梦》的课里,她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很深,关于人为什么要读经典,她说经典是一扇门,你读它,你走进去,把里面的人召唤出来,那个人不是经典的作者,你要召唤出来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今天在这场对我意义重大的音乐会里,我在佩特连科和柏林爱乐的合作中听到了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让我无比激动——把时间往前回溯,小学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杜甫的这首诗,那时我所认为的“好风景”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的好风景是草地,是阳光,是朋友间的玩乐,是无比具象化的童真。一周前,时隔多年再读到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我读到“正是江南好风景”这一句,感动之余也意识到,现在我理解的好风景不再像儿时那般童真,而是这风景真好,它好到豁达旷远,好到治愈人心,它甚至可能好到允许我们在这样的风景下面对别离。我在这首诗中把过往经历集合的我召唤出来了,而在今晚的马勒九里,当弦乐如薄雾般缓缓消散时,又把一周前读完这首诗感慨万分的那个我召唤出来了。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仅在于它能召唤出我自己,也因为它能让我在人生中的不同阶段,不断遇见新的我,不同的我。
所以何必纠结于佩特连科为什么没有像大多数版本一样更强调痛苦的演绎呢?马勒九的告别本就可以有千万种表现方式。可以呐喊,可以沉默,尽管底色是痛苦的,但也不影响美的存在,这是艺术作品里我渴望体会到的双重真实,杜甫是这样,马勒也是这样。在他生命最后的这部交响曲里,死亡不一定非要通过激烈的冲突来表现,第四乐章那些渐渐消失的弦乐,正如杜甫看着落花却仍然说着“风景正好”一般,弦乐彻底隐去了,佩特连科的双手还悬停在空中,音乐厅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真正的告别,是让消失本身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音乐会散场时,柏林下着小雨。我走在回去的路上,耳机里回放今晚音乐会的录音,我听着录音,马勒的风景、佩特连科的风景、杜甫的风景,还有我自己的风景,全都重叠在了一起。
2025.05.15
柏林爱乐厅
子易拉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