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卡蒙斯的诗句镌刻在欧陆西极的罗卡角,曾以为那已是天涯的绝响。
直到车轮碾过开普敦的晨霭,向南,再向南,直抵非洲大陆真正的终章——厄加勒斯角(Cape Agulhas),方知地理的尽头并非句点,而是感知破茧而生的起点。
武陵禅寺檐角的风铃,竟在此处天涯,与两洋的潮音共振。
破晓:朝霞如釉,心路启程
凌晨的N2公路,是泼向凡尘的一道金红釉彩。
车轮划破开普敦尚未散尽的夜色,东行。
车窗外,沉睡的葡萄园在熹微中舒展筋骨,成群的埃及雁在荒原投下悠长的剪影,偶有孤树如墨,点在无垠的草甸画卷上。
朝霞不是在天边,而是熔化了整个天际线,泼洒下来,将远山、低矮的农舍都镀上一层流动的暖金。
270公里的路途,竟似一场流动的禅坐。
发动机的嗡鸣与轮胎摩擦地面的节奏,意外地应和着记忆中武陵禅寺的木鱼清响。
师父的话语随晨风潜入:“感受是五蕴的浮沫,感知是理性的映照。”
此刻,飞逝的风景不正是这“浮沫”?而那颗试图穿透表象、触碰大地脉动的心,是否正悄然沉向“湖底”?
抵达:针角无声,界碑无界
当“Cape Agulhas”的路标出现,喧嚣彻底退潮。
与好望角的游人如织判若云泥,这里只有亘古的风,拍打着锈红色的嶙峋礁石,以及一座孤独守望的白塔。
最南端的界碑(南纬34°49’58″)静立礁岩之上,冰冷而坚实。
手指抚过碑上深刻的经纬度数字,那触感直抵心底。
旁边另一块石碑宣告:“此处,印度洋与大西洋相遇”(HERE THE INDIAN AND ATLANTIC OCEANS MEET)。
我凝视着脚下的海。
想象中的“分界线”在哪里?是想象中的泾渭分明?不,目光所及,唯有无垠的蓝,深浅交织,涛声合鸣。
海浪并非整齐划一地归属某一洋,它们在此处拥抱、缠绕、混沌交融,形成一片无法被标签切割的活水。
海鸟掠过,风带着咸腥穿过发隙。就在这无言的壮阔前,武陵禅寺的参究轰然落地,如醍醐灌顶!
感受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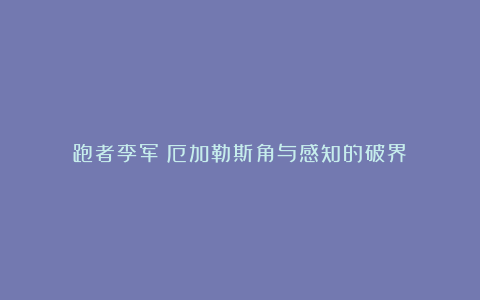
是界碑上冰冷的刻痕,是地图上那条虚拟的线,是头脑中“此为印度洋,彼为大西洋”的执着分别。
祂像一层透明的膜,将我与这浑然天成的海洋隔开。
而感知呢?
祂消融了这层膜。它不再辨认标签,不再执着名相。
祂是整个身心向这片无界之海的彻底敞开——是耳中涛声的雄浑与细碎,是皮肤承受风压的力度与温度,是眼中海水亿万种变幻的蓝,是心中升腾起的无边苍茫与敬畏。
大洋何曾需要分界?是人类认知的尺规,在自然的浩瀚面前,显得如此局促而徒劳。
感受是浪花,执着于形态与名目;感知是深海,容纳百川,无有分别。
陆地的终结处,大洋的交融点,不正是破除内 心一切疆界的最佳道场?
静观:荒原如镜,心海初生
坐在冰凉的礁石上,时间仿佛被海风稀释。
没有游客的喧哗,只有永恒的风声与浪涌。荒原向远方铺展,野草在劲风中伏倒又挺立,坚韧而沉默。
灯塔孤悬天涯,像一位历经沧桑的沉默智者。
这份原始、孤绝、未被“旅游滤镜”修饰的真实,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它不取悦感官,却深深震撼灵魂的本真。
此刻,卡蒙斯那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有了全新的、向内生长的诠释。地理的终结(“陆止于此”),恰恰是心灵感知的觉醒与无限延伸的起点(“心始于斯”)。
当外在的“最南端”标签被剥落,内在的“无南北”澄明便自然显现。
厄加勒斯角的风,像一把无形的拂尘,掸去了心头的尘埃与界限。最南端并非终点,而是一面映照“本来面目”的明镜——它照见感受的虚妄,照见证悟感知的辽阔无垠。
归途:灯塔如豆,心光不灭
踏上归程。回望厄加勒斯角,那灯塔如同心中亮起一点如豆的微光。
身体深处,印刻着那种沉甸甸的、带着海洋呼吸的印记。皮肤上似乎还残留着礁石的粗粝触感,耳畔依旧回响着两洋合奏的永恒交响。
270公里的归路,心绪已不同来时。那个被地图标记为“非洲最南端”的地理坐标,于我而言,已悄然转化为灵魂深处的一个“针角”(Agulhas 本意)。
祂精准地刺破了“感受”的泡沫,让“感知”的清泉如地下洋流般在生命深处汩汩涌动,深邃而宁静。
从此方知,真正的边界不在大洋交汇处,而在人心分别念生起的地方。破除它,即是彼岸。
厄加勒斯角,这个少为人知的“针角”,以其无言的礁石、混沌的洋流与亘古的荒原,为我上了一堂无声而深刻的禅修课。
祂让我亲证了武陵禅寺中听闻的道理:当“感受”的浪花止息于觉知的岸边,“感知”的海洋便无边展开,无有涯际,亦无分界。
此地,陆确已尽,海确已始,而心,亦于此破界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