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潘祖荫拥有多重身份,本文揭示其作为受印人的一面,涉及动机、回报、钤印方式、印章的细化专门化等诸多问题。
关键词:晚清 潘祖荫 受印 回报 钤盖方式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江苏吴县人。清咸丰二年(1852)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至工部、刑部、礼部、兵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以疾卒于任,赠太子太傅,谥“文勤”。善诗文、书法,好藏书、刻书,尤喜金石文字。
潘祖荫拥有多重身份,高级官员、文学家、收藏家、书法家等。作为后两者,就需要使用大量的印章,这是融入个人理念、凸显个性化之重要手段。
一、缘起与动机
当得到某一重要的珍贵的收藏品,或是特殊的礼遇包括御赐书画,便会请人刻治印章,用来纪念人生的荣耀时刻,把这动态的时刻用物质化的方式固化下来。同治九年潘祖荫获得宋本《金石录》残卷,极为惊喜,遂属赵之谦(1829-1884)刻“金石录十卷人家”朱文竖长方印记之。《潘祖荫日记》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提到“皇太后赏御笔画兰四幅”,三十日有“函致益甫,交捷峰”1之语,具体请托撝叔事项:“撝叔仁兄大人阁下:久不得书,甚念甚念。惟升祺日茂为颂。兹有万不能不奉求之事,务求俯允者:弟四月廿八,蒙皇太后赐画兰四幅。人皆不得,弟独得之,此乃异数,千载难逢。虽惶恐万状,而不能不求兄大人书一扁曰《赐兰堂》(篆)、一石章曰’赐兰堂’。务祈允之,幸勿却之,且祈早赐为荷(愈速愈妙)。数十年至好,当不见却也。千乞千乞,叩头叩头。敬颂升安。弟荫顿首,四月卅日。” 2【图1】可见潘氏请托的诚恳与迫切,想把这巨大的荣耀具体到匾额与印章等载体上,这才专门致信赵撝叔恳请速为之。撝叔“赐兰堂”印边款:“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此为潘大司寇纪皇太后特颁天藻,以志殊荣,敬勒斯石。”潘祖荫极为重视此事,赵撝叔在刻时亦是以极为庄重恭敬的心态小心为之,这在撝叔是大破例之事。“赐兰堂”除了赵撝叔所刻外,目前至少还可见其他三方同样内容印章,钤在光绪八年日记封底:“赐兰堂”白文竖方大印,盖在右上方,印文一行排列,笔画遒劲厚实,布局妥帖安稳。其下为一较小同内容白文方印,两侧有纹样,不过非龙形(视之为抽象龙形也未尝不可),因为空间逼仄,“兰”字篆法极为特别。右下则钤“赐兰堂”朱文竖方印,笔画同样厚实,章法紧密。三印应为同一人所刻【图2】。多次通过印章表现同一内容,可见潘祖荫对慈禧太后御赐兰画是多么重视且感到无上欣喜与荣耀。
此外尚有“御赐岁岁平安”“御赐松竹并茂”“御赐延年益寿”“御赐六松仙馆”等“御赐”开头竖长方印多枚,做法与“赐兰堂”类似。
二、受印与回报
潘祖荫求索印章最多之人可能就是赵之谦。撝叔为潘祖荫刻有“汉学居”白文方印、“祖荫”朱文连珠印、“伯寅藏书”朱文方印、“郑盦”白文方印朱文方印各一方、“面城堂”朱文方印、“如愿”白文方印、朱文竖长方印朱文椭圆印各一方、“攀古楼”朱文竖长方印、“吴潘祖荫章”白文方印、“滂喜斋”朱文方印、“八求精舍”朱文方印、“伯寅经眼”朱文方印、“吴县潘伯寅平生真赏”、“潘祖荫藏书记”竖长方印、“潘祖荫”白文方印、“翰林供奉”朱文方印、“小脉望馆”白文方印【图3】、“金石录十卷人家”朱文竖长方印、“宋本”“元本”朱文连珠印各一方、“龙自然室”“朱文方印、“说心堂”朱文方印以及“赐兰堂”朱文竖长方印等。撝叔不仅为潘氏刻印,还为其提供或购买印泥印盒,具体指导钤印之法,并建议潘氏雇请一专门人员从事之。潘氏采纳了意见。潘氏的回报是赠予刻书、拓片等,在纳资捐官的时刻,提供金钱资助,更关键的是为撝叔疏通关节、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障碍。这样的作用别人无法代替,故而撝叔也十分感激。3
故宫博物院藏有光绪三年(1877)吴大澂(1835-1902)致潘祖荫信札七十通,涉及金石收藏与鉴赏活动,也包括相互的馈赠与回报等。4这批信札主要作于吴大澂在京期间,记载吴氏频繁与潘祖荫古物鉴赏、金石交流等事。正如吴大澂在第70札所总结:“回忆夏秋摩挲金石,考订古文,手书日数至,赐观拓本,层出不穷,似此清福,未可多得也。”(11月25日第70札)吴大澂在信札中谦称不能刻印,其实他是能够刻印的。即便如此,吴大澂也参与了刻印过程,就是由其写篆,而由陈佩纲操刀刻治:“大澂能篆而不能刻,子振(陈佩纲,陈介祺族弟)能刻,甚妙。偶篆样本呈鉴,不可则再篆,以为何如?”(5月30日第6札)。此外,吴大澂为潘氏购买石料、探讨篆刻优劣等:“青山须待健时归”七字,石不宜小,俟购得送上。”(5月29日第4札)“昨至厂代购青田二方,价银二两八钱,未知可用否?徐辛谷送雪渔印,殊不见佳。’林’字篆法太奇,似白文较胜也。”(5月30日第5札)
吴大澂对潘氏的馈赠、付出与回报:为潘氏青铜器拓片编目(5月16日第1札),送邓盘邓匜拓片(6月11日18札)、《石门颂》《石门铭》拓片、六朝诸拓、隋刻二种拓片(5月28日第3札、6月4日第10札),为题“松壶斋”“艺芸精舍”“千载一时”“半苏白斋”“快哉轩”“镜轩”“负匴斋”等匾额。(5月29日第4札、6月5日第12札、8月6日48札等),绘制时壶样式并探讨绘法(6月3日第9札、6月9日15札)书联(6月11日18札)书面书签、李碑题签、题跋瓦册、(6月21日第22札等),绘制兰笺(6月26日第28札),为之拓器以及谋购李嘉福散盘、曶鼎拓片等。由于关系比较亲近,吴氏在信札中主动索要《沙南石刻》拓本,如成则以潘宗伯题名及硃拓《石门颂》回赠(5月28日第3札)。
潘祖荫对吴大澂的馈赠与回报:《三老碑》拓片(6月3日第9札)、高句丽石刻拓片、格伯敦拓片(6月4日第10札等)散盘拓片题跋(6月26日第28札)以及允吴氏拓器、观赏藏品等。更重要的是,当吴大澂进行三晋赈务募启列名时遇到了困难,潘祖荫出面疏通关系(8月19日第60札),使得赈灾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这批信札涉及到的信息还有就是吴大澂作为中介人居中介绍徐三庚(1826-1890)、陈佩纲(生卒不详)为潘祖荫刻印:“徐辛谷,名三庚,近号金罍,俟购得石,即属刻。”(5月28日第3札) “徐刻自以为是,又不听人调度,无法处之(5月30日第6札)。“徐刻’盉宀’,当再觅石送去。”5(6月25日第24札)“’盉宀’已属金罍刻之,再刻’豆棚’一印,亦函致矣。”(7月3日第34札)“顷遣仆人取印,径呈函丈,’盉宀’二字印,尚未得见。”(7月3日第36札)“’瓜棚’印,今午即有石,亦徐君(三庚)物,每方价钱七吊。”(7月4日37札)“陈子振摹印则佳,拓全形器必亦精细,吾师何不一试之。……其人朴实,必不孳孳为利。惟寒士衣食之需,不能不体恤耳。”(6月25日第24札)向潘氏积极推荐陈佩纲:“秦诏字体,刻印亦极宜,想陈子振必能仿刻也。”(6月2日第8札)对徐三庚刻印的回报是:“二金领到。润笔、石价均已付清。徐刻二印,当再促之。渠亦深感盛意也。”(6月24日第23札)“徐(三庚)润四金领到,石值不及一金,以后再算。”(8月5日第47札)请人刻印,石头自备,另付润笔,吴大澂居中联络传递消息。这里提到付给徐三庚治印润笔金额为“二金”“四金”,这是直接的金钱回报,干脆利落,少了枝节,短暂的人情关系往往如此操作,只是未详刻印内容与数目。光绪元年(1874),陈佩纲为潘祖荫作“壶天”朱文白文印各1枚,由陈介祺邮寄给潘氏。“壶天”乃指潘祖荫赁居留宿之“黄酒馆”,其地离潘氏入值官署甚近,为节省来回奔波之苦,且可多睡两个时辰,风雨天或须提早入贺之节日,潘祖荫便住在黄酒馆里。里面嚣尘湫隘,有“壶天”之题榜,故有陈佩纲以此为内容刻印之举。《潘祖荫日记》中出现“壶天”二字,便是其在黄酒馆之意。
对王石经刻印之回报,《潘祖荫日记》偶有透露: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西泉刻二印,润八两”6,润金还是相当丰厚的。
三、潘祖荫使用印章的细化与专门化
潘祖荫收藏古籍所用印章多是请赵之谦为之。撝叔为其刻有“伯寅藏书”朱文方印、“滂喜斋”朱文方印、“潘祖荫藏书记”朱文竖长方印,此印边款“郑盦司农收藏宋元秘本之记”,已经指明了印章所用之处,非是一般普通书籍。“宋本”连珠朱文印、“元本”朱文连珠印更是直接点名了钤盖的对象。“郑盦”朱文扁方印,边款特为注明“郑盦司农藏书之印。”而“八求精舍”朱文方印,乃潘氏推崇宋代藏书家郑樵所云之求书八法,故特请撝叔刻印名斋。
潘祖荫对信笺颇有心得看法,频频制作使用之。其所制时(大彬)壶笺上面配有专门印章为“千载一时”,此印亦钤于日记稿本上。潘氏又有“八兰斋”印在书札上钤盖。吴大澂致潘祖荫一函中云:“吾师所用兰笺,画不佳而纸甚雅,惟’喜’字木印不古,装入尺牍,以古雅为宜。偶橅叔丁宝林钟’侃喜’之’喜’,又见汉印’长年鹤’甚佳,橅出呈鉴,刻一木印用之,亦吉祥语也(百鹿亦可刻印,鹿鹤二印为对)。”7 “喜”字木印为潘氏信笺专用。吴大澂以为不古,建议更换。主动橅写“喜”字以及汉印“长年鹤”,建议以此刻木印,似较为古雅。李军在《病起自作笺 常言家国事——潘祖荫书札的几个维度》一文中提到潘祖荫使用印章与钤盖方式的一个特点,即将印章与笺纸融合。举例为潘祖荫致吴昌硕函中有书房图案笺纸,在书房一角场景外,左下角钤潘氏斋号之一“三苏仙馆”绿色方印,右上角倒钤“分廛百宋移架千元”绿色方印。8潘祖荫在致赵之谦信函中,多在左下角钤有“补万柳堂”“鞠躬室”“文字之福”“观电菴”“古錞于室”“二苏仙馆”等印,其中四月卅日致撝叔札六页皆在左下盖“补万柳堂”印,“二苏仙馆”印为蓝色。9【图4】更细致的描述:“潘祖荫书札中用印,按钤盖位置分,有引首、押角、骑缝等情况,其中押角最多。印章成为重要的装饰,尤其是潘祖荫所用部分素笺之上。依印章内容分,又有干支、斋号、警句闲章等几类。”10李文中列举59方内容形式朱白各异者。潘氏书札用印,还会考虑内容、大小与笺纸配合。其晚年病目所制一尺大巨笺上,钤盖的便是“梅花喜神之馆”之类巨印。11传统尺牍用印并非常态,偶一用之亦只是施于姓名处,表示信用与尊重。潘祖荫则经常大量地使用,但不是在落款姓名处,主要钤在书笺边角,成为其用印一大特色。
撝叔所刻“翰林供奉”朱文方印,边款为“郑盦司农奉敕书联,命刻此印。”印章是为潘氏书写对联时钤盖,特殊内容具备专门的用途,显而易见是有意为之。考察潘祖荫书法作品,如对联团扇等用印较为简单,多是白文“潘祖荫印”与朱文“伯寅”相搭配者。
青铜器及相关衍生品上,用印主要请王石经(1833—1918)为之。光绪元年(1875)正月陈介祺致信潘祖荫:“已为属西泉、子振作南公鼎斋、南公宝鼎之室、南鼎斋、盂斋、盂鼎斋印及南鼎斋古彝器、古文字、盂斋先秦文字、两京文字、盂斋法化诸印,且一斋名作大小数印。”12陈介祺与潘祖荫两人颇为投契,相互馈赠巨量拓片等作为礼物,陈介祺还作为中介人积极介绍王石经等人为其刻印,此举既提升王氏名望,又增加其收入。这和赵撝叔刻印是有求于潘氏,某些方面必须仰仗攀附潘氏的心理存在很大不同。从此信看,王石经、陈佩纲两人为潘祖荫刻印,内容较为多样,主要针对潘氏的青铜器尤其是大盂鼎而命名。形式数量,大小数印,颇为可观。同札又言:“西泉不欲刻甚小者,盖汉玺印小字字多者尤不易也。”说明王石经并非所有印章都刻,其中有其不情愿不擅长处。陈介祺作为师长辈,居中传话,是可以比较直接的。正月十九日陈致潘另一函:“’南宫鼎斋’印,今促西泉刻出。’斋’字乃弟影齐侯罍写之,尚相合。二人以废数日力矣。刀法矜贵非拘。” 13【图5】陈介祺作为中介人,督促王石经为潘祖荫刻印,并亲身写“斋”篆字参与之。又言作印之辛苦,二人费数日功夫,刻成后的效果陈氏还是满意的。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十六日,陈致潘函:“西泉刻大印毕,祺为之记。今拓上二纸,印后寄,均教之。”14 “伯寅宝藏第一”白文巨方印,边款为陈介祺亲为作记,以纪念“文修武迪”之不朽盛事【图6】。
王石经《甄古斋印谱》收有为潘祖荫治印多枚,包括“伯寅宝藏第一”“南公鼎斋”“惟庚寅吾以降”等。前有潘祖荫为之撰序:“簠斋丈曾属西泉为余刻印,今年始遇于都门,复为刻数枚。西泉之印近今无第二人,质之知者以为何如?光绪丙戌春二月下旬,吴县潘祖荫识。”【图7】陈介祺作为中介人,王石经得以为潘祖荫刻印。潘祖荫与王石经在光绪十二年(1886)在北京晤面。序言除了客套成分,潘祖荫对王西泉的篆刻评价极高,认为“近今无第二人”。笔者曾提过审美错位问题,当时陈介祺、吴云、潘祖荫等重要鉴藏家对王氏的篆刻都是衷心赞赏并推崇的15,以能得到其印为慰。放至当代,可知王氏篆刻已不入流矣。其弊主要在于心态泥古不化,线条拘谨细弱等。
也有例外。攀古楼乃潘氏收藏青铜器之所,赵撝叔、吴昌硕等人皆曾刻有“攀古楼”朱文方印。
对各类藏品以及往来信札的所钤印章内容与风格,潘祖荫有其主见与安排,如此细化专门化的操作只有有力者潘氏方能做得到。
四、使用与钤盖方式
潘祖荫具体使用印章,大部分应非其本人钤盖,而是请人代钤。潘氏公务繁剧,不少时候,诗文书法都需请人代笔,晚年深受目疾齿痛等困扰,日记书信等事皆由其夫人、仆人等代办,钤印如此琐事,潘氏也只能委托他人。赵之谦曾经建议雇一妥当之人,专门为之盖印。潘氏应该采纳了建议。
苏州博物馆藏光绪年稿本《潘祖荫日记》,封面与封底钤有潘氏印章数十枚。比如光绪七年(1881)“潘押”“八喜斋”“千载一时”“如愿”“喜”“红蝠书堂”“晚夝轩”“归思浓于酒”“耕巷小筑”“夙夜匪懈”“埙轩”“鞠躬室”“古乐轩”“古名居”“蚕麦堂”“百宋千元”“拙轩”“三代古陶轩”“观电庵”“葵藿是平生”“敬事后食”以及不同年份的干支印等,正文中钤有小印。光绪八年(1882)原稿封面有“壬午”四方,“喜”二方,“文字之福”“八喜斋”二方,又有“快哉轩”“日报平安福”“吉祥喜语”“如愿”“千载一时”“报国在丰年”“八愿斋”“出吉入和”等印。封底有“赐兰堂”三方,又有“江东书匮”“潘氏郑盦藏书”“郑盦秘笈”“莼丝馆”“半汸”“归思浓于酒”“寻书玩古”等。上海图书馆藏《潘文勤日记》时间是光绪十四年全年,其实与苏博所藏乃一个系列。封面钤有“龙威洞天”“如愿”“吉祥喜语”“戊子”“喜”“梅花喜神之馆”等,正文中亦有小印。其他年份除干支印外,印文内容多有重复者,亦有稿本封面未钤印章者。
潘祖荫斋号印,仅在苏博藏《潘祖荫日记》上就有30余方,仅光绪七年(1881)日记上就钤有16方,其中稀见者多达12方。加上历年干支印以及闲章等,总数当在一百方以上。日记上面干支印内容具有针对性,而钤印方式似乎缺少规律性,只是把所有印章盖一遍,把空间填满,整体上显得较为凌乱,这从一个侧面显示非潘氏本人亲力亲为者。潘祖荫索求所得印章甚多,显示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但无疑降低了所用印章的艺术水准,有些甚至可称低劣之作,以之钤盖,且钤印累累,疏于拣择,显得俗气拥塞,大体流于项元汴、弘历一路矣。当然这只是日记稿本有此状况。
如何在书笺上用印,前面已略述。尚须引申一下,赵撝叔所刻“赐兰堂”印,潘氏收到此印,极为珍重,使用极为谨慎,印迹并不多见。苏州博物馆藏潘祖荫致吴昌硕一件书札上盖有此印之蓝色印记,且多次钤盖。16这可由2017年吴门拍卖一件拍品“潘祖荫致族兄潘钟瑞札”中看出:“亡友从不为人刻印,独为弟刻此一印,是以从不用之,今已用之,则竟罔之矣。明日从直遵谕,专候驾临,不敬诣矣。香禅三哥大人,制荫顿首。”此处亡友指赵之谦,因为赵之谦刻此印不久即病逝于江西南城。潘氏在信中已经言明此印的珍视态度。
如何在大盂鼎拓片上钤印,陈介祺对潘祖荫还有具体而细致的建议:“鼎图下方拟用名印一,中用南公鼎斋,不用伯寅所藏第一。”17师(左上未右上反文旁,下为厂再右下为又)簋拓片上可见左下钤“郑盦藏敦”白文方印,右上钤“赐兰堂”朱文竖长方印。18
五、结语
除了上述赵之谦、徐三庚、王石经等人外,《潘祖荫日记》偶有记载其他刻印人及得印之信息:光绪九年九月十四日“得陶堂印一枚。”光19绪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谢墉以’二苏仙馆’印赠,为题’梅石庵图’四字。”20光绪十年十月十八日“以’羽陵山馆’’红蝠书堂’’晚夝轩’属梅石谢庸刻。”21我们稍后即可看到光绪十一年日记封面上已钤有名为谢墉所刻之三印,唯“羽陵山馆”易一字为“羽 王岑 山馆。22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日“张迪先篆’铜鼓斋’印,连石二金交子英。”23我们同样看到在光绪十二年日记封面上已钤有张迪先所刻此印。24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方长孺为刻三小印,皆不见工。”25因对方氏所刻不满意,后面有无使用则不得而知矣。
施印人当然还有吴昌硕等人。光绪九年四月至十一年潘祖荫回苏守制期间,曾致函吴昌硕求刻印。“病目久不愈,不能视,肿赤未消,谢客已月余矣。外三石,祈赐篆。屡渎不安,当图报。来札字须大如此,小则不见也。”26另一函:“印收到。百朋之赐,何以加之。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 荫顿首”27潘氏向吴求印,不止一次,不止一方,并且即刻表示报答之意。目前所见有“攀古楼”白文方印以及“氵允钟堂”“不如掩关”等印。吴昌硕弟子徐新周(1853-1925)为潘祖荫刻有“伯寅父审释彝器款识”朱文竖长方寿山石章。28胡义赞(1831-1902)为潘刻有“泉癖”等印。两人为金石书画鉴藏好友,更确切地说,胡是潘祖荫书画古董收藏之掮客或说中介人。
作为朝廷重臣,不少人以能为潘祖荫刻印为荣,借以抬高身价,获取口碑。赵之谦等人更是有求于潘氏,故屡屡为之治印,并涉及印章的材料、用品、钤印方法等。所以潘氏获取印章并不困难。对交情持续时间长者,以各种物品作为回报,一般不直接以现金作为报酬。而对交情短暂,由别人居中介绍者,则一般直接给予金钱作为润笔。
稍加统计,潘祖荫斋名有数十个之多,这些建筑现实中大都并不存在,只是有寓意的命名,表达不同人生时刻的感触与情怀。通过印章等形式,钤于各类软质物上,从而纪念某些时刻、实现某种理想、达到某种满足。这种方式,明代文徵明等人就屡屡如是施为。潘氏延续了江南“纸上造屋”的传统,载体却主要不在书法,而在日记、尺牍、拓片等处。
晚清鉴藏家存在使用印章细化的现象与趋势,比如干支印、收藏鉴赏印等,潘氏更是做到了专门化,其印章具有专门的用途、载体与钤盖方式,从而个性化地赋予了收藏品以及社交的重要形式与手段——尺牍等更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属性。
注释:
1.潘裕达、潘佳整理《潘祖荫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2月,第185页。
2.《书法》202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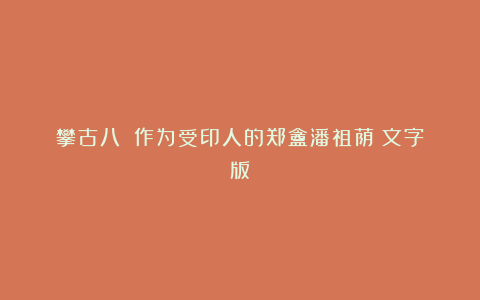
3.参见张恨无《寿如金石:作为施印人的悲盦赵之谦》一文。
4.参见李文君整理《光绪三年吴大澂致潘祖荫未刊信札》。《贵州文史丛刊》2021年第2期。
5.“盉宀”,此内容笔者认为有问题,然未看信札原件,无法判定。
6.同1,第 372页。
7.参见李文君整理《光绪三年吴大澂致潘祖荫未刊信札》《贵州文史丛刊》2021年第2期。吴大澂致潘祖荫6月14日第20札。
8.参见李军《病起自作笺 常言家国事——潘祖荫书札的几个维度》。《艺术工作》,2022年第6期(2022年12月15日),第59-60页。印章“三苏仙馆”当为“二苏仙馆”。
9.参见《书法》2020年第1期。
10.同4。
11.参见6,第60页。
12.光绪元年正月十一日陈介祺致潘祖荫,《秦前文字之语》,济南:齐鲁书社,1991,第46页。
13.陆明君 著《陈介祺年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4月,第301页。
14.同11,第320页。
15.陈介祺致潘祖荫札中有“西泉似不让撝叔也。”《簠斋》尺牍十二册本。陆明君《陈介祺年谱》光绪元年正月十一日陈介祺复潘祖荫书,第300页。
16.笔者看法:每页皆在右上角,数次之多,当非潘祖荫本人所钤,而是由潘氏指示,仆人等施为者。
17.光绪元年六月十五日陈介祺致潘祖荫函,《秦前文字之语》,第53页。
18.童衍方编著《吴昌硕集彝器款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8页。
19.同1,第245页。
20.同1,第249页。
21.同1,第285页。
22.同1,第295页。
23.同1,第327页。
24.同1,第361页。
25.同1,第344页。
26.信札藏于苏州博物馆藏。
27.同17。
28.2011年西泠印社春拍——文房清玩·近现代名家篆刻专场。
【图1】潘祖荫致赵之谦札1 《书法》2020年第1期。
【图1】潘祖荫致赵之谦札2 《书法》2020年第1期。
【图1】潘祖荫致赵之谦札3 《书法》2020年第1期。
【图1】潘祖荫致赵之谦札4《书法》2020年第1期。
【图2】《潘祖荫日记》光绪八年日记封面,苏州博物馆藏。
【图3】王义骅主编《赵之谦篆刻集粹》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11月,第5页。
【图4】“二苏仙馆”印,潘祖荫致赵之谦尺牍。《书法》2020年第1期
【图5】王石经刻“南公鼎斋”等,《甄古斋印谱》。民国涵芬楼影印。
【图6】王石经刻“伯寅宝藏第一”巨印,《甄古斋印谱》。民国涵芬楼影印。
【图7】潘祖荫序《甄古斋印谱》。民国涵芬楼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