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珍珠港
分散的云朵渐渐消散了,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邪恶岛屿的一部分。当我们飞过海岸线时,一股黑烟出现在了我们的右前方,接着,另一股黑烟在距离我们编队更近的地方出现了–大约只有200米。高射炮!这和我们以前在中国遇到的零星高射炮火不同,这是我头一次遇到密集的防空炮火。我眼看着高射炮炮弹爆炸时发出的黑烟距离自己越来越近。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也许我们的突袭并不是一次真正的奇袭。我们真的成功了么?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编队从卡胡库角左侧掠过。编队指挥官岛屿海军中佐随即改变了我们的飞行方向。接着,我按计划发现了卡内欧黑机场。这就像是在演习,所有的一切都很顺利。我的紧张感顿时消失了。我变得平静和沉着。
我们在空中并没有遇到预期的美军战斗机的阻截,我们的战斗机于是离开编队前去空袭机场。编队指挥官在发出攻击信号后随即脱离了编队,率领着他的机群向希卡姆机场发起了空袭。他机群的其余战机则分别向卡内欧黑空军基地和福特岛发动了攻击。我们的轰炸机将飞行高度保持在400米,低于云层。我们不顾敌人猛烈的高射炮火持续飞行在低空,我们的机群并没有损失多少飞机,只有29架飞机在战斗中被击落。
我们的78架轰炸机转向右边,从东面飞向珍珠港。我驾机飞在全中队的最前面,率领着机群发起了攻击。我们当时的高度为4000米,我在云层下面看到了前方的珍珠港。我们的俯冲轰炸机正在那里俯冲着发动攻击。
在火奴鲁鲁市上空,我的中队一边加速一边组成了攻击队型。我检查了飞机的投弹设备,并且打开了驾驶舱盖。由于港区浓烟弥漫,我的视线并不好,但当我飞近港口后,我发现了停靠在福特岛附近的一排美军战列舰。它们之中的几艘已经被浓烟笼罩,而另几艘战舰的侧面则正在汩汩地向外冒着棕色的燃油。它们的甲板和上层建筑上都有高射炮在喷吐着火舌,它们好像都在朝我射击。我看到另一队我军轰炸机此时正在我们的右侧进行俯冲,我不再感到孤独了。那个编队的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向下冲去,很快最后一架也进入了俯冲。现在轮到我们中队了。
我驾机倾斜转弯,这是我给队员们的攻击信号,然后向下冲去。地面上,数千颗曳光弹呼啸着向空中飞来,当它们从我的战机旁掠过时我感到它们好像飞得更快了。我当时的高度为3000米,速度为200节。我脚踏制动板转入俯冲,同时摘掉了轰炸瞄准器的盖子。我的战机以50度角向下冲去。由于港湾里没有航空母舰,我决定攻击一艘巡洋舰。福特岛上到处都冒着火焰,一片厚重的烟尘漂浮在清晨的空气中。我紧盯着自己的轰炸瞄准器,我看到许多糖果一样的子弹正密集地向我这边汇集而来,但又都在最后一刻从我的战机旁擦肩而过了。我中队的另外八架轰炸机排成一列紧随在我的身后。
我捕捉到了自己的目标,一艘大型巡洋舰,它已被牢牢地套在了我的瞄准器里。准尉齐藤开始向我通报高度。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正从机身左侧袭来。我一边不断靠近目标,一边校正偏移的飞机姿态,直到目标舰几乎充满我的视野。“600米,”齐藤喊道,“预备……投弹!’我投下了炸弹,然后立即拉动操纵杆开始爬升。我一度完全不知道投弹的结果,直到我拉起50米后才从通话器中听到了齐藤的喊声。我的撩望员兴奋地喊着我们投弹的结果。“编队指挥未中,第二架未中,第三架命中!调整得很好!第二梯队全都命中!”我后来才知道我们攻击的目标是奥马哈级轻巡洋舰“罗利”号。
1941年12月7日,浓烟翻滚的珍珠港港湾
整个空袭共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我只目击了第二攻击波的部分攻击行动。稍后,当我们返航后,我从渊田中佐的口中听到了第一攻击波的经历。
当第一攻击波飞抵珍珠港时,港湾上空弥漫着一层从房屋中腾起的渺渺炊烟。周围都很平静。渊田用自己的望远镜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当整个编队飞得更近以后,战列舰“内华达”号、“亚利桑那”号、“田纳西”号,“西弗吉尼亚”号、“俄克拉何马”号,“加利福尼亚”号和“马里兰”号都一一从薄雾中显露了出来,美国战舰特有的笼状主桅非常明显。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战列舰当时都在港湾里。
海湾里没有航空母舰,但渊田仍为自己的运气感到高兴。他向编队发出了攻击令,然后率领着自己的分队绕过瓦胡岛西侧,从巴伯角上空飞过。这个海角上有一个坚固的高炮阵地,但没有人向我们的战机开火。当渊田的战机靠近美国军舰时,他发现敌人的军舰上没有人在走动。军舰上的美军显然都还沉浸在梦乡之中。在确信自己的任务已经成功后,按照事前接到的指示,他发出了如下无线电报,“我们的奇袭已经成功。”
美国海军“罗利”号轻巡洋舰,阿部善次指挥的机群攻击的就是该舰
这份无线电被我们的旗舰“赤诚”号收到,它立即将电报的内容转发给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和“长门”号战列舰,后者是停泊在广岛的联合舰队旗舰。在接到这份电报后,军部立即向待机的作战部队下达了向马来西亚、香港、关岛、威克岛和其他目标发动进攻的命令。在渊田发出偷袭成功的电报后不久,希卡姆机场上腾起了爆炸的烟雾,接着福特岛也遭遇了空袭。这表明我们的俯冲轰炸机已经开始进攻。远处,惠勒机场也已被爆炸的浓烟所笼罩。
作为此次空袭的总指挥和水平轰炸机分队的指挥官,渊田看到美军战列舰旁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道鱼雷航迹,紧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几条这样的鱼雷航迹。这表明我们的潜艇正在用鱼雷发动攻击。他于是向自己的分队发出了开始轰炸的命令。突然,密集的高射炮火出现在他的编队面前。美军高射炮炮弹的炸点起初是在编队的前方,但很快就调整到了编队中央。大多数炮弹都是港湾里的军舰发射的,但也有一些炮火来自岸上的高炮阵地。
美军抢险队员站在倾覆的“俄克拉荷马”号战列舰上,设法营救幸存者,背景是坐沉的“马里兰”号战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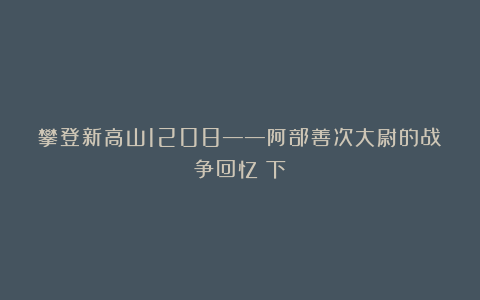
渊田对于敌人能够对突袭做出快速反应,并且在空袭后不久即开始回击感到十分钦佩。美军的高射炮火变得越来越准确。突然,渊田的座机在猛地抖动了一下之后开始向一侧滑去。他后来发现原来是机身上的一根控制索几乎被美军的炮弹打断了。尽管如此,他仍率领着自己的分队轰炸港内的美国战舰。当他们开始转向的时候,一股高度大约为1000米的红黑色火柱从战列舰“亚利桑那”号上喷涌而出。这次爆炸非常猛烈,正在港湾上空飞行的日本战机也都感受到了剧烈的晃动。渊田用无线电指示自己的轰炸机群再次轰炸“马里兰”号,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当第二攻击波抵达珍珠港时,战斗正好达到了最高峰。
活着真好
我们在飞离航母两个小时以后返回了航母,时间是上午8时30分。我们的全部损失是9架战斗机、15架俯冲轰炸机和5架鱼雷机,共有54名飞行员在战斗中身亡。我们在空袭中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作战力量,但我们没有遇到这次空袭的首要目标–美军航空母舰,因为它们当时都已经出海,但南云仍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既定作战任务。
我在回到自己的航母后仍然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做梦一般。我走进自己的小舱室,开始脱我的飞行服。在我整洁的桌面正中央放着一个信封,里面装有我的遗嘱,上面的收信人是我的父亲。突然,我的精神又振奋了起来,活着的感觉真好。上午9时,我们的舰队开始向西北方向返航,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空袭已经结束,我们完成了任务,但战争仍在继续。
许多美国军官曾经向我询问过,我们当时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入侵夏威夷。虽然我并不了解我们的高层是如何策划战略的,但我猜想当时他们之中也许没有人想到我们的空袭会取得成功。此外,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上为登陆部队提供后勤补给和支援的任务将非常艰巨。正如我们日本人所知,美国人即使数量很少也能组织起顽强的抵抗,我认为消灭他们将是非常困难的事。
空袭过后,美国水兵在清理被击落的日机残骸,这是一架99式舰载俯冲轰炸机。
我已经讲完了珍珠港空袭,我讲述的内容都是我曾经亲身参与过的那段经历。今天,我对美国人的宽容和理解很感激,日本已经开始了它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历史。1951年12月8日,我从国家警察后备队毕业后接受了第一项任命。当时,我仍没有意识到空袭珍珠港是多么重要的一天。那些在空袭珍珠港中失去了丈夫、父亲和儿子的人,当然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很担心自己讲述的简短故事会揭开一个旧伤疤。我从心底里真诚地为那些空袭中的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祈祷。
我曾经向美国人解释什么是武士。这个词用汉字书写时是两个字。第一个字的意思是“挡住敌人的刀剑’,而第二个字的意思则是“绅士”。所以,实际上武士道精神并不崇尚侵略,它的含义实际上就等同于美国人所说的“defense”(防御)一词。
已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是他指挥部队攻击了珍珠港,曾经极为反对和美国交战。他对美国十分了解,虽然反对与美国爆发战争,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帝国海军军官。当他登上旗舰“赤诚”号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美国爆发战争,你们将面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它的总司令海军上将金梅尔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军官,他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超越其他许多年长的军官被任命到这个岗位上的。要想战胜他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我们攻击珍珠港两天后,当我们在“赤诚”号的指挥舱里收听美国人的广播时,海军中将南云走进船舱。当我告诉他美国海军上将金梅尔已经被解除职务时,他表现得非常遗憾,他说他很替那位美国将军感到惋惜。
日本人在和美国爆发战争前对美国并无恶感或憎恨。为什么我们要犯这样一个大错误呢?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应该信守这样一个格言:“决不让珍珠港和广岛的悲剧重演。”
我再次用我的全部诚心为那些在珍珠港空袭中丧生的人祈祷。
干戈玉帛
尽管时隔多年,阿部仍对那些用双手把日本拖人战争的战犯们极其厌恶。“我的两位江田岛海军学校时的同学,担任的是驱逐舰舰长之类的低级职务,在得知日本战败投降后羞愧地自杀了”,他说,“那时有800位海军官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那些被定为甲级战犯的人为什么没有这样呢?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旧困扰我。当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时,那些鼓动日本发动战争,并把我们作为开战先锋的人应面向皇宫剖腹谢罪,那些军部的首脑们应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负责。如果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至少留给世界的是武士道精神的强烈印象,这才说明他们有真正的勇气。我总以为开战的声明已在空袭珍珠港前30分钟宣布了,当我最终发现事实的真相时,我极度震惊和羞愧,我觉得很遗憾。战争中突袭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那只应在宣布开战后才能进行”。
他说,那个时候,他和他的战友们只听日本政府告诉人民的那一套,仅仅偏激地看着自己的国家,“当我回顾那段日子,日本似乎确实太狭隘了。大部分的日本人对珍珠港一所知,在美国,12月7日来临的时候他们总会记得这个日子。这两个国家的区别是巨大的”。
晚年的阿部患上了癌症,他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揭示当年珍珠港的真相,以避免今天的年轻人再经历当年他们那代人的流血与悲哀。可怕的回忆和昔日的仇恨难以消却,前美军与日军官兵们间的彼此接纳并不容易。直到1991年,当阿部与其他一些日本老兵应邀到珍珠港参加珍珠港事件50周年纪念时,两国老兵之间才慢慢显露出友好的姿态。当理查德·费斯克写下了“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的赠言送给阿部,并邀请他昔日的敌人访问夏威夷时,伟大的友谊已牢不可摧,当迪克于2004年春逝世,阿部非常悲伤。
战争结束50年后,阿部善次和当年的美国老兵相逢一笑泯恩仇。
‘孩子们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很多,也许能教会他们的国家应如何传播和平’,阿部写给美国老兵杰尼弗的信中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奋斗以增进了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