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表在JDE上的文章《Why is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lining in China? A perspective from urban commuting》讨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此外,这篇文章在研究设计和识别策略上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也值得深入学习。
具体是啥呢?一起看看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持续下降的深层原因,聚焦于一个长期被忽视但高度相关的视角——城市通勤时间。尽管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劳动参与率却从1990年的73%下降至2020年的60%。作者指出,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和交通拥堵日益严重,通勤成本随之上升,这可能在悄然削弱女性的劳动供给。
基于2015年中国1%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平均通勤时间每增加1分钟,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会下降约0.5个百分点。城市之间通勤时长的差异能够解释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差异的40%以上。进一步地,从2008年到2020年,全国主要城市的通勤时间平均延长了4.7分钟,据估算,这一变化足以解释同期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近47%。
研究还表明,女性对通勤时间的敏感性显著高于男性;教育程度越高,女性对通勤的负面反应越小;而家庭负担较重(如有子女)的女性则受到的影响更大。此外,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通勤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篇文章在研究设计和识别策略上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值得学习。
首先,文章提出了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且理论价值突出的研究问题,并从“通勤”这一日常却常被忽略的视角切入,拓展了对中国城市化背景下性别劳动差异的理解。将通勤成本视为影响女性“工作—家庭”选择的重要变量,为解释女性劳动退出提供了新的机制。
其次,作者巧妙构造了外生性的工具变量,利用“潜在城市形态”中的紧凑度指标(Cohesion 和 Range Index)作为工具变量,借助地理约束和人口增长模型,避开了现实城市形态与治理水平等因素的内生性问题。这种方法既具有严谨的识别逻辑,也具有良好的推广潜力,特别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的研究情境。
此外,文章的数据整合能力也值得称道。它将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城市统计数据有机结合,体现了跨学科融合的实证研究范式。在方法上,作者通过多种模型交叉验证(OLS、2SLS、IV-Probit、控制函数法),确保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度,为社会科学量化研究树立了范例。
使用的数据集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为2015年中国1%人口抽样普查(Mini Census),覆盖全国范围,包含约13.5万名20至50岁已婚女性个体。数据详尽记录了个体及其配偶的教育水平、就业状态、通勤时间、户籍类型、是否租房、家庭子女数等信息。
为了构造与通勤时间相关但具外生性的工具变量,作者结合遥感夜间灯光数据(DMSP和VIIRS)测算城市实际与潜在建成区,并利用数字高程模型(DEM)、水体分布图和历史人口数据估算城市在地理约束下的“潜在城市形态”,进而构建城市紧凑度指标。
此外,研究还引入CEIC数据库和各类统计年鉴中的县级经济变量,如人均GDP、产业结构、住房价格等,用于控制宏观经济背景的差异。为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还使用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2004年及以后的反复截面数据,进行了跨期与外部数据的验证。
使用的计量方法
为识别通勤时间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因果效应,作者运用了一系列严谨的计量方法,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
首先,研究采用OLS线性概率模型(LPM)作为基准模型,对通勤时间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初步估计。结果表明二者显著负相关,但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该估计可能存在偏误。
为进一步识别因果关系,作者构建了两个外生性工具变量——Cohesion Index 和 Range Index,分别衡量城市形态的集中度与延展度。这些指标基于地理约束与预测人口规模而构建,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在此基础上,作者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发现通勤时间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存在显著负向的因果影响。
此外,作者还采用控制函数法(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结合IV-Probit模型对估计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在稳健性检验方面,文章进行了多维度测试:更换工具变量(如使用Proximity与Spin指数)、使用男性平均通勤时间作为替代解释变量、控制城市面积与产业结构变量,并排除近五年有迁徙经历的个体。同时,使用CHNS数据进行横截面与时间序列上的稳健性复核。所有结果均验证了研究主结论的可靠性。
实证模型
本节旨在构建一个用于评估通勤时间对女性劳动力参与影响的实证模型。本文的建模思路受到 Le Barbanchon 等(2021)研究的启发。该研究提出了一个职位搜索模型,指出通勤会降低工人的流动效用,且男女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在该框架中,当工资与通勤成本之间的差额超过失业状态下的贴现效用时,个体才会接受一份工作。因此,女性与男性在工资与通勤之间的权衡存在差异,从而在劳动市场上形成性别工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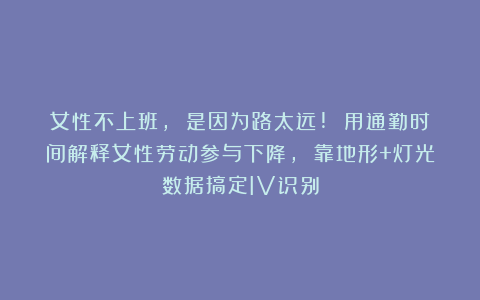
尽管 Le Barbanchon 等人主要关注劳动供给的“强度边际”(如工资水平),但其模型同样适用于解释“参与边际”——即个体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当失业者决定是否开始求职时,他们实质上是在权衡预期工资与预期通勤成本。一个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可视为个体预期通勤时间的代理变量,而预期工资则取决于其个体特征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状况。
基于此,提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Flp{ic}表示县c中女性个体i的劳动参与状态;commute{ic}为个体所在县平均通勤时间(单位为分钟,已标准化除以100);X{ic}为其他控制变量;p_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epsilon{ic}是误差项。系数 beta_1表征通勤时间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边际影响。正如 Le Barbanchon 等人所指出,这一影响在男性群体中具有不同表现,我们将在后文展示性别异质性分析。此外,为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在第4.3节引入二元选择模型进行补充验证。
然而,通勤时间commute_{ic}的内生性问题构成了估计 beta_1的主要挑战。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不仅受到地理因素(外生)的影响,还受到城市治理水平(内生)和交通规划等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治理能力更强的城市通常能够提供更高效的交通系统和政策环境,这可能同时影响通勤时间与女性的劳动参与行为。此外,个体在城市间的迁移选择也可能带来估计偏误。Costa 与 Kahn(2000)指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夫妇更倾向于迁入大城市以实现“双职工就近就业”,而大城市普遍通勤时间更长。若不加以控制,该排序行为可能使OLS低估通勤对劳动参与的真实影响(见 Farré 等,2023)。
为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引入第2.2节中构建的 Cohesion 指数与 Range 指数作为通勤时间的工具变量(IV),以识别其外生变动。一方面,城市的空间紧凑度与通勤时间显著相关。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土地扩张明显(Wang et al., 2020)。Angel 等(2010)指出,这一过程导致城市形态趋于“非紧凑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城市越分散,城市内部点对点之间的距离越大,进而通勤时间越长。本文所使用的两个指数以反向指标衡量城市紧凑度——值越大,表示城市形态越分散。附录表A.1列示了郑州若干县域的紧凑度指数及其平均通勤时间,实证结果表明这两个指标与通勤时间显著正相关。
另一方面,Harari(2020)指出,潜在城市形态反映的是城市扩展过程中所受地理约束,因而可视为外生。这使得基于潜在城市形态构建的 Cohesion 和 Range 指数具有良好的工具变量特性,与城市政策等内生混淆变量无关。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与城市经济学文献中的常见做法一致,例如 Baum-Snow(2007)使用州际高速公路的规划路线作为识别变量,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设定的第一阶段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个体i所在县域c的归一化紧凑度指数。
工具变量有效性的进一步检验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不仅要求其与被解释变量(通勤时间)高度相关,还需满足“排除限制”条件——即工具变量只能通过通勤时间影响劳动参与,而不能通过其他路径直接影响因变量。
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双职工家庭可能优先选择居住在城市结构更紧凑、通勤更短的地区;这一自我选择行为可能削弱因果识别的有效性。此外,“高能力夫妇”往往拥有更多资源,能够在生产率高、工资高但交通拥堵的大城市中定居,这种排序行为也可能干扰估计。
为检验排除限制是否成立,本文采用 Altonji 等(2005)的方法,使用可观测特征分析个体排序是否与工具变量相关。选取过去五年内有跨县迁移经历的样本,回归其个体特征与城市紧凑度指数之间的关系。附录表A.3展示了以下回归结果:第1、2列为女性与配偶拥有大学学历的概率,第3列为成为“高能力夫妇”的概率,第4列为生育子女数。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这些可观测变量均不相关,支持其外生性假设。
除个体层面外,还进一步考察工具变量是否与城市层面的其他关键变量相关,包括房价、人均GDP、道路密度、人口规模以及距海岸线的距离等。如果存在相关性,可能意味着工具变量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劳动参与,从而威胁识别策略的有效性。例如,城市形态可能与自然地理(如靠近湖泊、海岸)有关,而这些特征具备非金钱化吸引力(见 Diamond, 2016);城市紧凑度也可能影响住房成本,从而影响劳动激励。此外,潜在城市形态的构造依据人口增长预测,可能与地方经济水平(如人均GDP)存在关联。
为排除这些可能性,检验了上述变量与工具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附录表A.4的结果显示,Cohesion 与 Range 指数与这些城市特征均无显著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未发现任何证据反对将城市紧凑度指数作为有效的工具变量。虽然无法彻底排除潜在城市形态通过其他路径直接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但从统计与经济意义上看,这类影响可能性较小,不足以对实证识别造成实质性威胁。
*群友可直接前往计量社群下载全文PDF和附录code。
8年,计量经济圈近2500篇不重类计量文章,
可直接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任何计量相关问题,
Econometrics Cir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