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还没开始,石碑坳的田埂上已经热闹得像赶集。
村主任老陈站在最高处那块晒谷场,手里的大喇叭在晨雾里“刺啦”作响:“乡亲们,小田改大田,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这是响应号召,利国利民的好事!”
下面站着的百十号人,却静得像冬天的水田。
我爹蹲在最前面,一言不发地抽着旱烟,青灰色的烟雾缠绕着他花白的头发。他脚边放着一截锈迹斑斑的铁犁头,那是爷爷传下来的,犁身上还刻着“一九五三”几个模糊的字。
“张老倔,你倒是说句话啊!”老陈点了我爹的名。
爹缓缓起身,在鞋底磕了磕烟锅:“我不同意。”
四个字,硬邦邦地砸在地上,溅起一片窃窃私语。
“为啥不同意?你家那七块巴掌田,最大的不到八分,拖拉机转个弯都难!”老陈的嗓门又高了八度,“改成三块大田,插秧机、收割机直接下地,你儿子就不用年年往家跑帮忙了。”
说到我,爹的身子微微晃了晃。我在城里安了家,只有农忙和过年才回来。去年秋收,因为请假太多,差点丢了项目主管的位置。
“机器是省力,”爹的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清楚,“可田埂扒了,我爹、我爷爷埋哪儿?”
人群突然静了。
石碑坳的田埂不像别处。每条田埂向阳的那面,都埋着张家世代先人。没有墓碑,只有一丛丛年年自生的马齿苋或艾草。爷爷说,这样先人就能看着庄稼一茬茬长,保佑风调雨顺。
老陈顿了顿:“迁坟补贴一户五千,公墓都修好了……”
“那是坟吗?”爹突然激动起来,“那是根!根能随便挪吗?”
二伯站起来打圆场:“老倔,时代不一样了。村东头李有财家改了大田,去年多收了三成谷子……”
“李有财他爹埋后山,他当然不在乎!”爹的眼睛红了,“可我爹临终前说,要守着咱家的田。田埂在,他就能看见稻子黄。”
雾渐渐散了,阳光照在那些弯弯曲曲的田埂上。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牵着我的手,走过每一条田埂,讲着每一条田埂的故事——
“这条埂是你太爷爷挑土垒的,那年在旱,他就一担担从河里挑水……”
“看这丛栀子花,是你奶奶嫁过来那年种的,现在比碗口还粗了……”
“你爹就是在这条埂上学会走路的,摔了满嘴泥,还咯咯笑……”
那时田埂很宽,能并排走两个人。春天开满紫云英,蜜蜂嗡嗡的;夏天有青蛙跳进跳出;秋天稻穗低垂,拂过小腿痒痒的;冬天落了霜,像撒了层盐。
后来田埂越来越窄,因为要多种一行稻子。再后来,年轻人走了,有些田埂就塌了,荒草长出来。
“改了大田,打谷场还能晒谷子吗?”王婆婆颤巍巍地问。她家的晒谷场是全村最大的,三伏天铺满金黄的谷粒,孩子们在上面打滚。
老陈犹豫了一下:“晒谷场也在规划里,可能要建烘干中心……”
人群又骚动起来。晒谷场不只是晒谷子,还是全村议事的“会场”,是露天电影放映处,是八月十五摆长桌宴的地方。
“还有水渠,”瘸腿的三叔公敲着拐杖,“改成大田,老水渠要填平,新渠走直线。可老水渠弯弯绕绕,连着后山的泉眼,大旱年也没断过水!”
“新渠是水泥的,更科学!”老陈的额头渗出细汗。
“科学?”爹冷笑一声,“你爷爷没告诉你?石碑坳为什么旱涝保收?就因为老水渠顺着地势走,快慢有度。你修个笔直的水渠,下雨是快,可肥也冲走了!”
太阳升到头顶,争吵越来越激烈。同意的人说省力增收,不同意的人说断了根脉。两边的声音像两股水,在晒谷场上冲撞。
我突然发现,这场争论的核心,不只是田埂或晒谷场,而是两种时间观的冲突——一种要效率,一种要记忆;一种向前狂奔,一种频频回望。
中午休会时,爹蹲在自家田埂上,抚摸着一丛野菊花。我走过去,递给他一瓶水。
“爹,我知道你舍不得。可你今年六十八了,还能挑几担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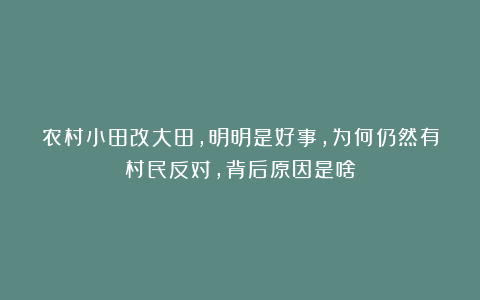
爹抬头看我,眼神浑浊:“去年你回来帮忙,肩上磨出的血泡,我看见了。”
我心里一紧。
“你娘走得早,我就剩这些田了。”爹的声音低下去,“每道埂都认识我的脚印。改了,我去哪儿找你爷爷说话?去哪儿给你娘采她最喜欢的金银花?”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春天的田野绿意萌动,田埂像大地的掌纹,每一道都刻着故事。西头那道埂埋着抗日时保护粮食被杀害的族老;东头那道埂有棵老乌桕,树下曾经是村里的私塾;南边的埂特别宽,因为下面是战备粮窖,现在长满了车前草……
“今晚村里放电影,”爹突然说,“放完电影再表决吧。”
老陈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夜幕降临,晒谷场挂起白色幕布。放的居然是老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胶片斑驳,声音时断时续,讲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建设的故事。
奇怪的是,全村人都来了,连最反对改田的老人也搬着小板凳坐在前排。当电影里响起“樱桃好吃树难栽”的歌声时,不少人跟着哼起来。
电影放到一半,突然停电了。人群一阵骚动,却没有散去。
黑暗中,不知谁先起了头,唱起了山歌。接着一个接一个,那些几乎被遗忘的调子,在夜空下流淌开来——
“三月插秧水满田哟,九月打谷堆成山……”
“田埂弯弯像条龙啊,龙头摇摇向天冲……”
歌声越来越响,年轻人在手机灯光里,惊讶地看着老人们泪流满面地唱着。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爹为什么坚持放电影——他不是要看电影,而是要看这片晒谷场最后一眼。
电影散场时,老陈又要拿起喇叭,爹却摆摆手:“不用说了,改吧。”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是有三个条件,”爹的声音在夜色中格外清晰,“第一,老水渠可以改,但要请省里的专家来看过,不能拍脑袋。第二,晒谷场留一半,让孩子们有个奔跑的地方。第三……”
他停顿了很久,“田埂里的先人骨殖,我们自己迁。不要公墓,就在新田的四个角,各垒一个小土包,种上树。我们要知道,先人还在看着这片田。”
人群沉默着。老陈张了张嘴,最终点了点头。
那晚,爹在田埂上坐了一夜。我也陪着他。下半夜起了露水,爹突然说:“你爷爷教过我,田是活的。它会疼,会呼吸,会记住每双脚。”
“那为什么同意改?”
“因为田也会老。”爹望着星空,“就像人会老一样。旧的田养不活新的人了。”
第一缕晨光照进石碑坳时,推土机来了。巨大的钢铁怪兽轰鸣着,碾过第一条田埂。
爹没有回头。他拿起那截断犁,走向新划定的田角。那里已经堆起一个小小的土包,他将犁头深深插进土里,像插下一枚时间的钉子。
“爹,爷爷,新田更肥,”他低声说,“你们看着,今年的稻子一定好。”
远处,新的田埂正在形成,笔直,宽阔,适合机器奔跑。而旧的田埂正一点点消失,连同那些紫云英、青蛙、童年的脚印和祖先的目光。
我忽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田埂断了可以再垒,只要还有人记得,哪条埂上曾开过什么花,埋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
转身离开时,我看见爹在四个田角各撒了一把稻种——那是他珍藏的老品种,产量不高,但特别香。
也许明年春天,那里会长出四丛青青的稻苗,在新田的边际,标记着旧田埂曾经蜿蜒的轨迹。
其实,农村“小田改大田”过程中遇到部分村民反对,这是一个涉及文化心理、利益调整、现实顾虑等多层次因素的复杂现象。尽管这一改革在宏观上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但具体到个体村民,他们的反对声音背后往往有着真实而深刻的逻辑。
土地重新分配时,村民会担心自家土地的位置、肥力、灌溉条件等“隐性价值”在新分配中受损。即便面积不变,耕地质量差异也会引发矛盾。
田埂、水渠等附属设施的清除可能涉及青苗、树木的补偿,若标准不明确或偏低,易引发抵触。
作者 | 鸿雁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