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栏屋里的笑声
杨进文
牛栏屋,顾名思义,就是耕牛住的屋子。自1949年建国后至1980年“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集体化道路。
时过境迁,很多儿时往事都淡忘了,但生产队里的那座牛栏屋,在我记忆的长河中始终挥之不去。因为那时的牛栏屋,是我们这群小伙伴的乐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娱乐圈”,曾经一阵阵幼稚的笑声,就是从那牛栏屋里传出来的。
生产队的牛栏屋,结构是一排长长的木房子,四排多间,用不是那么优质的木头榫卯排起屋架子,柱子上凿有长条槽口,屋上用竹片代替椽皮,用杉木皮当作瓦片盖好,里面一间一间用那粗糙的木枋隔着。而牛栏中间一条“通道”,是人与牛“齐步走”的出入过道。
每年稻谷秋收之后,社员们将晒干了的稻草捆好一担又一担的挑到生产队牛栏屋里。然后有人爬到牛栏屋上的“阁楼”,有的在上面码草堆放,有的在下面将稻草往上抛,配合得相当默契。把整个牛栏屋的“阁楼”塞得密不透风。稻草犹如进了保险箱,同时给耕牛遮挡了寒风,可谓一举两得。
到了冬天,山区里冰雪雨天的日子多,其时,我们这群“调皮鬼”(长辈对我们的戏称)视牛栏屋为“儿童乐园”,在那草楼上耍出筑地道、栽跟斗、拱地洞、捉迷藏、打草仗等令人开心的游戏,毫无顾忌地呼叫打闹,“唯恐天下不乱!”玩得不亦乐乎,经过一阵“摸爬滚打”,汗就全身冒了出来,额头上挂着豆大一点地任其滴落,反手去摸背上,也是汗涔涔的……每次都是尽兴而归。
最有意思的要算“筑地洞”,当我站在那被掏得乱七八糟的稻草前,望着眼前这一个黑黝黝的洞口,心中满是成就感。谁能想到,我们几个小伙伴居然完成了这样“伟大”的工程一一筑地道。
这事儿还得从几天前说起。那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看《地道战》,影片里那纵横交错的地道,既能躲避敌人的攻击,又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可把我们羡慕坏了。我当时就一拍大腿,说:“我们也来筑地道呗!”伙伴们眼睛一亮,纷纷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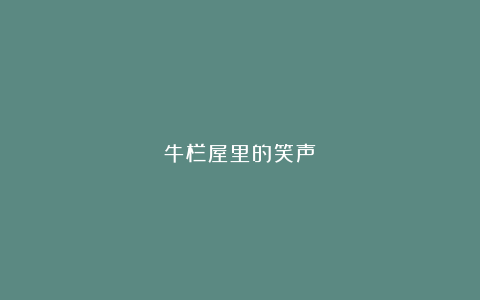
说干就干!于是,我们一面唱着《地道战》之歌:“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一面用手将那一小梱的草把子掏了出来,向里面延伸进去1米多深,一个小地道就算“筑”好了。一群小伙伴爬进地道里,策划着如何去捣鸟窝、交流着玩弹弓的技巧,讲述着《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及《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故事……直到感觉肚子饿了,才记起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
害怕回到家里被大人“惩罚”,伙伴们在离开牛栏屋时,都将自己身上那滚得皱巴巴的衣服,用小手反复进行整理。同伴之间相互寻找背心上或脑壳上还留存的细草碎屑,并给对方拣剔得一干二净,做到净身出“栏”,不露任何破绽,此时,大伙儿会意地笑了。
但是,在替对方清除头上的草屑过程中,有个别伙伴搞起“恶作剧”来,将事先藏于手心里的碎草,悄悄往站在对面的同伴头发上撒过,一时大伙儿忍俊不禁,快要笑岔了气……
当伙伴们见到这一搞笑场景,有的一边拍着小手,一边说着大人常讲的那句“三日没生意,伙计吃伙计!”的话,一群小伙伴又笑得更开心了。
我记得在那牛栏屋“乐园”里,有一次与同伴在草堆里“打地洞”时,洞里一片漆黑,可全然不知深浅,取到牛(稻)草最底层,我则从一个窟窿眼里直接重重的坠落到一头大水牯的背上,我立马顺势攀着牛栏枋爬了出来,幸好有惊无险。当同伴们见到我那个狼狈的样子,都朝着我哈哈地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大伙约定爬上牛栏屋,去掏取那些破坏生产队庄稼的麻雀窝,我们几个分头行动。我凭经验得知,麻雀的窝前会挂有一根几寸长的杂草或飘荡着一根鸟类羽毛,或许这就是麻雀窝的“门牌号”。那天,当我伸出小手直入其“老巢”,就感觉怎么不对劲呀!窝里一团肉乎乎、冰凉凉的东西在蠢蠢欲动,也许是一条黄泥蛇!吓得我魂飞魄散,手像触电似的缩了回来,庆幸的是我的手安然无恙,我不禁破涕而笑!
牛栏屋可谓是冬暖夏凉,每年开春之后,牛栏屋里的“阁楼”上存放的稻草就逐日减少,我们却仍然“眷恋”着那阁楼。星期天如果是遇到了下雨,室外不便玩耍,就相约爬到队里的牛栏屋楼上,大家用稻草编织“火车”,我们一边编织着“火车”,一边反复地唱着《火车向着韶山跑》——“呜!轰隆隆隆隆隆隆,轰隆隆隆隆隆隆,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穿过峻岭越过河,迎着霞光千万道,迎着霞光千万道……”唱着唱着大伙儿又开心的笑了。
我至今还觉得生产队那牛栏屋是个“儿童乐园”,趣味无穷,但是,我弄不懂的是如今的小宝贝,拥有着各式高档玩具,可才玩耍了一会儿,就索然无味,嚷着又要换新的。我不知是何故?试着在寻找答案,应该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了,小宝贝坐在“船”上,其玩欲随着水涨也高了。
斗移星转,随着生产队解散,集体没有了耕牛,牛栏屋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茫茫烟尘中。苦难的岁月常常成为最美好的回忆。每当我与当年的发小聚在一起谈及生产队里的牛栏屋时,大家一致公认牛栏屋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曾经从牛栏屋里传出来的一阵阵欢声笑语,至今仍然在我耳边回响。
作者简介:杨进文,苗族,笔名先进文化,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湖南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分会会员,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红网论坛特约评论员,作品散见于《中国工人》《中国绿色时报》《湖南日报》等报刊杂志。多次参加全国文学大赛,分别获过一、二、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