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前童,时光便慢了下来。卵石铺就的巷道被梅雨浸得乌亮,蜿蜒如一条条银灰色的溪流,引着人往岁月深处去。踩过“八卦水系”的石桥,明清老宅的瓦爿墙斑驳耸立,那些嵌在墙里的碎瓷片——青花的碗底、酱釉的瓮沿、甚至半枚康熙通宝——在斜阳下泛着幽微的光。镇里老人说,这是祖先“碎碎平安”的祈愿:倭寇侵袭的年代,童氏族人将残破的家当砌进墙垣,废墟里长出了新的脊梁。手指抚过冰凉的瓷片,仿佛触到六百年前战火与重建的余温。
转角的八卦亭旁斜出一株古樟,虬结的根系暴突于地面,像苍劲的龙爪扣进三合土夯成的墙基。树冠亭亭如盖,筛下碎金般的光斑,洒在青苔蔓生的《童氏祖训》碑上。倚树卖麦饼的阿婆用方言吟道:“樟树盖亭,童氏盖县。”原来明正统年间,前童人童伯礼倾尽家资捐建学宫,童氏的文脉从此生根。而今树影里嬉闹的孩童书包上印着英文单词,古樟的年轮与新生的枝叶在风里私语,吟唱着“耕读传家”的古今二重奏。
童氏宗祠的戏台正演着平调《金莲斩蛟》。旦角踩着“步步娇”鼓点翩跹起舞时,梁枋上鎏金的“狮子捧绣球”木雕倏然活了般震颤。台下梳羊角辫的女孩仰头问:“娘娘斩的蛟龙去哪儿了?”母亲笑着指向藻井:“瞧!它化作这’九龙盘顶’守着祠堂呢。”我倏然想起《徐霞客游记》开篇那句“癸丑之三月晦”,四百年前那位行者是否也曾在此歇脚?当台下乡亲为斩蛟英雄齐声喝彩,威继光的抗倭铠甲、方孝孺的铮铮铁骨、柔石的如椽巨笔,都融进铿锵的锣鼓点里,炖成一锅滚烫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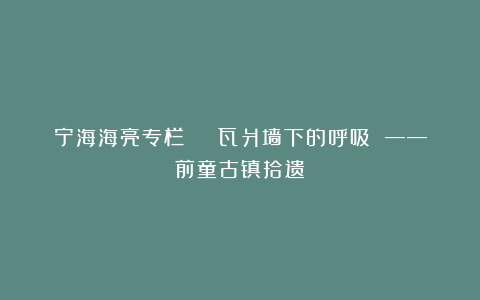
古镇鹿山村的东侧,山不高的鹿山,形似一头卧着的鹿,千百年来神鹿挡着白溪泛滥的洪水护佑着前童;明清老宅的瓦爿墙缝里,都有它祥和的气息。夕照散发的光辉,是古镇流传千年的风景。而鹿山村西侧的塔山,据传古时山上有塔,塔镇妖孽。清晨第一丝的日光照在身上,然后折射弥散整个古镇;塔山鹿山的东西呼应,鹿阜斜辉,塔峰晓日,就这样照应着、看护着古镇。此刻的一切安静平和。
暮色浸染白溪水,黄洋市老街的木门吱呀作响。竹器店的老匠人坐在门墩上劈篾,苍老的手指翻折如飞;篾条在掌心游走,渐渐编成蛏篮的筋骨。“后生仔,这手艺比不得你们敲键盘快喽。”他笑着将新编的蝈蝈笼递给我,“可宁海的滩涂若只产青蟹,不产这蛏篮,味道就少了一半。”店门前的二维码木牌与褪色的“前童三宝”招牌并肩而立,竹篾的清香混着网红油焖鸡的焦香,在晚风里酿出奇异的和谐。
归途的车载广播突然播报:“前童古镇入选省非遗保护示范区。”抬眼望去,杭绍台高铁的银龙正掠过金黄的稻田,远处海岸线的风力发电机缓缓旋转。暮色苍茫中,我突然读懂这片土地的大智慧:瓦爿墙的碎瓷守护着过往,蛏篮的经纬编织着当下,而高铁的轨迹正划向未来。真正的乡土从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门前奔流不息的白溪水——它裹挟着历史的沉香,在古老的河床里,永远向着明天奔涌。
(指导老师卢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