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张唯一留存于世的照片中,十六岁的诗人一袭黑衣,仿佛想要掩盖住“刚刚从一场凶险的肺病中摆脱出来”的现实,但消瘦而异常惨白的面容出卖了她。脖颈的束带分外引人注目,仿佛一个绝无可能忽视的象征,疾病、孤独、亲情、友人、爱情毕生束缚着她的心灵,唯独诗歌能够解开,但她从未想要解开,只是让它们各自都如其所是的存在着。我们无法不在诗人的眼神中驻留,“在那笔直而坚定的凝视中,绝无退缩之意——没有一丝轻蔑、隐晦或厌恶的痕迹。无论她当时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都无一点表露的意思。”
阿尔弗雷德·哈贝格的这本传记为我们呈现了一位白色的艾米莉·狄金森。那是一条白色的棉质连衣裙,“作为一种家居裙或外罩裙,总之是为平常的居家生活设计的,裙子的腰部比较宽松,圆领,有袖口,还有一个口袋;布料是凸纹棉布”。白色是单身与忠诚的象征,她在诗中写道:“这是一件庄严的事-我说-/做一个白色-女子-/若上帝认为我合适-穿着-/她无暇的神秘-”。
“一个讲究细节的中上阶层女子宁愿穿白色罩裙,自然不愿意接待那些穿着考究入时的拜访者。⋯⋯如果麦克家的那个人的回忆是可信的,早在1867年狄金森就开始站在’微开’的门边与来访者说话。另外,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回忆说‘艾米莉小姐’’害羞地站在栏杆后面跟我打招呼,但是从来不见我’。以上的例子可以解释为什么莱曼和克兰德尔(同是出版业人士)前往马萨诸塞州,结果只是跟诗人谈了话却’没有真的见到她’。”
黑色能溶解一切,正如白色会显露一切。黑色与白色的对立性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狄金森一生的精神样貌,这也是本传记着墨最多的地方,那就是现实与想象、友情的得到与失去、爱情的盼望与拒绝、信仰与人格独立性、孤独与社交、对家庭的依赖与对精神的追求、写作的内在性与交流的渴望、对公共生活的向往与逃离⋯⋯所有这些之间的矛盾性以及不可排解性,诗人选择了全部通过诗歌予以表现,她或许努力想要化解,但同样知道根本不可能化解。因为矛盾的特征和本质常常决定了它本身就是无法解决的,“生活是一条艰难而孤独的旅程”,生存是一个困境,只能挣扎,不可解脱。维特根斯坦说:“生活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而是一个需要体验的现实。”我们或许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待诗人、理解诗人,并从中得到如何“体验生活”的真谛。
阿尔弗雷德·哈贝格将传记的名称确定为《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已经在暗示了狄金森一生的主题,那就是“战争”和“诗”,但无疑主要是诗。她“喜欢把自己比作战火中的士兵或是为自己加冕前夜的拿破仑”,“(她)似乎觉得她的人生需要用勇气、献身、自律、荣誉这些字眼来形容:一场刺痛而甜蜜的快速战役,/就是丰富!就已足够!”。
这其中的缘由——如果万事万物一定都要有一个缘由的话(按照决定论)——我们或许只能归结为诗人所自我设定为困境的矛盾性,如果不因矛盾而被消解,就必须因矛盾而战斗。这本传记细致地为我们展现了诗歌之外和诗歌之内、但主要是诗歌之外的战斗。
对自我,她似乎想控制自己热情的天性。“我该怎么做-它如此呜咽-/这只小猎犬在我的内心/整天整夜吠叫着跳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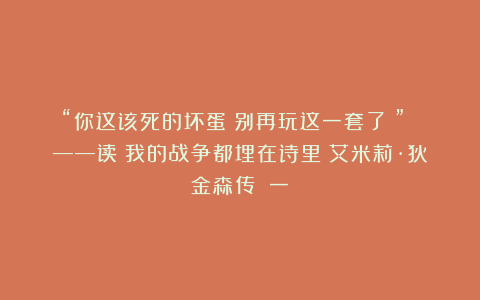
对于深爱的哥哥,无论他到了哪里,对她的喋喋不休是否感到厌烦,她都从不考虑,而是仅仅专注于兄妹之情的不可割舍和情逾骨肉。
对于苏珊,在成为她的嫂子之前和之后,狄金森从未改变过对对方的那种诚挚的情谊,即使很多时候,苏珊表现得若即若离,冷若冰霜。
对于发表与不发表,“她宣称发表对她来说,就像天空对鱼一样陌生——’如苍穹与鱼鳍无涉’。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为她表面的谦恭所误导,接下来她大胆地提出’如果名声属于我,我无法躲避她’。就像合众国初期那些闪耀的政治候选人,荣誉一定会找到她,而非相反”。
至于那些朋友,例如鲍尔斯先生、希金森先生,她一方面几乎复制了对苏珊的狂热和依恋,不停地通过信件发出灵魂的呼唤,一方面又在现实中距友人于千里之外。
我们在632页看到了极少的例外。风烛残年的鲍尔斯打起精神来到阿默斯特。[他走进狄金森宅邸,给楼上递了一张卡片,要求与艾米莉见面。回复是否定的,这对他来说是最后的稻草。⋯⋯塞缪尔“走到楼梯口,大声地坚持喊道,‘艾米莉,你这该死的家伙!别再玩这一套了!我从春田大老远过来看你。赶快给我下来。’”让维尼惊讶的是,艾米莉真的下楼了,并且看上去“光彩四射”“非常迷人”。按照比安奇讲述的版本,塞缪尔的用词是“坏蛋”,而不是“该死的家伙”。约翰逊根据诗人随后的也是最后一封给塞缪尔的信[“你的’坏蛋’,(又)我省略了形容词”]推测,完整而准确的措辞无疑是“你这该死的坏蛋”。](未完)
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年),美国诗人,25岁起隐居家中创作诗歌约1800首,生前仅发表7首,日常在温室书桌写诗并栽培异国花卉。其诗歌主题涉及自然、生命与信仰,诗风凝练婉约,善用破折号调节韵律节奏,意象清新,思想深沉,极富独创性。艾米莉·狄金森被视作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先驱,在纽约圣·约翰教堂“诗人角”与惠特曼及美国文学之父欧文并列纪念 。
评价:4.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