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之前,心里头早已描摹过她的样子。不是照着明信片上那些规规矩矩的风景去描的,倒像是在一册蒙了尘的旧书页间,偶然读到的几行零散诗句,便兀自拼凑起来,成了一个影影绰绰的梦。梦里的她,该是清冷的,带着些水汽的微凉,像一块被南太平洋的海水洗了千万年的温玉,静静地泊在天之涯、海之角。
我想象她的云。那该是怎样一种无所事事的、慢悠悠的白,一团一团,胖乎乎的,像新摘的棉花,又像贪睡的羊群,低低地悬着,仿佛一伸手,便能揪下一块来。我想象她的风,不是那种凛冽的、带着哨音的,而是润润的、凉凉的,贴着草尖儿滑过来,带着泥土与某种不知名草叶的清苦气。我想象她的静。那静,不该是死寂,而该是丰盈的,饱满的,像一滴巨大的、将坠未坠的露水,里头包裹着远山淡淡的影子,与一声若有若无的鸟鸣。
可真当双脚踩上这片土地,我才发觉,我所有的想象,都显得那般贫瘠,那般干瘪。
她比梦里更“亮”一些。不是那种刺眼的亮,是万物自身焕发出的、一种清透的光泽。那草坡的绿,是泼天泼地、毫无顾忌的,绿得那样天真,又那样深沉,从脚下一直滚到天边,与那胖乎乎的云朵纠缠在一起。云是活的,光也是活的。阳光不像别处那样直喇喇地晒下来,而是透过这云,被筛得柔和了,成了一匹宽宽朗朗的、光与影交织的薄纱,轻轻地盖在山峦圆润的曲线上。那光是会流淌的,前一秒还照亮这片草场,下一秒,便被一片路过的云的影子推着,慢吞吞地挪到远处的山谷里去了。于是,眼前的世界便有了呼吸,一明,一暗,仿佛大地在轻轻地打着节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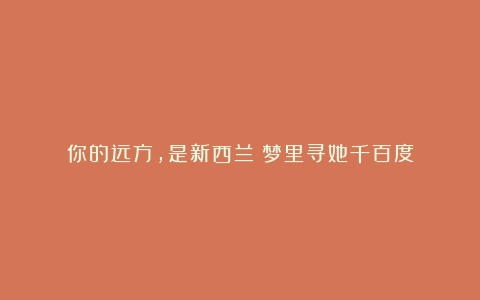
那份我曾在梦中勾勒的“静”,在这里也有了更为诗意的形体。它不在荒无人烟处,反倒是在有景物的所在,愈发显得深浓。你看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水是那种看了叫人心里一静的孔雀石绿,潺潺地,却不喧哗,只将两岸丰茂的水草梳理得一丝不苟。几株孤零零的树,站在辽阔的草坡上,枝干舒展成一个寂寥的、好看的姿态。它们什么也不说,就那么站着,便站成了一种哲学。风吹过的时候,带来一种微凉的、干净得像水晶一样的气息,那不只是草叶的味道,里头仿佛还混着远古冰川的寒意,与深海带来的咸润。
她的云是低低的,从来没有加过如此富有感染力的云朵;她的气是透明的,离得那么远你都能清清楚楚看到一切,她的风是有味道的,带着花草的香,带着湖水的蓝,若有若无,却无处不在……
我忽然便懂了。我梦里寻的那个“她”,并非某一座具体的山,某一片具体的湖。那是一种气息,一种韵致,一种未被尘嚣浸染的、天真而温柔的灵魂。我曾在书页与想象里,捕捉过她飘忽的衣角,而此刻,她正完完整整地站在我面前,呼吸着,微笑着,比一切虚幻的梦,更真实,也更像一个不愿醒来的、诗意的梦。
是我来迟了。还是,她一直在等着这样的我呢?风过耳,无人回答。只有满世界的亮光与寂静,温柔地将我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