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所写的《尼采的微言大义》是我最近尼采哲学时遇到的一篇让人愤怒的糟糕文章,一篇用大量的谎言来为谎言证道的文章。当然,尼采并不排斥“高贵的谎言”,正如他在《敌基督者》中所言:“高贵的谎言,因其良好的动机,为哲学家所肯定……最终它取决于应该服务的目的。”(很明显,尼采比起柏拉图,更像马基雅维利)但这篇文章出于什么目的呢?打着尼采的旗号,为尼采所痛恨的“律法秩序”招魂!
但是,写作此文的目的并非完全是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这会是一项异常庞大的工作),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对我没有半点好处。我写作此文更多是对近段时间阅读的一点总结,关于尼采、生机论、古代神秘主义,以及如何探索这个世界。
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一文的结论
把“权力意志”视为启蒙理性的极限,让人大跌眼镜的解读。无法想象,一个古典学学者竟看不出“权力意志”的古意,还是说他这就在给读者“下毒”了?
权力意志是什么?它是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是狄俄尼索斯,是迷醉与野性,是异教的恶魔,是无法被收编的生命活力,是内在于万物的运动冲动,是世界“变化的本原”——“我需要变化的本原和中心,从那里出发,意志迅速向四周扩散……”(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哪怕在苏格拉底的观念论奴隶哲学大爆发后,彼岸的幻觉也未能彻底抹去此岸的力量。早在希腊化时期,逍遥派大师斯特拉托便否认任何外在神明的存在,认为宇宙的运转由自然界无意识的力量维系;中世纪的“灵巧博士”司各脱,则将上帝置于万物的个体性中,主张“存在的单义性”,由此埋下了唯名论时代的种子;而等这些种子发芽,它们摇身一变,成了斯宾诺莎“能生的自然”,成了施蒂纳的“唯一者”,成了尼采的“权力意志”,成了伯格森的“生命冲力”,以及福柯、德勒兹“力的生成”……这条从前苏格拉底时代发展而来的内在性哲学谱系,既非“古典”,也非“现代/启蒙”,而是拒斥彼岸、崇拜“恶魔”/原始欲望的“异端”、“异教”、“神秘主义者”。这些敢发“不合时宜”之言的特立独行者,哪怕受尽侮辱、迫害,饱尝非议、孤独,也未曾低下他们高傲的头,又怎会阴暗猥琐地搞什么“微言大义”?
当激进的启蒙灵知派用神知反对神意,那些保守主义者便用神意反对神知,在这场“左脚踩右脚”的无聊闹剧中,彼岸和上帝的存在便被他们不怀好意地默认了。这些懦弱者在面对残忍且与我们自身意愿无关的自然时,毫不犹豫地将头埋进了沙子。他们用安详的幻想掩盖现象世界的残酷,用神知或神意的“真理性”来让人们与不可理解的世界保持距离。而这正是《玫瑰的名字》中反派约尔格的所作所为,这个丑陋的瞎子发现中世纪“存在的秩序”乱了,便满怀怨恨地用下毒杀人和自焚来抵抗这不可抵抗的一切。这自然是尼采厌恶至极的奴隶行为,但更重要的是他所谓“存在的秩序”究竟是什么?
否定现世的诺斯替教徒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人用强调分割与洁净的二元论来构筑对世界的认知,将肮脏的血肉及充满“吃与被吃”的自然逐出他们的乌托邦,所以他们所遵守的道德也是一种甘于饥饿、否定生命的道德,即尼采所言的“奴隶道德”。因而在这道德之下的世界,要么是一个因饥饿而死寂的世界,要么是一个虚伪的世界——他们不过是把所有的血腥藏在了餐桌之后。这一点不仅为鲁迅的《祝福》等文章所揭示,在埃科的《玫瑰的名字》中,以约尔格为代表的修道院同样虚伪贪婪、劣迹斑斑,对治下的“贱民”敲骨吸髓,以上帝之名做尽人间丑恶事。
祥林嫂:“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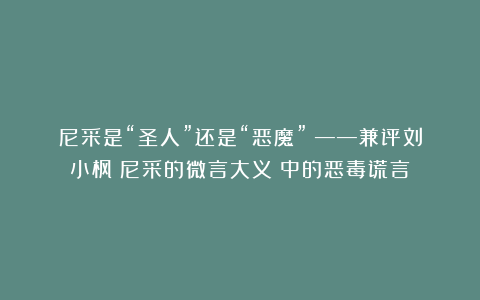
而与“奴隶道德”对应的“主人道德”则代表渴望进食与繁衍的“生命本能”(权力意志)。恰如生态学最关心的便是世界的饱食,能量的流动本身便是原因和结果,而要让一个生态系统正常运作起来,就必须有层级过渡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这便是尼采承认某种“等级制”的原因,自然生灵从不因恪守上帝的秩序而等级分明,每一个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只会在它们“填饱肚子”的斗争中不断变化,构成动态平衡的食物链/等级。在尼采的本体论中,力的差异与斗争正是构成意志的条件,而力的意志又促使力的生成。因此,强者和弱者的区别仅在于他们权力意志的强度,那些尼采意义上高贵德性无不透露着对强大生命力的赞扬。作为一股创造性的活力,尼采的高贵德性若越是被主流规训就越是失败,它代表着疯癫与魔怔,是栖居于人类内在的恶魔要从精神中分裂出来。就像茨威格在《与魔鬼作斗争》一书中的定义:“我用’魔鬼性’一词指称那种原始的、本质的,人人生而有之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将人驱逐出自身,使他超越自身,将他推进无限和本原之中。血液不安定、神经不安定、精神不安定,魔鬼就像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酵母,一种膨胀着的、折磨人的、紧张的酵母,发酵了所有危险过度、心醉神迷和自我毁灭的东西,而排斥了其他安静的存在。”尼采的超人便是这样的“魔人”,它拥有流畅的感知和无法被苦难抑制的活力,驱动着它去释放永不枯竭的攻击本能,不断向生命极限和禁忌发起挑战。
尼采对“魔性”如此着迷,究其根源,是他受到了晚期谢林所复活的古代神秘主义生机论(Vitalism)的影响,甚至尼采关于狄奥尼索斯的一切都逐字逐句来源于晚期谢林。
《谢林与尼采:释放爱之神》
与《荷马史诗》、《神谱》所代表的古希腊神话所不同,古希腊神秘学(主要是厄琉息斯秘仪和俄耳甫斯教派)所最为崇拜的神祗则是在十二主神中并未占据什么特殊地位的谷神德墨忒尔(即“地母”,荣格所言的“大母神原型”)、未有资格进入主神行列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第一次出生的狄奥尼索斯被认为是另一位地母盖亚的伴侣,最古老的“至高之神”、地母神与死而复生之神),以及在整个神话系统中只是偶尔被提到的冥后佩耳塞福涅。德墨忒尔掌管的粮食和狄奥尼索斯掌管的葡萄酒代表着希腊人最基本的生计,是生的代表,而佩耳塞福涅掌管的阴间世界代表着希腊人关于死后生活的观念,是死的代表。作为对古代荷马体赞美诗《德墨忒尔赞歌》的呼应,尼采发疯前夕定稿的《狄奥尼索斯颂歌》就是他与谢林一样将哲学视作对古代神秘学的继承的证明。而其中《阿里阿德涅的悲叹》篇章末尾新加入的狄奥尼索斯的念白(该诗最早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更是揭露了“狄奥尼索斯”的实质。
尼采《阿里阿德涅的悲叹》的结尾
在神话中,阿里阿德涅徘徊于忒修斯和狄俄尼索斯之间,她的感情从忒修斯身上转移到了狄奥尼索斯身上。一开始,她恨狄奥尼索斯。然而,被那个曾受她指点走出迷宫的忒修斯遗弃后,她被狄奥尼索斯带走,于是她发现了另一个“迷宫”。
要弄懂狄奥尼索斯为何是“迷宫”,首先需要知道忒修斯是谁?熟悉尼采生平的朋友肯定一眼能从诗中发现忒修斯暗指的是尼采曾经的好友瓦格纳,而瓦格纳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对应的正是那些声称要找回人的所有属性,克服所有异化,实现完整的人,将人推至上帝的位置的“高人”。这些“高人”是在末人时代名声扫地的前社会精英,他们包括隐修士、教宗、君王、文化名人、思辨哲学家等,查拉图斯特拉受“老预言家”(叔本华)的引诱对他们产生同情,把他们聚集起来,希望这些“绝望者”“重新笑起来”,鼓励他们要有“再走一次”的勇气,结果这些高人“他们又全都变得虔诚起来了,他们在祈祷,他们发狂了!”他们的举动直接把查拉图斯特拉气得“面孔变成紫铜色”,因而嘲讽他们”这是一种正宗的猪猡本性!一直在说咿-呀的——这是只有驴子和具有驴子头脑的人才会学好这一套。”但不怕失败的查拉图斯特拉决意“再来一次”,最后在“狮子来了,我的孩子们走近了”的预兆中,第三次下山。刘小枫等施特劳斯派长期把“我的孩子们”直接等同为“高人”,是因为施特劳斯在解读这段时,急于把“高贵等级”的“自然权利”说成尼采的“未来哲学家”主张。实际上,两年后发表的《善恶的彼岸》和尼采最后四年的其他文本中充满了对“高人”和人类的狂暴攻击,完全没有承认他们面向未来的价值和只说“是”的孩童本性。
对于忒修斯/高尚的人(《查》第二部)/高人(《查》第四部)来说,肯定就是承担,就是负责,就是承受考验,就是肩负重担。他踏入迷宫,战胜牛头怪,只是他沉重的责任。只要阿里阿德涅还爱着忒修斯这只会说“应该”的骆驼,她就只能一直活在否定生活的行动中,所有报复、狐疑、内疚和怨恨,就如同瓦格纳厚重而不间断的音乐般让人窒息,这就是《阿里阿德涅的悲叹》这首诗主要描写的东西。而狄奥尼索斯是肯定之神,祂的肯定是轻盈的肯定,祂的音乐是醉酒后的放声歌唱,祂的迷宫也是恣意生长、无边无际的迷宫。因此直到阿里阿德涅死去,她的道德之线也无法指引她走出狄奥尼索斯的爱,酒神的魔力将她从压抑与停滞的痛苦中解救了出来。
神话梗概
这则与迷宫有关的神话同样也是埃科《玫瑰的名字》贯穿全文的主题,他在《玫瑰的名字 注》中列出了三种迷宫。
埃科《玫瑰的名字 注》
从古典之迷宫到根茎之迷宫,迷宫的恶魔从米诺陶化为狄奥尼索斯,手里的阿里阿德涅不再为人提供任何出口。根茎之迷宫,或者说狄奥尼索斯本身,就是这个非人的世界。《玫瑰的名字》的主角威廉与著名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同名,因为彼时的人们终于从持续上千年的中世纪走出柏拉图主义的阴影,而启蒙观念论的柏拉图也暂时还未复活。威廉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唯名论兴起的时代,共相不再被认为是实存,而只是代指事物性质的名称。谈及《玫瑰的名字》故事设定的时代,埃科写道,“只有在奥卡姆派修士那里才能有深入的符号理论。更确切地说,这一理论以前存在过,然而以前,对符号的阐释或者是象征类型的,或者是倾向于在符号中读出理念和共相。”正如西蒙东在《想象力与创造》一书中的分析,阐释学与象征以隐含的实在论为前提,都是通向共相、激发整体的一种方法,它们将记忆-形象具体化。就像烟头对老兵的意义一样,它们的意义来自于心理记忆形象,而心理记忆形象实际上就是符号。这一符号在过去常常是基督和上帝,而在下一个时代则会是人的理性与精神。
古典的迷宫
身处两个时代夹缝中的威廉,要用何种方法来探索这个崭新的迷宫/世界呢?奥卡姆派修士那里所谓“深入的符号理论”又指什么呢?答案实际上在埃科的好友阿甘本的著作《万物的签名》里。阿甘本借着对福柯“考古学”方法的追根溯源,重提晚期中世纪明显带有唯名论特征的学说,“万物的签名”。和阐释及象征不同,“签名”将线索与细节作为意义的担保,以类比的方式使本质上沉默无言的世界变得可以理解,它并不揭示某种共相或真理,而仅仅是在探索“迷宫”的过程中为种种事物做上记号,以便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确证自身的存在。这些由签名所构成的、难以言传但通达理解力的羊肠小道,存在于生命的直觉或不断生成的知觉中,它的尽头不是外在的自然规律,而是内心世界的情动(Affect)。在这种层面上,尼采才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提出艺术与科学的“双脑制”——“一种较为高级的文化必须给人类一个双脑,可以说两个脑房,一个用来感受科学,另一个用来感受非科学”,这是因为科学家与艺术家共享着同一种迷醉而自省的酒神精神,恰如优秀的昆虫学家往往只是对昆虫有着异常且狂热的迷恋,而并不在乎自我理性的成熟和对普遍性的执念(启蒙)。也正是在这种层面上,科学才不是神学的婢女,不再是反对生命的“理论”,它无关古典、现代,乃至彼岸世界的一切纷扰,科学只是科学家在世间存活的痕迹,即“快乐的科学”。
根茎之迷宫
“丰饶的地母,引领我们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