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尼泊尔北部,一种被称作“兄弟共妻”的婚姻形式,仍在偏远山谷延续。
在这里,女性没有选择权,孩子不知父亲是谁,而冲突和沉默成为日常。
到底是文化传承,还是生存裹挟?这个制度背后藏着怎样的困境?
分裂的山地之家
“分家就是分命”,在尼泊尔胡姆拉区的上卡尔纳利河谷,老村长塔卡·普那,重复着这句村里的古训。
这个海拔3000多米的山村,土地如掌纹般破碎,每一块田都夹在岩石间,旱涝无定,十年九灾。
兄弟共妻的起点,不是情感,是土地。
村里有四兄弟,父亲去世时只留下0.8公顷耕地,和两头牦牛。
若按正常继承,四人各得不足一亩,分下去,每人都饿不饱自己,更养不起后代。
长兄坚决提出:“娶一个女人,四人共妻,田不分,人不”,这不是新提法,祖父辈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个模式在山地地区流传已久,藏语称之为“普拉”,意即兄弟共妻。
最早出现在古代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移民部族之间,为了稳固家产、避免资源外流,男人宁愿共用一个妻子。
婚姻成了压缩成本的工具。
而女性的位置,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选择之外。
村中流传的一个故事至今让人噤声:塔瑞拉,12岁时被送进帕桑家,那是个有五个儿子的家庭,婚礼前她没见过“丈夫”,甚至连谁是“大哥”都分不清。
婚约由父亲签下,新娘如一笔交易品,她唯一的“准备”,是母亲在临走前反复交代:“听话,忍耐,别惹事。”
村里老妇人说得直白:“一个女人可以养活五个男人,一碗饭分五口吃,不寒碜。”
然而谁都知道,饭能分,人不能。
每个丈夫都要求“公平”,每晚轮班,有时吵到动手,塔瑞拉头几年,几乎不敢闭眼入睡。最
初她试图讨好那个,看起来最温和的弟弟,但很快便被“家规”警告:不准偏心,不准独处,否则会被视为“破坏家庭秩序”。
这种家庭结构背后,隐藏着对女性身体、劳动和情感的彻底征用。
男人们在山上放牧、赶集、搬运货物;女人负责一切剩下的活:种地、做饭、洗衣、带孩子,连牲口棚都得打扫。
一天睡不上六小时,是“正常”,每年生一次孩子,是“期望”。
一个女人的五个孩子
每一个孩子出生前,她都要问自己一句:这一次,是谁的?
塔瑞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冬季,难产,没来得及送医,用一块生牛皮包着脐带,孩子硬生生熬过寒夜。
没人问她有没有准备好,只问“生的是不是男孩”。
按照习俗,长子默认登记在长兄名下,日后继承土地。
可亲生父亲是谁,没人清楚,也没人敢提,“我们都叫他爸爸,他也都叫我们儿子”,塔瑞拉的长子在接受采访时说。
孩子的身份模糊,情感的界限更模糊。
她怀上第二胎时,二弟正在远行,回来后不信孩子是自己的,逼她发誓、求村长作证。
第三胎开始,她彻底闭口不谈亲生父亲,连孩子的奶名都交给公婆起。
五个丈夫分摊家庭“使用权”,但不承担“责任”。
家庭内部的权力,集中于长兄手中。
他决定田地分配、牲畜买卖,也决定孩子能不能上学。
塔瑞拉曾想让女儿去镇上读书,被一句“女人识字干什么”挡了回来。
弟弟们有权,却无抚养义务,妻子的意见只在厨房里有效,出了院子没人听她说话。
当家庭内部出现矛盾,最容易成为“出气筒”的就是,这个唯一的女人。
一次因为三弟夜归误食冷饭,指责她“区别对待”,四人当场围攻,用木棍打得她肋骨断裂,第二天她依旧下田干活,无人道歉。
女性不顺从,就要服从“教训”。
长兄会说:“我们对她好,她就会服帖”,可“好”的标准只有一个:无条件服从,毫无怨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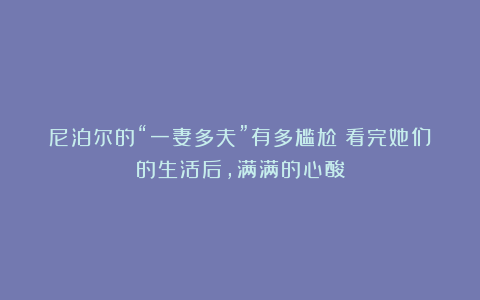
更讽刺的是,她没有离开的权利。
在尼泊尔农村,一旦女性离婚,意味着彻底“出局”:无家可归,无收入来源,子女也归丈夫家。
更关键的是,“被共用过”的女人,再难再嫁。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女人“脏”,无法再进入任何婚姻。
她曾试图逃走,三次都被村民带回,没有身份证,也没有钱,命运被户籍和亲属关系锁死。
至今她已育有五个孩子,小的才三岁,大已开始放牧,她说:“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这样活,但我知道,他们会记得我怎么熬过来的。”
兄弟之间,没有兄弟
在表面平静的山村之家,真正的斗争从不是女人之间,而是男人之间。
塔瑞拉的丈夫们从小一起放牧、一起长大,结婚那天,还曾在火堆旁发誓“永不分心”。
可这份誓言,在婚后两年彻底撕裂。
三弟动手打了长兄,因为发现他连续三晚未轮班,却让塔瑞拉悄悄陪睡。
这是兄弟共妻最深的裂缝:资源是共享的,情感不是,妻子的偏好、孩子的血缘,成为潜在的战场。
没有人愿意承认“她更喜欢谁”,但所有人都在争。
长兄拥有权威,弟弟们有不满,却无权改变规则,所有人都对“轮流制”口头遵守,却都想暗中多占一晚。
谁多睡了,谁就被嫉妒;谁得了宠,谁就被孤立。
共妻的婚姻制度,看似解决了财产分割问题,却制造出更隐蔽的权力斗争。
家里的牛卖出去,该由谁保管钱?孩子病了,谁该去请神医?三弟带回山药,却被四弟藏了一半。
“同床共妻”并未带来团结,而是加剧了猜忌、争夺与冷战。
女人既不能表达喜恶,又不能表现中立,她必须随时“端平一碗水”,否则就是制造兄弟纷争的“祸根”。
她曾试图让孩子们,称四个男人为“叔叔”,换来的是一顿鞭打和家庭会议:“你让孩子乱认爹,是想离间我们?”
村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有女人被指“挑拨兄弟感情”,最终被逐出家门,孩子归宗族,由村长重新安排婚配。
在这样的制度下,女性没有选择丈夫的权利,却要承担维护兄弟和睦的责任。
改变,从不是因为制度想变
这种制度,不是自己衰退的,是有人在死命挣脱。
在尼泊尔中部的戈尔卡镇,一家非政府组织“妇女之声”,悄悄建立了一所织布小作坊。
屋里坐着八位女子,其中五人来自兄弟共妻家庭,她们每天织地毯、缝手包,挣的钱不多,却是她们人生第一次握住自己的收入。
其中一人名叫帕米,17岁那年被送入三兄弟家,三年内生了三个孩子。
她说:“他们打我,我只能哭;现在我赚钱,我能走出去。”她没离婚,却开始白天独自外出,晚上不再挨打。
她开始学习尼泊尔语,而不是只会本地方言,还拿到身份证。
丈夫们一开始反对,但组织帮她找到卫生署的育儿补贴,家里经济改善后,反对声音变成沉默。
她说:“钱,是唯一让他们闭嘴的东西。”
在更偏远的山区,变革更为缓慢,但年轻一代已出现裂痕。
14岁的吉米,被父母安排与堂兄弟共婚,她拒绝,在学校写下求助信。
老师将她带到县城,之后安排她进入寄宿学校,如今她读到高三,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这不是个例,而是一种觉醒。
2017年,尼泊尔议会通过《婚姻法修正案》,明文禁止任何形式的一妻多夫制,并提出“以女性意愿为前提的合法婚配”。
但政策文件传不到山口,村里人只听族长一句话。
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批评尼泊尔“以传统之名,剥削女性之身”,并提出具体改革建议。
政府开始为女性教育拨款、设立育儿补助,但基层推行困难。
有的妇女宁愿忍受,也不敢离开。
她们说:“出去后,我是谁?住哪儿?吃什么?”没有人教她们如何独立生存,也没有安全网络接住她们的坠落。
但裂缝已经出现,帕米、吉米,还有更多无名女性,正用自己的方式,拆解这套体系。
这不是大刀阔斧的革命,而是一次次小小的“背叛”,她们偷偷藏钱、偷偷联系组织、偷偷告诉女儿:“以后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过。”
改变,不会一夜之间发生,但一旦开始,就不会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