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汇之间的权衡制约着树木如何在生理、生态和进化上对环境做出反应。这些权衡通常分布在一个连续体上:从高生产的生长到保守的对冲策略。储存在活树细胞(称为碳储存)中的非结构碳水化合物NSCs如何适应这种权衡框架尚不清楚。
我们利用来自同质园的种内遗传变异数据和来自全球数据库的跨物种表型变异数据,研究了生长与储存之间的关系。
我们证明了存储是积极积累的,这是保守的、押注生命史策略的一部分。储存的积累是以牺牲物种内部和跨物种的生长为代价的。在欧洲大叶杨Populus trichocarpa中的遗传权衡研究表明,基因型投资的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木材面积生长,它们就会损失1.2至1.7个单位的储存量。在不同物种中,每增加一个面积生长单位,树木的茎和根的储存量平均减少9.5%和10.4%。我们的发现影响了我们对基本植物生物学的理解,将储存纳入广泛使用的描述生命史策略的生长–生存权衡谱,并挑战了当今生态系统模型中对被动储存的假设。
-
当自然选择同时作用于共享有限能量资源的多种性状时,通常会形成权衡。对于获取资源手段有限的固着生长的植物而言,确定它们如何分配资源对于理解基本生理过程、确定生态群落中的功能作用以及预测当前和未来气候下的成功至关重要。
-
碳分配权衡模式被认为是植物生存策略变化的基础,植物生存策略通常遵循生产力和竞争(以生长为代表)vs寿命和持久性的投资轴。
-
人们一直争论储存在植物体内的碳(NSCs)如何与生长相关,从而影响树木的碳预算。常见的被动积累假说逐渐被质疑,新假说认为储存本身是一个竞争性的汇,并已演变为以牺牲增长为代价的积累。对植物对环境干扰的反应的研究证明储存是植物的一种保障,能够为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碳供应波动(如夜间、休眠季节和环境干扰)提供碳。但目前的研究报告的是对环境的可塑性反应,而不一定是可进化的生活史策略。是否也存在基因变异,导致一些树木储存更多的碳,而其他个体储存更少的碳?这种变异与生长中的遗传变异有关吗?为了真正理解碳储存是否是一个以牺牲增长为代价积极分配的优先汇,我们必须在基因水平上证明储存的变化会随着增长而变化,并可以根据选择而进化。
-
我们在同质园中研究欧洲大叶杨(Populus trichocarpa)的生长储存遗传权衡。同质园从不同范围的种群中挑选个体,并在同一地点种植。因此,在个体之间观察到的差异被认为是遗传的,而不是可塑性的。我们假设生长和储存之间存在权衡,反映了生命史策略的保守到高产的范围。接下来,我们将研究不同物种的生长和储存权衡,看看欧洲大叶杨体内发现的模式是否能在更高的分类尺度上重现。遗传的种内权衡揭示了物种的进化潜力和局限性,而种间权衡则为我们理解区分物种的生态学和生命史策略提供了信息。
-
数据预处理
-
核心分析
-
特异性内部权衡
-
种间权衡
我们的研究首次将储存确立为一种优先的碳分配汇。之所以长期难以在不同生物组织层级上证明“生长—储存”权衡的普遍性,部分原因在于先前讨论的其它变异来源会掩盖这种模式。储存与生长之间的这种关系,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植物生产力模型的结构与参数化方式。当前多数模型把储存视为一个“黑箱”,仅用来表示碳供给与生长、呼吸和繁殖需求之间的差额。尽管已有进展将储存进一步划分为“快速”和“缓慢”碳库,以反映其被利用的时间尺度,但截至目前,还没有模型允许NSC碳库与其他碳汇直接竞争资源。这一结果具有广泛影响,因为理解碳分配权衡对于我们在当下与未来环境下预测植物的成败至关重要。
-
上半部分:主动权衡(Active: Tradeoff) ——情景 I 和 II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基因型天生就具有不同的策略:一个偏向生长(生长多,储存少),另一个偏向储存(储存多,生长少)。野外观测到生长和储存的负相关,这很可能是由不同基因型之间存在真实的主动权衡策略所驱动的。
-
图 (a) 上半部分:我们在野外直接观测到,生长越快的个体,其储存量越低,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负相关直线。 -
图 (b) I 和 II:这解释了这种负相关是如何产生的。无论是资源差的环境1还是资源好的环境2,基因型1(星形)总是比基因型2(三角形)储存更多但生长更少。同时,两个基因型在环境2(资源好)中的生长和储存都高于环境1。 -
图 (c) I 和 II:当我们只看环境1或只看环境2时,连接两个基因型的线都是负斜率的。这揭示了在相同的碳供应水平下,它们之间存在着“要么多生长,要么多储存”的遗传权衡。 -
图 (d) I 和 II:当我们用统计方法校正了环境(碳供应)的影响后,这种内在的负向权衡关系就清晰地显现出来。
-
下半部分:被动过程(Passive: No tradeoff)
在这种情况下,基因型之间没有内在的策略差异。储存仅仅是碳供应超过生长需求后的“溢出物”。
情景III:野外观察到的正相关,很可能只是因为环境(碳供应)的可塑性导致的假象——资源好的地方什么都多,资源差的地方什么都少。这并不能证明储存是主动过程。
-
图 (a) 下半部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生长越快的个体,其储存量也越高,呈现出一条正相关直线。 -
图 (b) III:这解释了这种正相关是如何产生的。这里没有基因差异,只有环境差异。在环境2(资源好)中,植物有充足的碳,所以它既能快速生长,又能储存大量NSC。在环境1(资源差)中,碳供应不足,所以生长和储存都很少。 -
图 (c) III:在任何一个环境中,由于没有基因差异,所以只有一个数据点,无法体现权衡。 -
图 (d) III:当我们校正了环境(碳供应)的影响后,生长和储存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一条水平线),因为储存是被动的,不存在遗传上的权衡。
-
图 (a) 下半部分:这个情景同样在野外观察到正相关。 -
图 (b) IV:这是最复杂但最重要的一种情况。这里实际上存在主动权衡(基因型1偏储存,基因型2偏生长)。但是,基因型1(星形)不仅偏向储存,它本身获取碳的能力(碳供应)也更强(注意看,星形在两个环境中的总柱高都高于三角形)。因此,尽管它把更多的比例用于储存,但其强大的碳供应能力使得它的绝对生长量依然不低,甚至可能高于在差环境下偏向生长的基因型2。 -
图 (c) IV:在同一环境下,我们依然能看到负斜率的遗传权衡。 -
图 (d) IV:当我们校正了“碳供应”的遗传差异后,真实的负向权衡关系就会被揭示出来。
-
核心思想总结
①野外观测不可靠:简单地在野外测量生长和储存并做相关性分析,可能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负相关可能是真权衡,而正相关可能是环境假象,也可能是被掩盖的真权衡;②区分遗传与环境是关键:要证明NSC储存是一个主动过程,核心在于证明这种分配策略(生长vs.储存)是可遗传的,并且存在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③最终的检验标准:最可靠的证据来自于图(d)的分析。在统计上剔除了所有“碳供应”差异(无论是环境造成的还是遗传造成的)之后,如果生长和储存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那么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说,NSC储存是一个受主动调控的、存在真实权衡的生命策略。
图2.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将复杂的多变量数据(供应、生长、储存性状)可视化,直观地揭示了不同基因型之间的策略差异。这张图有力地证明了,在Populus trichocarpa这个物种内部,确实存在一个可遗传的、在“生长”和“储存”之间的根本性权衡,并且这种权衡策略与物种的原产地纬度紧密相关,表现出局部适应的特征。
PC1轴(横轴):这是最重要的变异轴。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史策略轴”或“碳供应vs.储存权衡轴。向左(负方向):由箭头叶面积指数、生长季长度)和基底面积增量,即生长速率所驱动。这代表了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策略:拥有更大的冠层、更长的生长季,从而实现更快的生长。向右(正方向):由箭头根系NSC浓度和茎干NSC浓度所驱动。这代表了一种“保守储存”的策略:将更多的碳资源用于储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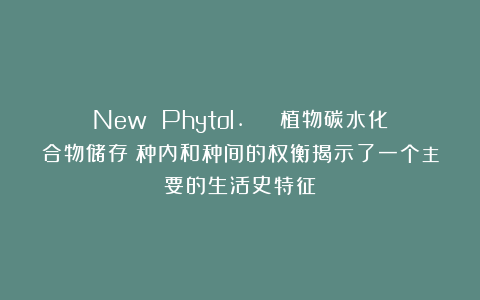
图3. 证明了在Populus trichocarpa物种内部,生长与储存之间存在一个真实的、内在的权衡关系。这张图的巧妙之处在于,它通过统计方法剥离了“碳供应能力”这一混淆因素,从而揭示了被掩盖的真相。图1(概念模型)告诉我们,要证明NSC储存是一个“主动过程”,就必须证明在剔除了碳供应差异的影响后,生长和储存之间仍然存在一个负相关关系。图3正是对这一核心假说的直接检验。
分析过程:研究人员首先用每个基因型的“碳供应能力”(PC1得分)去预测它的生长速率和NSC储存量。然后,他们计算出“实际观测值”与“模型预测值”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残差.因此,这张图展示的是:在排除了所有基因型在碳获取能力上的先天差异之后,它们如何分配剩余的碳资源。这完全对应了图1(d)中的逻辑.
这张图的结果揭示了:
-
NSC储存是一个主动过程:因为在控制了碳供应这一变量后,生长与储存之间存在显著的、可遗传的权衡关系。这否定了储存是被动“溢流”的假说。 -
权衡关系是真实存在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之前观察到的正相关是一种假象,是由不同基因型生产力差异造成的。当所有基因型被置于“同一起跑线”(即校正了碳供应能力)上时,它们在如何使用碳水化合物上,表现出了明确的“投资生长”或“存钱保命”的不同策略。
图4. 将研究的视角从单一物种内部的变异扩展到了跨越全球多个生物群落的不同物种之间,旨在检验“生长–储存”权衡是否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生态学规律。这张图通过整合来自全球已发表文献的数据,分析了不同树种的生长速率、木材密度与其在茎和根中的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NSC)储存量之间的关系。
-
跨物种的“生长–储存”权衡得到证实(图a和b)
-
“储存”策略与“慢”生活史策略协同进化 (图c和d)
图(c)和(d)展示了茎和根的NSC储存浓度与木材密度之间的关系。木材密度是衡量植物“生活史节奏”的一个经典指标:低密度木材通常与快速生长、短寿命的“快速投资–快速回报”策略相关;而高密度木材则与缓慢生长、长寿命的“慢投资–慢回报”保守策略相关。核心发现:在这两个图中,我们观察到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线斜率m分别为5.7和5.5)。这意味着,木材密度越大的物种,其在茎和根中储存的NSC浓度也越高。
权衡定义了生命的极限,并在多个组织尺度上保持生物多样性。当自然选择同时作用于共享有限能量资源的多种性状时,通常会形成权衡。对于增加资源获取手段有限的生物,特别是固着树种,确定它们如何分配资源对于理解基本生理过程、确定生态群落中的功能作用以及预测当前和未来气候下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权衡的重要性导致了数十年来对木本植物如何在代谢、生长、繁殖和防御的竞争需求中分配其有限的碳供应的研究,即碳分配。碳分配权衡模式被认为是植物生存策略变化的基础,植物生存策略通常遵循生产力和竞争(以生长为代表)与寿命和持久性的投资轴。沿着这条主轴的权衡支撑了我们对基本植物生物学和群落动力学的理解,现在正被用来降低植物系统的复杂性,以更好地参数化生态系统模型,这是预测全球气候的关键工具。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储存或存在于木质组织中的不稳定非结构碳水化合物(NSCs)如何与生长相关,从而影响树木的碳预算。一种假说,即被动积累,认为储存是最低优先级的库,并在其他库需求被满足后作为光合作用的副产品积累。根据这一假设,储存是一种可塑性特征,只有在生长、防御、繁殖和所有其他碳需求得到满足后,供应过剩,储存才会增加。尽管反对这一假设的证据越来越多,但在大多数植物模型中,储存库通常表现为被动的,碳水化合物只有在满足其他需求后才能积累。另一种假设是,主动积累,即储存本身是一个竞争性的汇,并已演变为以牺牲增长为代价的积累,作为增长–生存权衡的一部分。主动积累可以通过上调细胞中的碳水化合物储存或下调生长或其他碳汇来实现,有时被称为“半主动储存”。为了进化,储存必须是一种可遗传的特征(即变异是遗传的,可以传递给后代),可以选择以牺牲生长为代价增加。这种基因权衡表明,适应性选择或基因组约束形成了一种关系。无论哪种情况,这种关系都是两个性状之间遗传权衡的结果,并传递给后代(高储存和低生长的后代将产生高储存和低生长的后代,反之亦然)。在主动储存假设的情况下,我们预测储存投资将沿着植物生命史特征的竞争与寿命谱下降,其中,作为保守的赌注对冲策略的一部分,对储存的大量投资在更随机或极端的环境中提供了适应度效益。
迄今为止,在理解碳水化合物储存在植物对极端环境(即储存可塑性)的反应中的作用方面取得了进展。储存通常被认为是植物的一种保障,为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碳供应波动(如夜间、休眠季节和环境干扰)提供碳。在NSCs的成分中,只有淀粉除了储存之外没有其他功能。可溶性糖是呼吸和其他代谢功能的底物。然而,由于淀粉是可溶性糖的来源,可溶性糖用于合成淀粉,因此两个可互换库(NSC)的总和通常被用作储存的衡量标准,即使在任何给定时间只有一小部分是长期储存的。否则,单独测量淀粉可能会低估储存量,特别是已知糖会在季节性到每小时的时间尺度上进出淀粉。
事实上,在胁迫开始时具有较高的NSC储存已被证明可以延长热带幼苗在干旱和阴凉条件下的寿命。这些结果表明,更高的储存可能确实有选择性的好处。类似地,对植物对环境干扰的反应的研究,如落叶、干旱,甚至CO2胁迫,已经证明,NSC储存可以在干扰后维持或增强,通常以牺牲生长为代价。虽然这些研究表明,与其他用途相比,投资储存有暂时的适应性益处,但它们报告的是对环境的可塑性反应,而不一定是可进化的生活史策略。是否也存在基因变异,导致一些个体树木储存更多的碳,而其他个体储存更少的碳?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变异与生长中的遗传变异有关吗?为了真正理解碳储存是否是一个以牺牲增长为代价积极分配的优先汇,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并在基因水平上证明储存的变化会随着增长而变化,并可以根据选择而进化。
证明分配特征之间的权衡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源和汇的可塑性和遗传变异都可以掩盖潜在的模式(见图1)。因此,测量两个性状之间的明显关系可以反映任何数量的过程,如碳供应的遗传变异(图1ii,iii),而不是真正的权衡。用买车和买房之间的权衡来比喻这种现象最恰当不过了。我们直观地知道,个人必须选择将多少财富分配给每一种财富,因此存在一种权衡。然而,如果对所有个人进行考察,汽车和房屋投资之间往往存在正相关关系,因为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可以在这两方面花费更多的钱。正如个体的财富不同一样,树木产生碳供应的能力也不同,这既是由于生长条件的可塑性变化,也是由于对供应相关性状(如叶片脱落时间)的基因控制。由于碳分配权衡本质上是由对有限碳供应资源的竞争形成的,并且有助于植物碳供应的特征在不同程度上是可遗传的(见材料和方法一节中的“碳供应”),我们在评估碳汇之间的权衡时必须考虑碳供应的可遗传差异。
物种内存在生长–储存权衡
我们首先确定碳汇(包括储存)的变异是可遗传的。由于遗传率是一个同质园中的相对指标,因此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测量结果与在不同环境中使用相同基因型进行的研究中对生长、物候和碳储存的测量结果相似。我们发现所有分配性状的遗传率都很重要,因为遗传变异会传递给后代,并在选择过程中进化,从而产生分配权衡。为了进一步证明碳储存是由树木主动分配的,我们在储存和生长方面量化的遗传变异之间寻找负相关或权衡关系。然而,在考虑碳汇的变异时,我们还必须考虑碳供应的变异。对于像欧洲大叶杨这样的高产物种,碳供应的变化可能会掩盖碳汇权衡的信号(图 1)。当我们用性状的 PC1 来近似地控制碳供应的变化时,我们发现生长和储存从正相关转为负相关(图 3)。我们确信 PC1 准确地捕捉到了供应量的变化,因为它与使用相同基因型、生长季长度和纬度测量的模型碳供应量密切相关,而这些都是已知的年光合吸收代用指标(图 S6)。我们所发现的权衡存在大量潜在的遗传变异。基因型每投资一个单位的生长,就会放弃 1.2 到 1.7 个单位的储藏,或者基因型每投资一个单位的储藏就会放弃 0.6 到 0.8 个单位的生长(图 3)。因此,在树木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储藏投资的少量增加可能会导致竞争性生长的巨大代价。
有趣的是,我们对 PC1 所代表的碳供应量变化的估计也包括了高增长和高储存量。从统计学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比较生长/储存和供应的残差之前,我们最初发现生长、储存和供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可能具有生物学意义。虽然有些植物在储存中投入的碳比例相对高于生长,但它们的总体供应量仍可能高于其他植物。因此,这些植物可能有一个额外的被动储存库,并且由于其供应过剩,生长率也相对较高。事实上,当供应过剩时,植物可以被动地积累储存,同时维持一个储备库,这一观点已被普遍接受。
虽然我们在本研究中考虑了生长和储存,将储存确定为优先吸收汇,但现在需要更多地关注储存如何与防御、繁殖和新陈代谢等其它吸收汇发生变化。在物种内部,防御有时会与生长相互抵消。因此,如果生长和防御是共生的,那么储存和防御也可能是共生的。此外,储存的碳水化合物可能为制造某些防御化合物提供基质或能量,使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繁殖与c储存之间的关系也是理解的关键,因为选择作用于遗传变异以提高适应性,而适应性被定义为繁殖成功率。了解储存与繁殖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储存是如何通过进化形成的,从而了解是什么驱动了储存在地形和时间上的变化。最后,我们在这项研究中只考察了次生生长(直径扩大)。尽管已知 DBH 与生物量有很好的相关性,但对初级生长的额外考虑可能会在未来的研究中提供更多信息。
我们在此发现的主动积累是机制性的,这意味着增加的储存可以通过上调细胞中碳水化合物的积累或下调生长或其他碳汇(有时称为 ‘半主动储存‘)来实现。无论哪种情况,都有证据表明,在某些环境条件下,较高的储存量可能会使个体适应性受益。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在某些环境条件下,较高的储存量会带来适应性优势,这可能会导致局部适应模式(即在某些环境中选择高储存量)。然而,我们几乎没有发现在权衡策略中进行局部调整的证据;相反,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种群内变异。这种变异可能至关重要,使得树木这种寿命长且固着生长的生物,能够在时间或微环境上异质的环境中持续存在。鉴于对选择的进化响应需要遗传变异,我们在欧洲大叶杨种群内观察到的生长–储存权衡中的丰富遗传变异有望促进对未来环境变化的进化响应。
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毛欧洲大叶杨的生长和储存之间存在明显的遗传权衡,表明储存会主动竞争碳。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权衡中存在局部适应性的证据。要进一步了解这种权衡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是如何维持的,还需要对哪些条件有利于高储存者和快速生长者进行研究。此外,要将碳储存作为一种竞争性碳汇,就必须对碳储存与其他碳汇(如抗病性、新陈代谢和繁殖)之间的关系开展新的研究。
储存与生长之间的种间权衡
我们在欧洲大叶杨中的发现证实了生长–储存权衡的存在和演化。为进一步判断我们所发现的碳的主动分配是否不仅限于欧洲大叶杨、而且构成植物生活史策略的一个基本方面,我们分析了不同树种中生长与储存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利用全球碳储量测量数据库,我们发现不同物种的年增长率与碳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支持了两者之间的权衡(图4)。面积每增加 1 平方厘米/年,树木茎部和根部的储量分别减少9.5%和 10.4%(图 4)。生长与储存之间的权衡遵循既定的从保守–竞争的谱,生长缓慢的保守物种储存更多,而生长迅速的竞争物种储存较少。原木蓄积量与木材密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图 4c、d)进一步强调了这种保守与竞争之间的权衡。木材密度每增加 0.1 克/厘米-3,茎部和根部的碳储量分别增加 76.8%和 73.3%。这些关系表明,对高木质密度的投资可能代表了一种进化的保守、‘安全 ‘的生长策略,但却牺牲了高效、快速的生长。
我们特意选择了研究总的 NSCs 作为储存指标,而不是仅仅研究淀粉,因为淀粉是严格意义上的储存分子。不过,我们在休眠期早期就进行了种内采样,以确保我们能捕捉到最大的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在植物薄壁细胞中发挥着多种作用,例如扮演着呼吸和渗透调节的基质。因此,我们看到的变化可能部分是主动分配给代谢需要的结果。直觉上,我们会认为生长速度较快、代谢活跃的生物量比例较高的树木代谢呼吸分配较多。如果是这样,由于代谢需求的积极分配而产生的变化将削弱而不是加强我们所发现的权衡。最后,在所有组织中,糖分都会以季节、每日甚至每小时的时间尺度在淀粉中进进出出,而总 NSCs 则更为稳定。糖和淀粉之间的这种来回转换与淀粉水解酶对环境的敏感性有关,并表明仅研究淀粉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没有控制不同物种之间碳供应的变化,但仍然看到了权衡。这表明,在这一系列物种中,碳供应的变化小于碳汇分配的变化(图 1i)。物种内与物种间碳供应与碳汇变化的相对数量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不同尺度上考察时,性状之间的关系会被打破或发生逆转。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强调,叶片质与其他叶片经济学谱(LES)性状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分类尺度上保持不变,而叶片寿命与单位面积叶片质量(LMA)之间的关系在物种内为负,但在较高的组织水平上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在考察不同物种时,叶片寿命呈现梯度分布,从叶片廉价的落叶被子植物物种到针叶树物种,针叶树物种的针叶寿命很长,它们在针叶上投入了大量资源。然而,在物种内部考察时,落叶物种的叶片寿命更多地反映了生长季节的长度,或者说近似于碳供应。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缺乏热带生物群落的样本,这也可能让我们在没有控制供应的情况下看到了一种权衡。热带物种的生产力很高,因此,如果包含更多的热带物种,物种间的供给变化可能会超过吸收汇的变化。从图 4中可以看出这种模式,热带物种分别向高生长/高储存或高储存/低密度象限移动。总之,虽然碳供应可能会混淆模式,但只有在较小的分类学分析尺度或考虑较大的生产力范围时才会出现问题。
虽然我们的数据库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并首次提供了种间生长–储存权衡的证据,但这些数据仍不完善,因此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也需要今后进行研究。首先,我们只研究了茎和粗根储存中的大量NSC(葡萄糖、果糖、蔗糖和淀粉)。其他器官(如枝条)和化合物(如糖醇和脂质)也可能有助于储存预算。虽然器官的储藏量往往是相关的,而且整体测得NSCs一般能捕获约85-95%的碳储量,但未来的研究应考察其他化合物和器官对整个树木储存的贡献程度。其次,跨物种权衡本质上并不代表基因型差异,而是反映了对环境的可塑性反应,或本质上是物种的地理分布。然而,我们发现了一种可遗传的权衡,加上之前有证据表明 LES 性状很可能是由局部适应性进化形成的,这使我们更有信心地认为,我们发现的跨物种权衡也反映了一种进化反应。无论如何,我们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检验遗传的高储存量在某些环境中是否具有适应性,并证明储存梯度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第三,与特异性内部分析一样,我们没有考虑其他碳汇。其他碳汇与储量之间的关系可能部分解释了我们的模型R2较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图4a,b)。最后,我们的标准是测量时间在 4 个月或以上的研究,这表明我们可能没有捕捉到所有情况下的季节性最大值。不过,我们对物种进行了总结,以增加考虑的测量次数,并进一步检查数据是否存在偏差。三分之二的研究持续了一年或更长时间,而在其余三分之一的较短时间内,我们都在 9 月至 2 月间进行了测量,而这正是许多生物群落的季节性最大值,这表明我们很可能捕捉到了所考虑物种的最大值或接近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