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给花们浇水,发现很多马蜂萦绕。又有马蜂来筑巢了?寻着马蜂踪迹,靠女墙树间花丛搜寻马蜂窝巢,未见。观察马蜂出入,发现另有“源头”,竟在雨棚里面。
——才去北京几天,它们居然在雨棚顶靠南窗筑起一窝蜂巢,马蜂们正忙碌出入。
这位置太闹心了,正处楼梯口头顶。我一上楼,抬头赫然,伸手可触,且必须从蜂群穿过。略略惊骇时,心也柔软赞叹:这巢漂亮,堪称巧夺天工。如果不妨碍我生活,它们在此安家落户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可是,被马蜂蛰真不好玩。虽然,马蜂一般不会主动发起攻击,但它们非常敏感、自卫意识超强。日常频繁上下出入,我们怎能保证不会无意间惹到它们?就算我特别小心可刻意回避,却无法保证老婆孩子也能确保无虞,一不小心被蜇是大概率事件。
这马蜂窝,要不要捣毁,我一时颇费思量。
这幢楼伫立万石山半山腰。我加楼上有个露台,站女墙边伸手能摘到山上树叶。常有麻雀、八哥、鹦鹉、长尾雉鸡等鸟雀飞临,多半是来觅食的,有时在我茶桌旁的自动流水接水喝。也有松鼠从墙头蹿上来,警惕灵巧躲闪光顾。入夜和凌晨时分,蛐蛐儿们和叫不出名的虫子喋喋叫个不休,走近就踩熄了,一离开叫声如合唱重启,总也找不见它们的影子。日常倒腾花盆清理露台时,会赶出这种那种、这样那样的虫子,钻土或四散逃奔,没法把那些悦耳的鸣叫与它们一一对号入座。
离自然很近,可以说密切地融入了自然,这甚合我意。与野生生灵们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与其建立友好和谐的沟通,乃至成为朋友,温馨和美。至于那些惹人不快的生灵,我以为是可以也应该宽怀的:既选择了这个山麓小楼楼顶住房,就断不了要与这些“原居民”打交道,顺其自然与它们共享时空和平共处,各得其乐。
但如马蜂般引我不适的东西不断敲打我已然相当强健的神经。撑起六只脚看起来巴掌大的蜘蛛黑黢黢很瘆人;成团成窝、成群结队的蚂蚁稀松平常到处掏洞;几乎所有花盆底下都有密密麻麻红色细小蜈蚣,蠕蠕爬动很扎眼;花盆里还有屎壳郎和一些叫不出名的爬虫;也有老鼠出没……。
苍蝇、蚊子、蟑螂等飞虫更屡见不鲜。它们尤其胆大妄为,敢与我贴近斗智斗勇。不打,它们绕圈纠缠,或停那儿一动不动;出手打去,却早已无影无踪……
更离谱的,一二楼邻居反映,曾发现有蛇爬上纱窗,试图进入室内,还相当粗长……
不禁反思自己对这些自然生灵的好恶分类。人作为万物灵长,主宰世界,能与各种生灵互不侵害、友好相处多好。那些如马蜂、蜈蚣、蜘蛛、蟑螂、蛇蝎之类貌似丑陋、肮脏、有攻击性、侵害力的生灵,绝大多数奉行“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生存法则。大家互相让渡、宽容,难道不能良性互动和谐共处吗?
马蜂、马蜂窝问题还在纠结,接下来的事就不仅是犹豫、思量了。
晚上,正端坐露台看电视,一条半尺多长的大蜈蚣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红红赤赤,大摇大摆爬上地毯,百足运行,走走停停。我一时汗毛倒竖,毛骨悚然。
打还是不打,我意识里瞬间下了结论:不打。这么大,得成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吧?都要成精了,它或许比我入住这里还早呢。何况,我住这10年了,它从没惹我,凭什么见而杀之?它也是一条命啊!
在这无常的空间,我们不期而遇,这里面也有缘份和因果呢。
面对悠然现身的大蜈蚣,我没动。像看表演一样,惊惧中我眼睁睁看着那条长大的蜈蚣这儿嗅嗅、那儿拱拱,有时还翘头举头,很悠闲的样子,逐渐消失在电视柜下,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马蜂、蜈蚣,蜈蚣、马蜂……这两生灵在我意识里或交替出现,或搅在一起,一时难以释怀。
善念、善意在纷繁的生活流里受到强烈跌宕、冲击。
为了防止蜈蚣等虫子钻进室内,我早就在门边缘封上胶皮,并设置了隔开楼上楼下的铝合金封闭门。黄昏、晚上上楼,我都小心翼翼打亮手电,看清楼板,避免踩到蜈蚣、蜘蛛之类。
为了向各路自然生灵释放善意,这些年来,我做了很多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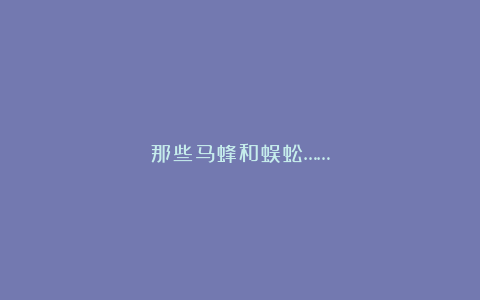
清除了女墙上阻挡松鼠通行的石块、花盆等,专门给松鼠们持续投喂核桃、开心果等坚果,期待它们可以跟我一起吃核桃、剥松子;
买了鸟食定期在女墙和顶棚上投喂,还在高处挂了不关门的鸟笼,盼望各种鸟来陪我安居,期待它们有一天敢落在我的头上、肩上、手臂上与我嬉戏;
我也对虫子们给予了特别的忍让,除草、翻盆从不伤害它们。即使它们把我的白兰、三角梅、茶花等花叶啃光、锈光,我也从不打农药,而是采取生态环保办法,护树苗、拒杀戮。
但不知是各路生灵不理解不领情,还是我的善意之真诚没有达到令它们完全理解接受的程度,至今我仍是它们高度戒备的对象,躲我像躲恶魔一样。
终于,我彻底恼怒了。
好不容易遇到台风天之后的一个凉爽夏夜,我在露台喝酒吃坚果看电视,正悠然怡然呢,猛不丁耳朵轰然反应,右手臂被火烫针扎一样爆烈刺痛,抬臂就见一只马蜂正飞离眼前。
我被蛰了,“作案”的应该正是那只刚刚飞走的马蜂。
这痛持续难忍越来越剧烈。先是红了一圈,接着是肿起一块,随后整个小手臂红肿起来,胀痛欲裂,火辣难忍……
捣了,捣了,必须捣了。我瞬间判了那马蜂窝的“死刑”。
站起身去窥探那隐于昏暗中的马蜂窝,焦躁爆火中,我未敢轻举妄动,打算明天设法清除这窝马蜂。
据说,清除马蜂窝可联系专门机构专门队伍。我不想麻烦他们。
这窝看上去像一只大海螺,两边有防风防水透气口(如文首图),下部头端有个拇指头大的出入口。马蜂虽多,但每次只能出入一只,晚上基本没有马蜂出入。晚上是最好的解决时机。方法我已想好。垫只凳子,用一只布袋套上马蜂窝,连根拔下,封闭布袋,提上山去放生。
说干就干。准备好布袋的当晚8点多钟,观察到马蜂们均已归巢消停,我端只椅子轻轻放到马蜂窝下方,站上去。我情绪异常紧张,耳朵莫名轰然,兜起布袋的双手竟有些颤抖。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一兜,兜上去,笼住袋口,发力拔下。顿时,“嗡嗡嗡嗡嗡”一袋轰鸣,我浑身鸡皮疙瘩燥痒,赶紧用绳子扎紧布袋口,拧灯笼般拧下露台,出门,下楼,一路小跑,直奔山坡院墙根,解开布袋口,扔火把一样,把那一袋马蜂用力扔过院墙,拔腿逃窜……
这过程太紧张刺激了。
马蜂掀起的心理波澜尚未平静,那条巨大蜈蚣也卡在我心灵深处,使我对这露台的安全有了顾虑。
拔除马蜂窝的次日早晨,成群的马蜂又回来了,它们萦绕在窝巢根部,似乎在重建窝巢。
没想到它们如此迷恋这地方。这是个很好的地方吗?当然。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嘛。可这是我的生存空间啊!如此无视我的存在固执而激烈地与我竞争生存空间,就不怕我下绝手?当然,它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剔除毒刺后手臂依然剧烈肿胀疼痛,无比瘙痒,但我已不像昨天那么怨恨了,倒生了些怜惜和理解。为了生存,大家都不容易,何况是我把众多马蜂同心协力、耗时费力建造的马蜂窝野蛮地拔除、捣毁了。
可我不能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困扰和危险之中吧!居然很确切地触到美好人性的底线。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我抢占了它们的生存空间。
但我必须彻底赶走它们,包括那条巨大的蜈蚣。要达到这个目的,温柔的、野蛮的、甚至恶毒的办法多的是。
我在不断确认和质疑我的善良。同时,我也更加笃定着主动与这个世界和睦共处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