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环球人文地理”
01. 家乡永远在心底,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得回家过年,记得火锅的奔腾和家乡年夜饭的味道。 落梅入夏,梅开年关。关于过年,我云淡风轻的母亲是相当讲究的。 从除夕到大年夜,家里暗香浮动的必须是南山买回的巨枝腊梅,一米五长的两束,斜插在钢琴旁的钧瓷花瓶里,芬芳、雪意,甚至隐隐有上品梅子酒带来的微醉。 春节期间,拜年的亲朋推开门,也推开满屋雅致的古意,瞬间就会被香气击中,开口就是:“老太太,这梅花哪里来?街巷上没这么大的呢?” “当然是南山,南山冬天的腊梅花,江津夏天的青梅酒,年年都是要的,过年嘛,仪式感缺不得。”说这话的时候,母亲坐在客厅,脸上的笑容谦逊温和。 母亲是个有学养的老派人,讲究、素雅,保持着独一份儿的高贵和尊严,她其实做什么都很专注,仿佛天地间唯此一物一事。就像那些擦得锃亮的老旧黄花梨家具,或者睡前她必须饮的酒,以前是暗红的通化,现在是琥珀色的梅见。 家乡重庆是山城,奇幻、现代。在我的记忆里,南山的梅花一开,年意就浓了。记得读博离开的那个夏天,阳光灿烂,母亲有些不舍,她说我身上已经有了梅子成熟的味道,她说家乡永远在心底,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得回家过年,记得火锅的奔腾和家乡年夜饭的味道…… 其实母亲是遗憾的,父亲退休前是船长,常年漂泊在海洋和劣质白酒混合的味道里。然后,母亲老了,女儿却又去了大洋彼岸。 因为疫情,快四年时间,重庆和母亲都只生活在我梦里,每次站在纽约灯火阑珊的落地窗前,想起母亲的年夜饭和她热烈的飘满醉意的梅花,我的泪水总会掉落在异乡嘈杂的风中。 这时候,汤姆·克鲁斯就会从身后环抱着我,安慰地说:宝贝,我们会回去的,我们会回到老太太的年夜饭里去的。
是的,因为帅气和威猛,也因为外形实在有些酷似,我一直把我的先生叫做汤姆·克鲁斯。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几十年前从中国重庆移民过去的,所以自小,先生就有个随母姓的中国名字林志荪…… 这个除夕,当我和汤姆·克鲁斯终于回到重庆,回到母亲的年夜饭桌上的时候,南山的梅花又到了暗香袭人的季节,而母亲和父亲头上的白发,又增加了很多岁月的痕迹。 我舅舅有句名言:春节就是时光的扣子,“啪嗒”一声就将去年和今年扣在了一起,也将北地和南国扣在了一起——这个祝酒的开场白,是做语文教师的舅舅曾经每年在年夜饭上说的,从白衣飘飘说到白发苍苍。当年我将这句话写进作文,被老师用红笔结实地勾了一串波浪。 但今年的年夜饭不一样!舅舅笑着举杯:“今年我们家,将太平洋那边都扣到一起了!来,为美利坚归来的志荪,举个杯!” 汤姆·克鲁斯,哦,志荪,我的先生,此刻激动万分地站起来,第一个举起了酒杯。这个在生活中常常被我取笑只能算半个炎黄子孙的混血儿,参与我家春节的各种活动最是积极。 那一刻我有些恍惚:大圆桌上是满汉全席般的年夜饭,所有人站起来,十几个杯子碰到一起。两个正在上幼儿园的第四代,笑脸像他们举起的橙黄色果汁。窗外,有烟花和笑语在飞,一派热闹之中,我突然捕捉到了父亲的酒杯和他流淌着笑意的眼神…… 02. 父亲和酒的故事, 一如归隐的侠客, 脱下披风,前尘往事拂衣去, 只把栏杆拍遍。 但是多年前,父亲的眼神不是这样。 那时候的年夜饭上,每当全家人碰杯,父亲的眼神里只有委屈、无奈,以及孩童才有的小倔强。很多年来,父亲的这种眼神曾经是我春节记忆里最固定的闪现。 我的船长父亲性格坚韧耿直,说一不二,但遇到温柔固执的母亲,大多时候会缴械投降,溃败在每一次的眼神较量中。 原因很简单,母亲不允许退休后的老船长喝酒。一大家人碰杯的时候,父亲的眼神总会委屈地探过去,然后悲剧性地遭遇到另一双眼神的断然拒绝,最后他会叹口气,无奈地举起汤碗和我们碰杯…… 记得我读研回家的第一个春节,满屋酒杯清脆的声调里,父亲喃喃地说:过年过节的,不喝酒像什么话嘛?母亲秋波一寒,回答道:你的肠胃怎么回事,你不清楚吗?于是父亲只得闷闷地低下头,可怜地举起了汤碗。那一刻,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父亲是从船长位置上退休的。小时候去过父亲的船,那是一艘很多层楼高的巨轮,气派、辉煌、漂亮。 我深切感受到父亲的工作和别人是不一样的,那是领着一群人驾驶着庞然大物,航行在江河湖海上的豪迈。我记得水手叔叔们看向父亲的眼神,坚定、严谨、忠诚、等级分明,那层层传递的信任,最终全部集结到父亲身上。板着脸一丝不苟的父亲很严肃,表现得机智,沉稳、经验丰富。 即使在家中做主的母亲到了船上,也是要扮演一个温良贤淑的配合者。也只有我,才敢在甲板上举着手要求冷面船长抱,抱起来还笑嘻嘻地捏着船长的鼻子问:“你怎么不笑呀?爸爸。” 每结束一趟航行,父亲都会带着他的船员们喝一场大酒。喝醉后被送回来的父亲,总是满身的酒气和海藻味,偶尔还会被罚睡一个星期的沙发。 尽管如此,但母亲从未阻止过父亲远航归来的大酒仪式。只是经年累月下来,父亲的胃却不行了。光荣退休的老船长,从大海回归到妻子的客厅和饭厅。每当举杯团圆的时刻,在爱与责备的眼神里,老船长只能慢腾腾地举起自己的汤碗。
这是一大家子早就默认了的场景。父亲和酒的故事,一如归隐的侠客,脱下披风,前尘往事拂衣去,只把栏杆拍遍。 但今年的团圆饭上,父亲却一反常态地端起了酒杯,那酒杯透明幽深,里面荡漾着好看的琥珀色。 我有很多疑问,但最终被汤姆·克鲁斯提了出来,这个家伙知道父亲的故事,而且常年对船长岳父充满好奇,他操着拗口的普通话问:“老船长,为什么要干杯?你不是一直喝汤吗?”然后连比带划地问母亲:“妈妈,你——不妻管严了吗?现在——爸爸是不怕你了吗?” 全场忍俊不禁。甚至威严的铁面船长也笑出声来,但他没有接话,只是用海洋般的眼神温柔地望向妻子。 母亲压住笑,以一种独有的矜持和优雅解释:“志荪啊,中国人的年,没有酒,实在算不上团圆,你岳父喝的是梅见,用梅子酿制,度数适当,暖胃,舒心,我们已经喝了好些年,睡前喝上一杯,夜里会很安稳,他这样的年龄,白酒燥、啤酒寒,喝喝梅见就很好……”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母亲,而她正起身去打开一瓶梅见。 这时候,汤姆·克鲁斯蹩脚的普通话再次响起:“梅见?梅子?是我美国妈妈最喜欢的那种酒吗?” 03. 我真的好想告诉他,什么是西岭雪山上的青梅味道,什么是梅子眠霜卧雪、入坛成酒,什么是古典的诗意…… 实际上,无论中文系本硕连读的我在少女时代有什么遐想,都没有预计到第一次去汤姆·克鲁斯家晚宴的场景:他的父亲,一个头上捆着红头绳的金发碧眼老绅士,看到我的时候是如此雀跃,他在四盎司威士忌之后,突然如梦方醒地带着我和他的儿子去到后院,取出铁锹,借着美利坚的月光,挖出来一坛深埋的青梅酒。 老绅士说:“林志荪终于把他心爱的姑娘带回家了,这坛酒,可以开了,这坛酒,是志荪妈妈留给你的……”他的美式英语很磁性很清脆。他说这话的时候,泪水突然涌满了眼眶。 后来我才知道,汤姆·克鲁斯的妈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重庆抵达美国的,比我来这里的时候还要小,刚刚高中毕业。从工作签证熬到拿绿卡,经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一直到后来读大学,遇见了汤姆·克鲁斯的爸爸,结婚生子,安定下来。 再后来,他们搬到罗切斯特市郊,林志荪便是在这个总是杂草妩媚的小院里长大。 在汤姆·克鲁斯出生的那一年,他的妈妈便请重庆的家人带来肥硕欲滴的梅子,酿出一坛青梅酒,深埋在院子里,他的妈妈说:等儿媳进门的那一天,打开酒,按照中国人的礼仪,好好醉一场…… 但遗憾的是,汤姆·克鲁斯的母亲后来因病去世,而她说出的愿望,基本上类似于遗言。 作为中文系的女生,我知道我未见过面的公婆埋下的那坛酒,其实就是传说中的状元红。 当我喝下去的时候,已经是她离世的第十九个年头。 那一天,在汤姆·克鲁斯家,酒香馥郁,芬芳内敛,仿佛柔软甜美的河流溢进口腔,婉转迤逦到愁肠。那一天,罗切斯特市郊绿草如茵,纷纷扬扬的雨水洒落下来,空气里仿佛有了重庆南山梅花的香气。 那一天,我端起的酒杯琥珀流光。第一口,流烟清驿路;第二口,如见故人归。第三口的时候,我仿佛看见汤姆·克鲁斯的中国妈妈,撑着一把油纸伞翩然南山下,季节是梅子成熟的初夏……
2023年的年夜饭,缺席四年后,我终于回来。 十多个人围桌举杯的时候,我的老船长父亲端着宽口的酒杯,杯里的琥珀色晶莹剔透,他脸上的笑容有一种多年没见的释然。 而我的汤姆·克鲁斯酒量显然很大,后来他放弃了茅台,开始喝起梅见,边喝边用奇怪的中文语无伦次地说:梅子酒,妈妈的酒,我最喜欢的中国的酒,我的老船长,你是美国人的好朋友…… 看着笨笨的晕得萌萌的汤姆·克鲁斯,我真的好想告诉他,什么是西岭雪山上的青梅味道,什么是梅子眠霜卧雪、入坛成酒,什么是古典的诗意…… 这个难得的除夕和迟到的年夜饭有些漫长,重庆南滨路的满天烟花一直灿烂到了热搜,我们一家人欢声小酌,一直到深夜。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有些微醺,我们其实想一直喝到大年十五元宵夜。 后来,我和汤姆·克鲁斯相拥在落地窗灯火阑珊的客厅,南山梅花的暗香里,我抬头看见窗外天心月圆,花枝春满。那时候,我仿佛惺忪地看见我没见过面的公婆,穿着一袭梅花旗袍,走在梅子如雨的重庆,身上散发着梅见酒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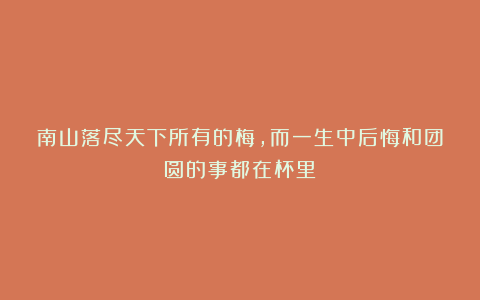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